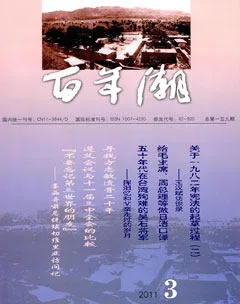战火中的抗日战争史料征集委员会
抗日战争爆发,北平院校匆匆南迁。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先生偕北图一部分同人南下,先后与长沙临时大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合办后方大学图书馆。在此期间,深感关于此次战争的文献需要及时搜集整理并加以保存,以备将来纂成专书,以记录我中华民族此次伟大的奋斗经过。为此,北平图书馆与西南联合大学合组中日战事史料征集委员会,于1939年1月1日正式成立,地址在昆明大西门外地坛,经费由两单位分担。史料会由委员会领导,委员会由袁同礼、冯友兰、刘崇鋐、姚从吾、钱端升、傅斯年、陈寅恪、顾颉刚诸先生组成。其中,袁先生任主席,冯友兰先生为副主席,姚从吾任总编纂,刘崇鋐任副总编纂,钱穆、郑天挺为中文编辑,叶公超、蔡文侯、雷海宗为英文编辑,吴达元、邵循正为法文编辑,刘泽荣为俄文编辑,皮名举、冯文潜为德文编辑,王信忠、傅恩龄为日文编辑。
史料会的工作分征集、整编两部分。北平图书馆负责采访、征集和初步整理,西南联合大学则负责编纂。征集史料不仅限于战争本身,包括政治、社会、经济、交通、教育及其他方面;搜集之范围,不限于本国及中文书刊,除昆明外,也在重庆及沪港等地派有专人在各地搜集出版或市面发售的有关报纸、杂志及小册子等,其中包括欧美、日本、苏联、南美等,也包括敌国以及各中立国之出版物,月与此次战事有关者,办均搜集。
初期参加史料会负责具体工作的人有:万斯年(中文、日文采访)、王育伊(中文资料整理工作)、高亚伟(中文战事书籍提要)、赵芳瑛(中文杂志索引)、周正福(中文剪报)、颜泽霪、刘金宝(西文采访和西文资料整理工作)、王厚真(西文杂志索引)等。虽然后来人员历经变动,但工作效率很高。
搜集工作方面,仅1939年1月到4月四个月的时间,已搜集到:中文书籍846种;西文书籍177种,西文小册子238种;日文书籍267种;订购中文期刊359种(伪组织刊物10种),西文期刊133种(英文116种,法文7种,德文8种,意文、荷文各1种);日文期刊32种;中文日报94种(伪报15种);西文日报39种(英文23种,法文4种,德文7种,意文1种,俄文4种);日文日报8种。资料搜集包括:远东问题专家论著单行本,外国人士同情抗战之讲演稿,各国驻华新闻记者稿件,外侨之机要函件及报告书,各国教产被毁损失调查,各国商业损失调查,各国社团及工会抵制日货之宣传品与广告,海外中国各政党之出版物,文化机关被毁调查,医药防疫及战地救护设施报告,敌人汉奸之宣传品,战地照片等12项。在整理工作方面有日报剪排归类。剪报排列方法分编年及分类两种,编年从时序,分类依性质,暂拟九大类,即军事、政治、经济、交通、文化(含教育)、民运、各地、日本、国际关系(含外交)。订出剪报详细实施办法,每种日报有一份不剪,作永久保存。对搜集到的中日两国及国际间出版的中日问题之小册子,也按类排列,以供研究之用。
编辑工作方面,4个月中已初步编成或正在编辑的有《卢沟桥事变以来大事日历长编》、《卢沟桥事变以来每日战况详表》、《卢沟桥事变以来战局转移地图》、《卢沟桥事变以来中日战事简明一览表》、《中日战事纪事长编》、《卢沟桥事变以来新出战事书籍提要》、《西文中日关系书目》、《西文中日关系书目汇编》,并出版了《暴日侵华与国际舆论》英文本第一辑。
索引工作进行的有中文杂志索引、西文杂志索引(根据欧美出版13种索引如《读者期刊文献指南》、《国际期刊索引》等,将论及中日战争或远东及太平洋问题者编成《中日战事论文索引》、《中国问题论文索引》两种);另编英文《中日战时公牍索引》、《战时中国国际关系史料汇编》等。
以上编辑工作的基础在于事先广泛搜集大量的图书资料,而这些图书资料的搜集是煞费苦心的,处于战争年代,艰辛倍于平时。除在后方(昆明、重庆)征集外,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袁先生曾向中国共产党代表机关,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领导人周恩来同志提出申请,请求支援搜集抗日史料工作,周恩来同志和驻陕办事处林伯渠同志热情支持。1939年4月10日,林伯渠同志又致函李俨先生,请他转交北平图书馆书籍50册。同年7月17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函告北图馆长:兹有周副部长交下书籍数十册,今后尚有陆续寄上。并附赠书清单。此后,北平图书馆昆明、重庆两办事处直接与延安解放社、延安新中华报社、延安新华书店、重庆新华日报社等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出版机关建立了经常征订书刊、日报的业务联系,按期订购《解放》、《中华》、《新华日报》、《群众周刊》、《新中华报》等。由于我党老一辈革命家在繁忙的抗日救国工作中热心关注搜集抗日史料,使我党早期出版的一批批珍贵的革命文献与抗日史料正式公开入藏北平图书馆,这也是北图馆史上的重要一页。
同时,北图还在沦陷区搜集敌伪资料。此项工作袁先生交给驻上海办事处的钱存训先生来做。当时上海分馆任务很繁重,但还兼任敌战资料的搜集工作,奉命搜集日本和伪组织方面的刊物和文件,小至居住证、通行证、配给证、传单、布告,大至中日文合刊的各级伪政府公报及地方报纸。这些都是在京沪两地搜集后寄到香港办事处,再转送昆明。在敌占区,搜集史料更为艰苦。一方面征订不在日伪“禁例”的刊物;另一方面与党政军机关联络,搜集宣言、传单、秘密刊物及报纸;同时又与外国驻华使馆、报社各方取得联系,征求“外人投资损失调查”等材料及各种刊物;还和图书馆、图书馆服务社、各书店(包括日本内山书店)打交道,为的是采购或转购图书、杂志、报纸;也曾托上海工部局教育处负责人代为征求各救济机关团体文献。总之,凡一书、一刊、一物往往是几经周折才能取得,而寄往中转站香港办事处邮包曾有过被检查扣留等情况。至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唯一渠道被迫中断。存储之史料,有些未及运昆,深为可惜。
抗战胜利前史料会征集的史料,仅昆明部分,据不完全记录,入藏有中文书5180种。约6000册,中文小册子400余件,中文杂志2350种(其中继续出版的485种)。其中,中文报纸169种;日文书520册,日文杂志120种,日文报纸8种;西文书1922册,西文杂志373种,西文报纸49种。1940年7月,史料会曾编印《战事史料集刊》,将已整理之史料分期刊印。后另印丛刊,分中文之部及日文之部,每集约10种,均已脱稿。已编就者尚有各战区长编14种,《抗战书目提要》1种(由中国文化服务社印行)。尚未成书者有抗战论文索引3万余条,分类剪贴报纸50大箱,辑录欧美论中国之各种论文数百篇,成绩斐然。
我是1943年在西南联大毕业后,受聘于北平图书馆为助理编纂,8月留史料会参加工作的。半年后,改聘为西南联大历史系助教、清华大学历史系助教,仍在史料会工作。由于经费拮据,交通阻塞,此时史料搜集更为不易。而这时史料会的工作人员已几经变动,比初期相对减少,有的人另有安排,也有的赴美留学或去各地直接参加抗日工作等等。当时的人员大都是受聘于北图和清华、北大历史系,工作仍分图书、杂志、日报、剪报几个分组,暑假时有历史系学生来帮助整理资料。冯友兰和姚从吾两位先生下课后常到史料会去指导工作。袁先生那时大部分时间是在重庆或到国外去为图书馆事业而奔波劳碌,到昆明时当然必到他苦心经营的史料会。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宣告结束,史料会也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西南联大除师范学院和附中继续留昆(今为云南师范大学)外,三校师生陆续北返平津。6月,我也随学校北返,回到北平图书馆。
史料会的图书资料托运是和西南联大的图书仪器一起由昆明起运抵平津的,到1947年夏始陆续运回平馆。当时这些史料存北海静心斋,派专人管理,并继续征集。1948年5月16日,在北海静心斋举办抗战史料展览,计分:抗战史料、敌伪资料、战时期刊及剪报、战时日报、敌伪期刊、敌伪日报等六个陈列室,总共约1.5万余件。此项史料为国内仅有之一部,展览中对各次战役及游击战等珍贵重要史料均已陈列,展览充分展示了八年艰苦努力结出的累累硕果。
回忆当年,抗日战争爆发,平津相继沦陷,共同的遭遇使清华、北大、南开师生和北图同仁辗转流亡,汇集到长沙;当战火迅速蔓延,不得不“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时,北图和学校又一起迁往昆明。到联大开始了“笳吹弦诵在山城(昆明)”的峥嵘岁月时,北图和联大又共同在史料会并肩作战。当时史料会设在西南联大后门外的地坛,历史系办公室和史料会同在一院,遥遥相对。地坛地处偏僻,四周都是荒丘野坟,旁边只有一条羊肠古道。每当风雨来临,周遭的白杨树沙沙作响,令人有荒漠之感。但史料会内工作却是有条不紊,各种资料邮件源源不断。
西南联大是与抗战相始终的,史料会也与西南联大相始终。由于联大师生和北图同人大都来自战区,亲历战火,辗转流亡,备尝艰辛,因此不论个人原来的政治倾向如何,爱国主义的精神是共通的。史料会能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征集和保存那么多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一手资料,这是北图和西南联大风雨同舟、亲密合作的丰硕成果,也是袁同礼先生的卓著功绩。这段经历是令人难忘的。
我在史料会工作三年后,又回到北平图书馆。袁先生作为一馆之长,不苟言笑,态度比较严肃,但交谈时却平易近人。只要他在馆(他常到国外),就习惯到各办公室去转转,且事必躬亲,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时光流逝,一切事都已是60余年前的了!至于史料会,它在北图的历史长河中仅仅是一条小小的支流,为时虽短,但毕竟是一段不寻常的历程。因此,就我零星所忆,写此短文,略填北图馆史空白的一角,并以此纪念为我国图书馆事业奠定永久基础的袁同礼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