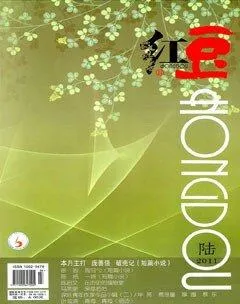天地遗痕
诗意安居一陇东剪纸
陇东,广袤厚重的黄土地上,掘出一个个暗沉沉、灰朴朴的窑洞。坐在炕头的老婆婆,拿一把剪刀,折好一张大红纸,信手剪去。艳艳的门神、窗花、炕围花、顶棚花之类依次贴起来之后,窑洞忽然变得光彩耀眼,对生活的渴望和幸福感开始满溢出来。
剪纸,是平易的生活里绽出诗意的花朵。
小时候,要过年了,奶奶就剪了各种各样的窗花,我的任务是把那张剪完的纸一点点地展开。
起伏不断、牵牵连连的线条,稍不小心就弄断了。展开后,一波连着一波,旋转着铺开去,每一剪刀都是有道理的。
看着简单,奶奶画好图案让我剪。可是不是这剪断了,就是那儿少剪了。
剪下来的窗花,奶奶再打了稀稀的糨子,贴在窗户上,旧旧的窗格子立刻有了节日的喜庆。
剩下的碎红纸,不要了,我沾些水,把嘴唇脸蛋染得鲜红。
奶奶说像猴子屁股,难看死了。
后来去峨眉山,见很多猴子,它们无一例外地将红屁股藏着掖着,像是知道难看,满怀羞愧一般。
红纸摸一下就把手指染红了。红色向内折着,握着剪了半天的奶奶的手却干干净净。
鲜艳的红色被窗棂子框着,在日子里一点点地变旧。
明年,又会有新的红色,喜庆而又鲜艳的红着。
奶奶不是陇东人,奶奶那个年纪的人,会剪纸就像吃饭、睡觉一样,仿佛是她们生活的一部分,自然而又顺理成章。
我要说的是被安放在陇东大背景下的剪纸。陇东剪纸多用红色或黑色纸,轻飘飘的剪纸承载着陇东最厚重古老的文化。我固执己见般觉得,剪纸,就应该用最鲜艳的红色。如同陇东厚厚的黄土地上开出来的一条花,浸染了太阳的颜色,质朴而美丽。
这条花,可以这样开,也可以那样开,随意而没有定式,充满着多方面的可能性。我见过很多个版本的陇东“回娘家”剪纸,有坐轿回的,有骑驴回的,有的甚至剪了个轿车上去,扎了朝天小辫的孩子蹦蹦跳跳地跑在母亲前面,心情急切,外婆会给糖吃吧,于是在画面上灿烂地咧开小嘴笑着。
周先祖公刘在董志塬上挖窑洞,建村落,教民稼穑,那时还没有纸,我很好奇他们用什么来装饰窑洞。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原始人尚且挂了骨头或石子串成的项链系了短裙,这才挥舞着长发手拉着手跳起舞来呢。
跳着跳着,跳上了彩陶罐。陇东出土的大量仰韶时的陶器上,画着手拉手跳舞的小人,一囤又一圈,望久了令人目眩。
又有大肚子的青蛙和鱼,随着荡漾的水波纹,一路游上陶罐。披散着长发的女子一边提着尖底双耳瓶去马莲河打水,一边想,我为什么就不能一次多生几个孩子呢?
旧石器时代的岩画、仰韶彩陶、秦汉画像石及画像砖,一路看下去,似乎都能在后来的庆阳剪纸中找到相似的形象。
司马迁曾感慨日:“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这些司马迁“不敢言”的“怪物”到底长什么样呢?陇东剪纸中大量动物的奇诡形象似乎可以让我们当做参考。仿佛是古时的蛙、鱼、虎、牛、蛇、蜥蜴、鹰、鹿、羊等,穿越数千年的时空,走到了陇东剪纸中。
有幅叫做《鹿鹤同春》的剪纸,一棵形似鹿头的树,树梢栖有两只鸟,什么鸟呢?看不出来,“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估且认为是喜鹊吧,传说能够带来幸福的鸟。树干左右两旁,各剪鹿鹤一只。鹿长着曾在彩陶罐上炫耀过的两只阔大的角,鹤则伶仃着一双细瘦的腿,一只立着,一只暂时收起来歇歇。鹿鹤图腾象征纹样,两汉时流行最广。马王堆汉墓刺绣纹样和汉画像石图样中,都有着相似的图形。
剪纸最早的记载当推世居陇东的东汉哲学家王符。他在《潜夫论》中说:“或裁好缯,作为疏头,令工采画,雇人书祝,虚饰巧言,欲邀多福。或裂拆缯彩,裁广数分,长各五寸,缝绘佩之。或纺彩丝为縻,断之以绕臂……或赳削绮毅,寸窃八采,以成榆叶、无穷、水波之文,碎刺缝,作为笥囊、裙襦、衣被,费缯百缣,用功十倍。”显然庆阳人很早就用功于裁剪各式花样了。
说剪纸,让人先想到造纸术。自从东汉的蔡伦发明纸张后,中国的文化就有了开天辟地的变化。连篇累牍的厚重历史告一段落,后来的书生们意气风发地说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放马滩的西汉古墓中,出土绘有地图的麻纸。暗沉沉、灰朴朴的地图,像是在窑洞里画出来似的,还是在那种没有贴窗花的窑洞里,因为,没有生机。
纸渐渐地除了印书写字绘地图外,也有了别的用处,比如剪出一些形象来祭奠或是装饰,慢慢的,也有了鲜艳的红色。
剪纸和窑洞,是绝配。
写到这里,秋风瑟瑟,吹得窗户一开一合,起身望望窗外,一株高大的新疆杨散了一地的枯叶。忽然想起《史记》中的有剪桐封弟的故事,记述西周初期成王用梧桐叶剪成“圭”赐其弟,封姬虞到唐为侯。这是剪纸的雏形吗?很是严肃而隆重。梧枫叶不是杨树叶,只是树叶“圭”放久了,就是眼前满地枯叶的样子吧。
在关注陇东剪纸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男性剪纸艺人多为风水先生。f电1门将剪纸或化为灰烬或贴于某处,常与招魂、辟邪、送病、疗病、镇宅、压,凉、驱鬼、祈雨等种种民俗相关。比如,迎亲途中,遇到庙宇、大树、巨石、水井或十字路口时要撤红纸狮子驱邪。再比如庆阳人视“疳”为恶神,每年正月二十三“燎疳”,家家门口点起火堆,剪好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图案的纸人,男女老少拿点燃的香烛给剪好的小纸人点出眼睛、鼻子、耳、嘴及指头,哪儿不适就用香点纸娃娃的哪儿,然后烧掉。
剪得最多的是各种各样的“抓髻娃娃”。抓髻娃娃两脚分开,稳稳地站着,双手都很忙,忙着握住鸡、鱼、虎、兔什么的。形象接近金文的“天”字,传说是轩辕黄帝的族徽。春节时候贴门上,可以户户添吉,人人增富。
儿时,春节的时候我家贴的是门神,奶奶不会剪抓髻娃娃,奶奶只会剪秦叔宝和尉迟敬德,他们无论白脸还是红脸,在剪纸上都是红艳艳的,从唐朝辛苦地站到了今天。
中国人一向对红色有着天生的好感,逢年过节,铺天盖地的红,弄得喜气洋洋、热热闹闹的,这才放心。
自古以来,红色就是象征喜庆、吉祥。民间以朱砂辟邪,用来悬之门户,抵制恶气。
古人修建门户大多不是防盗,而是好看,所以有“夜不闭户”之说。灾难降临,妖魔鬼怪来袭,门神装饰着我们的梦。
有一位世外高人授方,在香囊里装入朱砂,放进七根灯心草七粒黑豆,再放一些经咒或桃木符,可以辟邪。
这是中成药朱砂安神丸的成份,可以扶正祛邪。
红色的朱砂有着最纯正的红,皇帝批阅奏折时专用的颜色。天下见了都要跪拜接书,不能正视。
有女子长朱砂痣,殷红一点,如果位置恰到好处,更添韵味。《红楼梦》中的香菱就是如此,眉间一点红,只可惜红颜薄命。
红颜自古多薄命。宋代时不仅三寸金莲之风盛行,天下女子走起路来一步三摇,于是只好乖乖地呆在男人们的视线之内。而且贞洁之风越刮越甚,流行“守宫”痣。相传用瓦罐一类的东西把壁虎养起来,天天喂给它丹砂,大概吃到七斤丹砂的时候,就把壁虎捣烂,用来点在女人的肢体上,殷红一点,以测女子贞洁与否。此法据说只适合用于未婚女子。
与辟邪的香囊方子一般,带着巫气。
去庙宇或法坛,求得一道保平安或是驱邪避灾的灵符,多是黄纸红字,而灵符上面的红字,就是用朱砂画上去的。
其实单用朱砂是不能令黄纸上色的,需要加上花红粉用水调和,才可以成功画出一道红字灵符。还有些符是要烧成灰后掺水口服的。
想起丰子恺说他初习画时,就是从画灵符开始的。再看他的小品画,质朴而民间,更是个个深意无穷,让^忍不住想绕到画的背面去看看。
在中国传统剪纸与外国现代艺术之间,有一个人可以看做桥梁,他是获得世界声誉的中国当代剪纸艺术家吕胜中。
吕胜中的“小红人”剪纸,小小的身体顶着硕大的头颅,四肢伸展。这个酷似婴儿的形象,大大小小一串一串挂满后,有着奇异另类而震撼人心的力量,他自称为招魂堂。招魂堂原本是他做给自己宿舍的装饰,如同贴在窑洞的剪纸一般,是他对自己生活的“诗意的安居”。
他曾自言:“有很多时间,我都在挣扎着走出民间,力争不要像民间……不是显出学院派的拘谨的马脚,就是有着马蒂斯的癫狂……”
吕胜中最终从学院派走上了追寻传统的道路。野兽派的马蒂斯也是位剪纸高手,晚年因为疾病折磨,只好在床上,拿一把大剪刀,用各种颜色的纸,继续表达着他对形式美的热恋与执著。细微的剪刀声响震惊了巴黎的艺术界。
从现代剪纸艺术的康庄大道绕回庆阳传统剪纸的乡间小路。没有暮归的老牛,只有一株巨大的生命树。
陇东闻名的剪纸艺人彭粉女,有幅叫做《生命树》的作品。树枝用力向八方伸展,有飞翔之势。让人想起凡·高的《星月夜》,旋转神秘的天空,让我更想看看天空下面的大地是什么样子。画家画了一座座立着烟囱,弥漫着人间气息的小房子。生命树上,老鼠、猴子等动物攀缘其间。
《山海经·大荒东经》说:“大荒之中有山名日孽君页、羝,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叶如芥。有谷日温源谷,汤谷上有扶木,一日六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古人认为山不及天,则有树接连。树为登天的工具,直插云霄。彭粉女的生命树剪纸仿佛是对这记载的翻版。
相传古羌人一支由陇东而迁南,成羌族,羌族遗风南北相同。至今羌族人依旧认为树神威力无比,主宰五谷丰登、祛灾赐福。每年端午,他们都要举行祭树仪式,男子挂五色旗,进神山点燃柏枝,将五色彩旗敬献给一棵高大挺拔的大树,以此为保护神。
陇东剪纸,充满质朴而民间的意味。一草一木,一人一物,皆可剪了进去。再起一个个吉祥喜庆的名字,二龙戏珠、麻姑献寿、鲤鱼钻莲、五福捧寿,凡此种种。简单,却又透着原始象征的巫气;繁杂,却又凝练地突出了所要表达的东西。
一幅叫《官上加官》的剪纸,昂首挺胸立着一只大公鸡,鸡冠如花,站在鸡冠花丛中,火红的鸡冠与鸡冠花争艳吗?硬是一枝高过一枝去。官(冠)上加官(冠),真是喜人的好兆头。
看到一张彭粉女坐在炕头拿一把大剪刀剪纸的照片,像我奶奶。
奶奶得了类风湿,手脚的关节一天天肿大,甚至变得弯曲,指关节向一旁扭曲,像斜着从皮肤里长出来一般,鼓着,泛着亮光。
奶奶的手指头放不进剪刀把子里了。奶奶的手日以继夜地疼着,甚至握不住吃饭的勺子。
我撕一张作业本上的白纸,折好,剪了一串手拉手的穿着裙子的跳舞娃娃,小心,不把手拉着的地方剪断。不用等过年,把这串娃娃放在奶奶炕上的时候,奶奶露出天真的笑容,像是小时候,我把奶奶剪好的纸一点点完全打开时的那种出乎意料的惊喜。
抓髻娃娃、小红人、手拉手的跳舞娃娃,它们反复在我的梦里出现。梦里,我敞开屋门,让这些小人,—个个走进屋来。我小心翼翼地做守护者,诗意地安居。
细致入微的“绌绌”庆阳香包
2002年,庆阳举办首届香包节,我们仿佛是循着香味奔着去的。满街的香包,飞禽走兽、瓜果梨桃,无所不包,无所不有。
香包又叫“绌绌”。庆阳女子七八岁便习针线,绌绌又叫藏针绣,把针脚全部藏个无影无踪,龙啊凤啊花啊草啊,就从香包E跃然而出。像是用精益求精的针线功夫反驳,越叫绌绌,就越细致入微。
见一只半圆的香包,带盖,可以打开,用来装手帕什么的,又有可以挂在身上的带子,很有些古色古香的意味。一问,说是双塔寺的千岁香包的样子。
双塔寺坐落在子午岭中部的河谷地带,豹子川与双塔沟小溪交汇处的—个小台地上。
豹子川听着就是英雄出没的地方,曾经辉煌一时的双塔寺为金代海陵王的近臣所建。近臣是谁?《石塔院记》的碑文已经残缺不全了。
爬上子午岭至今能看到秦直道遗迹,始皇帝帝国的康庄大道,原本可以让秦国高大的四轮马车一路奔驰下去。可惜,才秦二世,就芳草萋萋了。始皇帝大概没有料到自己会在巡游的途中睡下,不再醒来,连夜赶书的诵功碑文刚刚写好,还没未来得及刻出来。而此时,太子扶苏在子午岭日夜督修秦直道呢。
秦直道,宽阔笔直地伸向夕阳的方向,太子扶苏饮下长安方向快马加鞭送来的鸩酒。夕阳轰然坠地,无尽的黑暗。
而我此时在想,子午岭上,秦时的工匠戴不戴香包呢?
中国最早的医学著作《黄帝内经》中记载,《黄帝内经》的作者歧伯曾经随时携带一只可以驱瘟疫、防蛇毒的药袋,并开创了“熏蒸法”。
J射白是庆阳人,从此装了各种草药的药袋在董志塬人们的身上层出不穷。人们将这种带在身边的药袋称为香包。
屈原在《离骚》中写道:“扈江篱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江篱、辟芷、秋兰皆为香草。纫是连缀之意。这里的意思是说屈原所在的战国时期,人们已经开始把装满香草的饰物带在身上。
秦时按说已有佩戴香包的习俗。汉代《礼记》中日:“男女未冠笄者……衿缨皆陪容臭。”容臭是香包的又一种说法,与绌绌的称呼似乎有些相似之处,说明汉代未成年的男女都是佩戴香包的。
双塔寺,两座高耸的金代砂石塔,远望着遥不可及的秦直道,继续着宋代美女细细瘦瘦的造型。
其中的一座曾被盗割往台湾,后来追回。那么高的塔,月黑风高夜,黑衣人不是飞檐走壁,而是登上半山,然后,“咯吱咯吱”地锯塔,动静有些大啊。
先盗走了九层,后又盗了两层,塔共十三层。
政府组织了考古队,开始了紧张的发掘工作。清理出金至明代大殿、偏殿、钟楼、三门殿等重要建筑基址,出土数百件文物。金代香包是从另一座塔里得以重见天日的,人称千岁香包。
好在被盗的不是香包,否则怕是没那么好找了。
千岁香包上面刺绣了轮回的纹饰图案,据说这种图案由梅花变形而来。从唐代起,它就被作为佛胸前吉祥的标志。细看《西游记》,唐僧师徒终于到达西天求得真经,佛胸前就饰有旋转形的这个图案。一只小小的香包,绣上细细密密的梅花、荷花,还有枝枝蔓蔓的图案,原来是按照佛教教义设计,带着这件小香包的人应该有着一颗虔诚的向佛之心。
唐宋时,香囊不再是仕女们专用,官吏们也开始频繁地佩戴荷包了,有的甚至上朝时也将荷包缀在朝服之上。当然,荷包与香包不完全一样,香包里主要装的是香草,而荷包主要是用来“盛手巾细物”等,像现在男士随身带着的那包餐巾纸。社会越发展,日子却越过越没有那么用心了。
从双塔寺出土的金代香包,就是可以装手巾的荷包。
明清两代,香包已十分兴盛。《红楼梦》里基本上人人都戴了香包出场。丫头们拿在手里给主子绣的东西里,常常是各样的香包。
司棋送给表兄弟的定腈物,也是一只香囊。
《聊斋》里的狐女们徐徐走出来时倒是没有特别强调香包。可是,我感觉她们一定带了—样散发着香气的香包,这是人间的气息啊,可以遮去狐狸的妖邪味,让她们一个个在人间的书生面前千娇百媚起来。
一女子摊前,挂着用绿布卷盘成的蛇,上面绣了几朵艳红的梅花,让我觉得这是一条诞生在这里充满乡土气息的龙,忽一日就会飞向这块厚厚的黄土地上面的天空。
勇猛威武的老虎狮子,祛除邪恶之气保平安。鱼儿钻莲蓬,自然是比喻爱情的。葫芦和石榴多籽,戴上盼望多子多福的。大枣、花生、桂圆、莲子,是要送给新婚的女子,取其谐音,早(枣)生贵(桂)子之义。
庆阳手执针线的女子又个个像是抽象艺术家,并不拘泥于真实,或大头小身,有头无尾的比比皆是,却又个个神似,完全由刺绣时想法肆意为之。庆阳的风味被庆阳女子以这种方式呈现了出来。满是意念化了的浓得化不开的黄土的味道。
“猫吃老鼠”的香包,猫吃掉老鼠后,猫肚上清清楚楚绣着几只神态安然的小老鼠,仿佛是猫和老鼠的又一种生活方式。
人形的香包上面,前后都长着鼻子、眼睛、嘴。一次在甘肃省博物馆看青铜器展,见一只祭祀时巫师戴的面具就是双面的,上半张脸方下半张脸圆,头上长角,前后都长了五官。戴上这样的面具,无所不能的神就来到了人们面前。
戴上人形的香包就可以眼观六路,多好,人便有了神力。
从庆阳回家的时候,车上所有的人都买了大包小包的。满车弥漫着香草的气息。回到家,俗艳巨大的香包挂起来时,怎么看都觉得没有在庆阳看的时候漂亮。
庆阳香包的美丽也是要有庆阳厚重的黄土为背景的。
我带回来两只小小的、用彩绳盘绕缝制而成的壁鞋,挂在墙上,下面垂了细长的流苏。壁鞋避邪,果然事事顺利了很多。
这也是一种生活的意念化吧。牛郎织女来相会——西和七夕节
又是一年七夕节,记得这个节日是因为儿子的生日。七夕节,月色正好,每年我们都吃着蛋糕点着蜡烛过七夕。
这一天,是中国的情人节。不吃巧克力没有玫瑰。从清晨的第一缕曙光,到暮色四合。天上人间,仿佛都在等待着一次饱含着期盼的欢聚。七月七日,是牛郎带着一双儿女与织女相会的日子。
夜幕降临,黑暗让天空有了大地一样的厚度。银河,—条流淌着星星的冰冷的河,流水记录了牛郎和织女又一年隔河相望的生活,除了星星,银河里还流淌着哀伤、恍惚、无奈、期待,和这一天的喜气洋洋。
王母金簪一画,画出一条银河隔开了牛郎和织女时,他们的孩子从筐中爬出来,扑在河边,拼命用葫芦瓢想要舀完银河里的星星——舀得亮晶晶的星星撒得满天都是。
西周的《诗-小雅·大东》中,牛郎和织女曾是天上两颗亮闪闪的星星。到了汉代的《古诗十九首》中,他们俨然已是一对相亲相爱的爱人。诗中对f蛳]离别后织女的生活进行了描述:“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
七夕,半个月亮挂在天上,合家相聚的织女不忘赐福给最灵巧的女子,于是又叫“乞巧节”。
甘肃陇南西和的“乞巧节”是最隆重的。西和志书中推测,织女是秦人的先祖。
殷商时,秦的祖先被分封在西和一带,因养马发迹。去西和路上,弯曲起伏的山脉万马奔腾般闯进视线,仿佛听到黄昏长嘶一声,夕阳轰然落地。
织女从山之东移家到河之北,荒凉是荒凉,与牛郎的好日子从秦朝就开始过起吧。
乞巧时,姑娘们穿起绣花鞋,镶花边的大襟衣裙,头顶丝帕插花,手拉着手唱起《迎巧歌》:“每年有个七月七,天上牛郎配织女。巧娘娘莲花台,南天门你开开,把我巧娘娘送出来。一片天两片天,我把巧娘娘接下凡。巧娘娘穿的缎子鞋。我打高山接你来。巧娘娘穿的偏带鞋,我打河边接你来……”
据说牛郎织女故事的发源地在山东沂源,沂源有个织女洞,相传洞里曾经住过织女。人间的生活是务实的,除了织布,织女整日四处忙活个不停,烟雾弥漫的灶台边,磨粗了织女的纤纤擢素手,风送来田野的气息,牛郎望着飘飘悠悠的炊烟回家。风穿过篱笆轻轻摇动院子里的黄菊花,立着的竹板门影子被光拉得又细又长印在地下,整个小院弥漫着细细碎碎的安详和愉悦。
织女洞里住过的,也许只是每日辛勤织布的普普通通的山东女子而已,爽直、能干,下了织机,织女大概还会做白纸一样整整齐齐的山东煎饼,卷了屋前园子里种的大葱,带一罐粥,给放牛种田的牛郎丈夫带到田边当午饭。
七夕。最有人情味的是喜鹊。成群结队的喜鹊穿了黑色礼服,露着白色胸衣,严肃地飞上天去,搭起一架温暖的拱桥。它们忽然停止了唧唧喳喳,天空寂静,明月是一扇门,空出幸福的庭院。
记得儿时,隔壁男孩子爬上门前粗壮的榆树,从树顶的喜鹊窝里,掏了两只羽毛还没有长全的小喜鹊回家。结果喜鹊围在他家门前窗外,只要他一出门,成群结队的喜鹊追在他的后面,使劲地叫嚷着啄着。后来他把小喜鹊送了回去,喜鹊们还继续追逐了他两天。老人们说,那是喜鹊骂人哩。
儿子画过一幅叫《七夕》的画,画中央黑压压一队喜鹊。每天他们放学时,从楼上望去,就排着这样歪歪歪斜斜的队,晃晃悠悠从校门口出来,然后一哄而散。织女穿了古装,脸蛋红扑扑的两团,是人间劳动妇女的样子。王母叉着腰,怒发冲冠的样子,头发乱乱的,不知道画的时候是不是想起了冲他大叫的女老师。他的老师生气时会罚他抄写错题一百遍。牛郎可能想不出来长什么样,于是背身立着,画了黑黑的头发。
出生在这一天的儿子,我希望他长大后喜欢的女子都喜欢他,哪怕是朴朴素素的生活,每一天都能过得活色生香。还有,就算是别离中间也不要隔着条河。
偶尔翻书,见汉武帝的生日也是七夕。为了上应天象。亦或者是纪念生日,汉武帝在长安开凿了当时最具规模的江河一昆明池。汉武帝将它想象为天上的银河,特地在河两岸雕塑了牛郎和织女像。从御林宛围猎归来的武帝,泛舟池中,偶尔也会变得温情脉脉。
更多的时候,武帝将“武”字发挥到了极致,他的爱情里,时时有军鼓轰鸣。晚年他曾宠爱钩戈夫人,立其子为太子。可是“子幼而母壮”,于是赐死。钩戈夫人,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挂在天上的月牙,越来越弯,越来越细。史载她出生时一手紧握,与武帝相遇手方能展开,手心中,是一枚月牙形的红色胎记。七夕、月牙与叫钩戈的女子,宿命般地相遇。
到了唐朝的七夕,该玄宗与杨玉环上演长安城里的爱情神话,对月盟誓,永不相离相弃。败居易录在了《长恨歌》里:“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可惜,到底还是没能遵守。同生可以,共死时,皇帝到底还是舍不得自己。盟誓,只是相爱的人在月光下做的傻事而已,有什么用呢?
尚武的汉武帝比唐玄宗更多帝王的霸气,而唐玄宗比汉武帝似乎更适合出生在温情弥慢的七夕。
宋朝婉约派的词人秦观收起小儿女情状,在《鹊桥仙》里达观起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这句诗让我想起苏东坡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时间和距离能隔断爱情吗?很久以前,有个男孩子把这句话写在信里寄给我。毕竟千里之遥,渐行渐远,所以诗里也说是“但愿”。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我知道这是怎样的豪情壮志啊。两情相悦,当然是盼望着要长相厮守的。
偶尔想起他,还是十八岁时的模样。
七夕。在银河下面忽然想起—个与河的有关的故事。
一座沉睡的小镇。河时而湍急时而平缓,岸边露出几米高的褐色山岩,寸草不生,涨水时它们会重新浸入水中。此时山岩裸露,像是等待着水流温柔地抚摸。不时跃起的鱼,画出银质的线条。青绿的山,被—条光滑的马道曲曲折折地划开,有骑马的人狂奔而来。
我姑父的妹妹嫁到了这里,她的女儿,在这里长大,我应该叫她姐的,事实上,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她。十多年前吧,那时,我还在上学。而我的姐姐,二十岁出头。她在河边长成了花骨朵,含苞欲放。
晴朗而远离酷暑,小镇有着善解人意的夏天。那时候,小镇上来的旅行者还不多。他背着个大背囊,来找住处,就住在了姐家。
他住得很悠闲,白天进山,夜晚,坐着院子里,仰着头,很久都不说话。天上,月亮圆圆地挂着。自从有他安静地坐在院子里,姐忽然听到了蟋蟀磨擦翅膀的声音。
十几年后,我也听到了这种有节奏的鸣音,夹杂在“哗哗”的流水声里,如果足够安静,就能听到。
他每天进山的时候,背着—个硕大的画夹。山谷深处,除了青山绿水,还藏着很多艳红色的石崖。他张开手臂长啸一声,吓了她一跳。
山路渐渐陡峭,很多牛粪羊粪,他担心牛和羊怎么爬得上来,她就笑了。其实这是它们每天回家的路。
他支起画架画画时,她就在一旁看。
红色山崖与天空,用一条无拘无束的线截然分开。上面遍布了无数凹凸,她指着那些凹凸说,这是一面长满鼻孔的山崖。他停住笔微笑,真像唉。
画累了,他就编童话逗她玩。说是这儿住着一个红头发的好心仙人,法术高明,历尽艰险找到仙人谷来的人,仙人就会答应他—个请求。但是你得把鼻孔送给仙人,因为仙人有着一个石头身体,所以得用很多个鼻孔同时呼吸……
他又开始画了,她去捉蝴蝶。蝴蝶忽高忽低地飞,她必须拿出所有的精神来对付它,没有网,她用帽子扣住,然后放进瓶子里。她捉了好几只颜色缤纷的蝴蝶给他看。他因为花粉过敏,连蝴蝶也不敢动的,因为蝴蝶有着一对沾满粉沫的花翅膀。他甚至连瓶子也不敢动,只是远远地隔着瓶子看。她的笑声就清脆地四散开来。
回家时,她把所有的蝴蝶都放了回去。
他终于要离开了,头一天夜里,他又坐在院子里看月亮,月亮已经日复一日缺了下去。她轻轻走到他身边,轻轻地说明年的这时候,你会来吗?你记住,你要是不来,你就再也见不到我了。他说好。然后,她轻轻地走回屋子,睡了。河水欢快地“哗哗”唱着。
她说得太轻了,轻得像没有发生过,像个梦。他答应,也就忘了。
第二年他没有来,第三年他也没有来。有一年,他忽然想起那个半个月亮的夜晚,有个花骨朵般的女子说过的那些魔咒般的话,不禁打了个冷战。
我很想说他日夜兼程地赶来,事实上,就是今天,小镇也不通夜班车。
就算是日夜兼程,他赶来的还是太晚了。她母亲告诉他,他走后的第二年夏天,有一天夜里,她跳进了门前的那条河。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追问。
她母亲不说话,转起转经轮,唵嘛呢叭弥吽……
我没有见过姐。我去的时候。她家的院子里,大丽花正忘乎所以地盛开着。
出了院子,一只黑色体形硕大的藏狗拴在树荫下,四肢松弛,正在舒服地午睡。
雨在清晨前就停了,河水涨了,却依旧清澈,哗哗地流着,或喜或忧,抑或是喜忧参半。
表姐曾经是冶木河边最灵巧的女子啊。
七夕的月亮落了,当白昼来临,天上的织女和人间的众女子要凭着一腔子激情,才能挣扎着,蹬过一个又一个满是离散的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