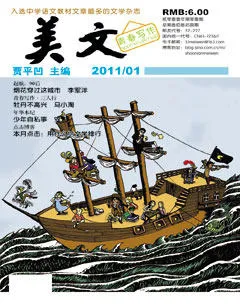闲话安安
有人柔声细气地唤他“安安”,有人咬牙切齿地叫他“鹌鹑”;有人赞他随和幽默堪为师中楷模,有人斥他忽冷忽热性情实难琢磨;有人舍弃晚饭跑到老师食堂只为一睹其芳容,有人见他便绕道而行恨不得退避三舍。这么一个众说纷纭争议颇丰的人物,似乎是应为其立本作传方妥,无奈小女子胸无潘江陆海之才,这位先生又未及不惑,以此论平生为时尚早,故敢尽拙笔,大胆对其“闲话”一番,虽寥寥数语,亦本了“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家传统,各位看官少安毋躁,且听小女子慢慢道来——
足足九年的求学生涯里,每一个夹着历史课本走上讲台的先生无不以他们那独特的外貌一遍一遍地加深着我这样的印象:教历史的先生们,非但经纶满腹博古通今,而且他们的脸就是一副效果奇佳的活教具。悠悠中华五千年的风雨沧桑往往在他们的脸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更有甚者完全可以指着自己的五官给学生讲解上古时期山顶洞人的外貌特征。鉴于以上种种认识,当这位先生踩着高一第一节历史课的铃声闪亮登场的时候,我真的很有一种“这是哪个班的语文老师走错班级了”的眩晕感。眉若远山,瞳似黑玉,再辅以那实在玲珑的身高和习惯性微驼的背,纤弱文雅的知识分子气质油然而生,讲解北京猿人是不太可能了,演绎一下金庸笔下素袍青袂的白面书生倒是形神皆备。别看他生得羸弱,气场却着实可以,在我们万分狐疑的目光的注视下,大谈特谈起西周的政治制度,以气定神闲彻底击碎我们的所有顾虑:谁说长了一张娃娃脸就不能把历史讲得风生水起?
可以说,他的到来彻底粉碎了部分同学妄想从初中一直延续到高中的历史课美梦。据不完全统计,除去个别复习课外,该先生几乎就没有在讲台上老老实实地呆过十分钟。上课铃响,他走上讲台,敲一下鼠标打开课件,便走下讲台,在教室里的两条走廊之间转来转去,一只手习惯性地整理着外套的衣领(当然,夏天除外),另一只手则颇有力度地在空中挥舞作指点江山状。一节内容终了,他旋风般转身冲上讲台敲一下鼠标,随即又匆匆走下讲台开始他那似乎永远不会结束的游走,足足四十五分钟不歇脚,完完全全的乐此不疲。
这样一来,教室里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在他的如此亲身探访下被尽收眼底,若是还有胆大包天者敢与其打游击,该先生还有一招杀手锏——若是你数学功底不算好,数到200以上的数字就犯晕的话,千万不要妄图统计他每节课说“是不是”的次数,因为他每讲数十字,其后必跟一“是不是?”若是教室内响应之声不甚热烈,他便挑眉扬声:“哎,是不是啊?”必得全教室之人亮开喉咙齐声高呼“是——”他方满意一笑,在从睡梦中被吵醒的同学怨恨的目光里,施施然地继续着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
该先生讲课另有一显著特点,那就是板书基本不见踪影,只有幻灯片一统天下。师生一月,几乎未见他在黑板上写一个汉字,偶尔不得已要板书,也只有数字独挑大梁,其余的一律用三角圆圈之流代替。起初我们认为是东西太多写起来麻烦,可后来历史课代表无意中拿了张他做过的历史卷子过来,谜底才算是真正水落石出:该先生虽然长得像个书生,下笔却全无书生气质,真迹犹如电灯泡内细细长长的钨丝,即使用明文写密报被截获也绝对不会被认出。有生调皮,带了卷子去找他,奚落的话还未出口,他便忙不迭地把卷子抢回手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折叠起来,红脸讷讷道:“XX真是,我明明叫她拿答案过去,居然把我的卷子拿走……”虽然证据被他收走,但“历史老师写字比我们还难看”的新闻在我们班却着实沸沸扬扬了一阵子,以至于日后再看他在黑板上鬼画符众生便忍不住交头接耳,掩口窃笑。
说到笑,该先生在高一级部可谓是声名远扬,本班一女生曾对其有“一笑倾城,二笑倾国,三笑倾我心”的极高评价。一般人笑则笑矣,而他的笑却分外与众不同:左边嘴角首先翘起一丝可疑的弧度,随即右边嘴角将扬出一抹近乎完美的笑意,眸底若流星耀眼璀璨,笑容极是干净澄澈,有种孩子般的清透纯真。该笑如此,却并不是千金难求,上镜率之高令人咋舌:在走廊里向他打招呼的时候会出现,上课讲到兴起时会出现,甚至某日课上到一半,走廊里那个喋喋不休的家伙突然消音,引众人诧异地抬头,却见他自顾自地笑得灿烂。有胆大者高声问:“老师,你笑什么?”他笑意却丝毫不减,低眉轻声:“笑还不让啊……”言语间皓齿微露,珍珠般温润迷人。
本以为像这样文弱随和的先生不是块当班主任的材料,可没想到他统治的二四班和我们班仅有一墙之隔。于是每日早读时分,我睡眼惺忪地从走廊里穿过,其他的教室里都是松松散散人还没到齐一半,唯有二四班已经座无虚席,他端坐于书声琅琅之上,颇有种秦始皇睥睨天下的威仪,治班之严可见一斑。据说二四班的政治体制颇像19世纪的德国,对外宣称民主共和,对内却是独裁专治,非身临其境不可体会。于是你在走廊里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对话:“呀!你是二四班的,有安安做班主任,真是太幸福了!”“什么啊,那鹌鹑有什么好,分在他班里,简直就是倒了八辈子的霉!”
鉴于他的粉丝实在太多,所以他的个人隐私估计是被弟子们挖得最为彻底的一个,爱称、外号之类的东西更是以每天数个的速度更新,连网络语言的更新换代速度都自叹不如。曾经有个别胳膊肘向外拐的实在厉害的家伙,在走廊里问他想不想知道我们私下里都叫他什么。当那些颇具语不惊人死不休气质的外号被一一说出的时候,方才还沉稳笃定的先生的脸开始无法抑制地向西红柿靠拢,最终一边摇头说着“你们这些人啊……”一边转身落荒而逃,去的却分明是自己刚刚来的那个方向。
疯狂的暑假过后,新学期一切翻新,二二班变成了理科班,班主任被换掉,副班主任被换掉,不少读文科的同学纷纷离去,一切都新得那么刺眼而陌生。所以在得知他依旧教我们历史的时候,被离愁别绪笼罩了数日的同学们私下里很是激动了一下。然而新学期的第一节历史课,却因为种种原因被化学吞并,于是乎班里怨声载道,新来的化学老师人没露面,形象已减三分。期待了整整两天之后,当这个书生模样的老师再次出现在教室门口,一瞬间真的有种想鼓掌的冲动,他的走姿,他的笑容,他的口头禅,此时想来竟是如此的亲切而难以忘怀。
有次上课的闲暇,他告诉我们说在大学里历史是公共课,可以随便去听,当时我们班全体嗤之以鼻,心想有谁好容易熬到大学还去听这么让人打瞌睡的课。其实现在想来,去听听也不错,也许会在“中国近代交通运输业发展”那里想起那个改编《情深深雨蒙蒙》帮我们记各种发明的人;也许会在“全球化浪潮”那里想起那个用“麦兜的一天”的漫画讲解全球化作用的人;在昏昏欲睡的间隙里想起那个在教室里转来转去并一刻不停地说着“是不是”的人。
他是“安安”,他也是“鹌鹑”;你可以说他随和幽默堪为师中楷模,也可以说他忽冷忽热性情实难琢磨;你可以舍弃晚饭跑到老师食堂只为一睹其芳容,也可以见他便绕道而行恨不得退避三舍。无论如何,这些都黯淡不了他在我们这些弟子心中应该有的形象。闲话至此,百感交集,小女子无才作结,便特邀二四班班长一表心声:
“我总结不出来,但他是一个为学生好,却不放在嘴上的好老师,他为我们班同学做了很多事,但是他从来不说。我们班没有副班主任,他比别的班主任累,二四班是他自己带出来的,结果,到了高二,不让他教了,历史也不让他教了,这样,他还让我好好配合新班主任工作……安安,我想对你说,虽然很多人都只记得你训斥学生的场景,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们会记起你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