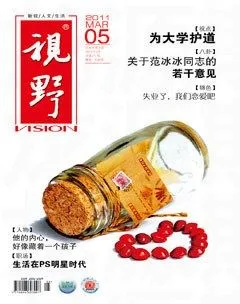咱们就是平等的
一
我说过,我当年做记者,起因是因为赵铁林。
在学校图书馆处理废旧杂志的地方,看到一期《光与影》,封面就是这张照片,皮儿都快掉了。我看完这组拍16岁妓女的片子,吓了一跳,就给这杂志写了篇文章,算是评论。
主编到北京来找我,扫视了一眼我的破宿舍,说“我们的北京记者站就设在这儿了”。我说行,惟一的条件就是让我跟这个拍照的赵铁林合作一次。
等我在孤独症儿童治疗中心见到老赵,我很意外。那年他五十了吧,长得挺糙挺壮,我没想过这样的照片是这个年纪的人拍的。我要采访的是个日本回来的妈妈,一个人带着孩子,她不理我,但让他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拍完就要走,我眼巴巴地看着他,他说了一句“想拍弱者,就要让弱者同情你”。我不理解他的话,只能等在人家门外,帘子下着,我什么也看不见,闻见她做饭,听见她和孩子吃饭,天黑透了,我就那么站着。
小孩子出来玩,下台阶歪一下,我下意识扶一下,跟他在院子里玩。
过一会儿她出来,牵条狗。“我去散步,你也一起吧。”算是完成了这次采访。
二
赵铁林对我解释过这个同情:“我当时比这些小姐还穷,她们可怜我,让我拍她们。”他其实是北航的毕业生,原来在北京的计算机所任一个副职,做生意失败,穷得要死,租的地方就是她们住的地方。他说过一开始还有那种不得志的文人劲儿,找个“李香君”或者“杜十娘”之类的识货的人,满足他救风尘的愿望,后来才发现“根本没那回事儿”。他老老实实地开始给她们拍“美人照”,一张二十块钱,养活自己,就是这么开始的。
有人认为他的照片“伤害”了她们,或者在“关怀”她们,老赵说“无所谓伤害也谈不上关怀”,就是平等。“当她们认为你也是在为生存而挣扎的时候,咱们就是平等的了。”
三
这种题材有很多人拍。
老赵说过,要么就是一脚踹开门的拍法,或是给钱给她们,拍的照片用来消费。还有一种是在画册上常见的,以居高临下的角度去拍,觉得“她们是弱势群体”。摄影师并不露面,但你可以从他的照片里清清楚楚地看见轻蔑或者怜悯——两者背后有个相似的东西,都是优越感。
我赞成他的话,但是我觉得,一个题材怕得并不是过度,怕的是单一。
在当年那篇文章里我写“她的目光一下一下打在我的身上,让我感到疼痛的亲切”。
四
我做记者十年,才正学着从常常会有的道德评判和政治正确中尽力脱身,去试图观察,只是观察。但赵铁林压根连这个姿态都没有。“我和她们交往,拍她们,并且告诉她们我的目的,这对她们来说就是对她们的尊重,她们知道我不会扭曲她们。”
当年他给过我一张名片,名字上有一个黑框。别人问,他就笑“我死过很多次了”。他说“生死寻常之事”。
我们后来再没有联系,一直到前天朋友说起,才知道他一年前已经去世,我半天说不出话来。
我在网上看到他去世前的照片,看到他被折磨的样子,心里不能平静。
但写下这篇文章,并非要唏嘘他的命运。
他像他拍摄的人一样,承受命运施加于身的一切,并不粉饰和夸张,也不需要怜悯或者虚浮的敬意。
十年前在那篇文章里,我写过他的照片向我揭示的真理:生和死,苦难和苍老,都蕴涵在每一个人的体内,总有一天我们会与之遭逢。“我们将浑然难分,像水溶于水中。”
(毛俊瑞摘自“天涯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