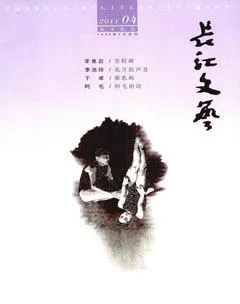为了不能遗忘的遗产
水果湖的高知楼要拆了,连同它所在的小院。因为六湖连通的宏伟蓝图,因为东湖要与沙湖贯通。而靠近这个区域的建筑就都要寿终正寝了。这座楼和这座小院,原本是湖北文艺家聚集的文脉之地,许多重量级的作家、文艺家都曾居住在这里,像徐迟、碧野、吴丈蜀,等等……去年夏天,徐迟的女儿徐音带着法国的金融家丈夫回汉休假,想与几位老熟人聚一聚。方方主席善解人意,专门在八一路湖锦酒店设宴款待,也把我叫去了。席间,徐音谈及父亲书房里留下的近千套书籍、曾写过许多名篇的电脑以及接待过很多作家、朋友的沙发、茶几等,拆迁后往哪里搬。她问,组织上能不能设一个专馆把它们保存起来。闲谈间流露出几分伤感和担忧,又有几分期待和冀盼。
这座楼和这座小院,南接水果湖,东眺双湖桥,院子不大,20多亩地,虽说算不上设计精美、布局典雅的名园,但颇具幽静清雅之气。院中栽满桂花树和冬青树,入秋有丹桂飘香,冬季则依然郁郁葱葱。曾是我常去的地方。我和徐迟先生算是忘年交,这座小院和徐老的家也是我常去的地方。一提到这座楼,在我脑海里浮现出的,便是那轮金秋的夕阳,它的余晖洒落在这座院落,也洒落在徐老的书桌上……
一
记得第一次走进徐老的家,正是1985年的金秋时节。我当时是武汉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筹备组的成员,按邓朴方主席的要求,各省会城市要成立基金会,武汉市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自然也要先行先试。我建议推选徐迟为名誉理事,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因为是我推荐的文化名人,所以联络工作也落在我身上。我到徐老家时,得知他前列腺开刀不久,还在家康复。那时徐老的身体还很虚弱,但目光很慈祥,微笑的嘴唇像一个月牙儿。那天,他穿着花格子衬衣,很有风度。他细心地听着我的讲述,眉宇间是那样的俊朗。我说,我读了您的《哥德巴赫猜想》之后就萌发出拜见您的想法,今天梦想成真了。然后连续背诵几段《猜想》里的精彩文句,譬如“四大家族”、“红楼一梦”、“数学家的逻辑比钢铁还硬”,等等,最后说明了聘请他担任名誉理事的来意。他问道,你是做福利工作的?我看得出来,他的内心有一个疑问:你怎么像一个文学小青年。思忖片刻,他终于答应出任基金会的名誉理事。我非常高兴地连跑带跳下到一楼,骑着自行车离开小院。打那以后,文化助残的活动就越来越多了,残联与文联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了。
1990年8月,武汉市残联举办首届全国残疾人长江笔会,史光柱、刘琦、谢涵等20多位残疾人作家将从武汉乘船驶向重庆,在万里长江上畅文抒怀。这是武汉残疾人事业的一次创举。我邀请了徐迟、曾卓、方方、肖复兴等作家出席开幕式,按照会务安排,我要去接徐老到会。于是,又一次走进水果湖这座小院,径直上了二楼,敲开徐老家的门。要出门时,徐老忽然说,永泽你等等,我换件衣服。当他换上一件天蓝色的T恤重又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惊呆了,说,您太帅气了。内心却想,为什么徐老非要换上一件这么靓丽的服饰呢,仅仅是体现诗人气质吗?
那天,徐老在汉口滨江饭店顶层望江厅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辞,“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司马迁遭宫刑才有史记。身体的残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心灵的残缺,你们遇挫而不馁,你们是完美的残疾人。”他接着又说,要读书,人不读书就会变成野兽……语毕,掌声四起。显然,与会代表都被他掷地有声的人生感悟和隽永睿智的演讲所打动,所折服,也被他弥漫着青春气息的诗人气质所感染。哦,此刻我才明白,他的讲演,是从内心到语言、从智慧到仪表的全方位的讲演。因为在他的心里,讲演的对象是最值得尊重的一群特殊的朋友。
二
1991年10月,浙江湖州南浔中学举行校庆活动,邀请1948年曾在学校执教的徐迟回家乡和母校,并为他祝寿。我为此做了一个策划,以湖北电视台和银河影视公司的名义为徐老拍一部传记艺术片,最初起名为《故园之恋》。我担任撰稿和制片人,拍摄小组要随同徐老回南浔家乡。我因此驱车来到水果湖的这座小院,又一次在徐老的客厅向他报告拍摄的创意:以故乡行为契机,分三个阶段展示他一生追梦、圆梦的心路历程。徐老和我边喝咖啡边聊天,徐老讲起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往事。1945年毛主席赴重庆谈判时,徐迟在《新华日报》发表了一首《颂歌》:“毛泽东,毛泽东,我一生的光荣,是能够给你颂扬,金鸡样,高亢、嘹亮……”在国统区中,他成为第一个公开发表诗歌赞颂毛主席的人;当毛泽东会见重庆文艺界代表时,徐迟拿了一本精美的册页请毛主席赠言题词。几天后毛主席欣然命笔题写了那句十分有名的“诗言志”……这段耳熟能详的往事,在文艺界传为佳话。而这个题词后来成为新中国诗歌创作的指南。在蒸腾的香气里,咖啡又续了一杯,徐老又谈到文气优雅的冰心老师1931年在燕京大学开设了一门名为“诗”的课程,用英语讲述外国诗歌经典的一些故事。那天晚上徐老的讲述,后来都被我写进了专题片。
那年10月中旬,我带着摄制组陪同76岁高龄的徐老一道回南浔家乡。记得庆典活动当天,徐老穿上一套蓝色西服,扎着枣红的领带,精神矍铄地走上讲台,对济济一堂的三代学子说:“居里夫人说过,把太阳拿过来,然后扔出去,最后把扔出去的太阳拿过来放好。近五十年的风云,我们又相聚了……”他就是这样的出语不凡,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我顿时受到启发,把专题片的片名改为《把太阳拿过来》。南浔拍摄后,我又北上专程到冰心家中采访老人。那天,冰心老人满脸笑容地说,你们是湖北来的吗?给我在本上留一个地址。然后指着墙上倒写的“福”说,这是赵朴初先生题的“福”字,今天是福到家了。谈起对徐迟的印象,老人说,他是一个好学生,才华出众,富有创意,他当年编辑的一本刊名为《旷野》的作业,我给他打了一个优。你们回去代我向他问个好。
“有个梦诞生在摇篮里,做了很长很长;有个谜跋涉在风雨中,猜了很久很久。把太阳拿过来,燃烧了真诚的诗情……”1992年,徐迟传记艺术片《把太阳拿过来》在全国近50个地方电视台播出,赢得了观众的广泛赞誉。湖北电视台著名编导黄益凑告诉我,这是当年电视台最受欢迎的节目。
三
1996年5月到10月,武汉市正筹办第三届“中国武汉国际杂技艺术节”,俄罗斯、加拿大、法国、德国等十几个国家或地区将派团来汉参加角逐,党和国家领导人李鹏、刘华清等为艺术节题了词;中国文联副主席、时任中国杂协主席夏菊花担任组委会主席。时任武汉市副市长的陈华芳、副秘书长罗友松委托我牵头,为杂技节编撰宣传纪念册,以彰显武汉杂技艺术,我便想请徐迟、曾卓、方方、夏雨田、池莉等几位作家撰写短文。这个念头一萌生,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到徐老家跟他聊聊,听听他的意见。
5月上旬,徐老刚从北京返回水果湖的这座小院。他在京期间,《哥德巴赫猜想》的主人公、著名数学家陈景润因病逝世,北京电视台为此专门采访了徐老。《猜想》文中的主人公英年早逝,无疑给徐老带来了巨大的感伤。徐老是一位非常珍视情感、重视人才的人。我见到徐老时,他的神情露出了几分悲哀、几分眷念。当年,正是因为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描绘了陈景润这样的科学家形象,引来了科学的春天这般繁花似锦的景象。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念已成为民族共识,当畸形的人才观已被唾弃,那位在数学王国探峰觅险、摘取数学王冠上的明珠的数学家却离我们远去……这,怎能不引起徐老心灵的震颤!
这次在他家中,不是喝咖啡而是喝绿茶,是他家乡带来的西湖龙井。交谈中,我为两件事征求徐老的意见,一是请他为武汉市残联“济世之家”书画义卖活动写幅书法作品,书写内容是《猜想》中抒情华彩段的节选;二是请他为杂技节写篇杂技赋。尽管身体十分疲惫,徐老仍然爽快地答应了。因为他把公益文化活动视为作家的职责和担当。这样的胸襟和情怀,足以让当今大搞“唯钱是举”的所谓文化名流所汗颜。没过几天,徐老便通知我到家里取作品。他写了两幅四尺的长卷书法作品,气韵生动,行云流水,章法自然,错落有致。一幅义卖款为两万多元,用于残疾人公益设施建设。而另一幅悬挂在武汉济世书画社的厅堂里。1999年徐老辞世三周年之际,我们将它转赠湖州南浔徐迟纪念馆永久珍藏。而徐老写的杂技赋,在纪念册上一经刊载,便为人们击掌称妙,叹为观止。现将全文敬录如下,以飨读者:
挑战美的极限
——杂技赋
徐 迟
什么是完美的点、线、面?星星是完美的点;陨星是完美的直线;娥眉月是弯弯的、纤细的曲线;一个个的星座、星云,和扫帚星,和中秋月,是完美的面。怎样是完美的天体?都是扁、匀、圆的;太阳系、银河系、河外系,所有的天体都是一只只的盘,一只只的碗。她顶着碗,是的,顶着叠了起来的天体,十个盘就是一个天庭,一千个河。她是一只神奇的金凤凰,众鸟绕着她歌唱,他们踊跃旋转,跳剑飞丸,俯仰逍遥,连绵九仞,离合驰骋,孔雀开屏,花团锦明,逆着长空而翔舞,旋转一千零八十度,显逸才之敏武,似失重之模拟。方凌空坠落兮举手相招,急惊险万状兮笑容双手来迎。椅子椅子兮联成了一串长行,一行白鹭兮冲上青天。人体呵,眼睛呵,肌肉呵,自是力的不竭的泉源!均匀呵,平衡呵,轻盈呵,是美的保证。我们是红尘中的凡夫俗子,我们没有见过仙界的神仙,然而我们却见到了人类中的挑战者,规定了没有人能做到的极限,就向它们冲击与挑战。一个个不可能突破的极限竟被突破了,就把那极限再提高,他们就这样上升,赫严严兮至于世界之绝顶!这就是我们武汉市的杂技艺术。为作杂技赋。
这是可与泰戈尔、雪莱等大师媲美的神来之笔,这是饱含楚文化神韵的瑰丽浪漫的锦绣诗篇,这是当代词赋的经典华章。这也是徐老在世的最后一篇散文诗。
1996年12月13日,徐迟先生在汉辞世,他带着挑战文学、挑战美的极限的梦想和信念,奔向天宇,与星光同辉。
他走了,他留给我们什么?
他是现当代中国诗坛风格独具的诗人,他是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开山者。《哥德巴赫猜想》、《生命之树常绿》、《在湍急的漩涡》、《地质之光》等报告文学,报晓了科学的春天。他在外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上具有卓越的贡献,所翻译的《瓦尔登湖》一开新文学译著的风范。他也是文艺鄂军的领军人物之一,是荆楚文化的一张闪亮的名片。
徐迟留给了我们一笔厚重的文化遗产。文化遗产,词典上说,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保护文化名人的文化遗产,是科学发展、和谐社会赋予我们的职责,也是城市文化建设彰显软实力的重要任务。
去年10月,我有幸随中国文艺家代表团访问巴黎和阿姆斯特丹,同法国文人协会、荷兰对外文化交流中心的同行进行友好交流。法国文学家协会会长介绍说,这个协会原址是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后来整体搬迁到郊外。雨果、大仲马都是协会的前任会长,建筑可以改装,文脉应该长流。在协会的大厅里,陈列着雕塑家罗丹雕塑的巴尔扎克塑像,会议室摆设着十几任会长的肖像壁挂。岁月虽然流逝,星光依然闪烁。而在阿姆斯特丹城区的梵高艺术馆,门前永远是人头攒动,访客络绎。梵高生前所画《麦田上空的乌鸦》等200幅原作,吸引着世界各国的游客,也成为荷兰人骄傲的名片。
从法国回来,我就参加了潜江第二届曹禺文化周活动。潜江市政府同中国文联、中国剧协共建“梅苑”暨曹禺剧本创作基地、中国剧协“梅花奖”交流中心、曹禺大剧院等项目。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文联主席孙家正为曹禺大剧院题名,并参加奠基仪式。江汉平原的一颗明珠——潜江,因曹禺戏剧文化的彰显而熠熠生辉。著名剧作家魏明伦感叹道,中国文学家得到像曹禺这样的礼遇是罕见的。
从潜江返回武汉,我再次路过水果湖高知楼。我久久地、深情地望着它。也许,这座小院将被新的景观和建筑所代替;也许,那些诞生过许多艺术精品的创作空间不复存在。但这座城市的文化艺术遗产一定要设法保留和传承,那些象征着城市的眼睛、城市的名片的艺术精神一定要珍藏。或许,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好的做法和外地好的经验,将城市的规划建设和文化遗产的保护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正如六湖要连通,历史文脉更要连通。或许,在楚河汉界般的城市公园的环境中,将文化名人的故居、纪念馆、艺术馆、陈列馆有机地规划其中,让人文的美不致流失,自然美便会更富于内涵。令人欣喜的是,在编制全省文艺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时,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批示,要将兴建荆楚文苑(湖北文艺家之家)的项目纳入“十二五”规划,以进一步推动湖北文艺大繁荣大发展。
徐老,您听见了吗?
责任编辑 易 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