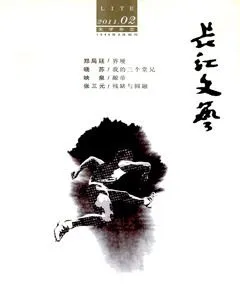残缺与圆融
在襄阳与诸葛亮毗邻而居,算起来,有整整21年。应该说,我与诸葛亮算是故交了,尽管我们相隔1700多年。时间不是距离,只要心有灵犀,照样神交。我与米芾、孟浩然都成为好友,便是证明。奇怪的是,我与诸葛亮一直相处淡漠,古隆中虽去过几回,但一直感到陌生。当然,那是快10年前的事了。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来到襄阳。初来乍到,兴冲冲地游过两回古隆中。之后,便去得少了,有数的几回都是陪客人去的。相反,对襄阳几处比古隆中名气小得多的景点,如鹿门山、米公祠、水镜庄等,我却去了一回又一回。是古隆中的景色不美?不是的。《三国演义》第37回写道:“行数里,勒马回观隆中景物,果然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广而平坦,林不大而茂密;猿鹤相亲,松篁交翠……”这是初冬的古隆中。真正到了冬天,古隆中的景致则别有洞天:“时值隆冬,天气严寒,彤云密布。行无数里,忽然朔风凛凛,瑞雪霏霏,山如玉簇,林似银妆。”冬天的景色尚且如此,古隆中春、夏、秋的景象便可想而知了,圆融丰满,万物滋长,欣欣向荣。这样的景致,即使不是绝无仅有,想必天下也不会多。是古隆中没有内涵?也不是的。古隆中是诸葛亮躬耕之地,是诸葛亮刻苦磨砺后一飞冲天的地方。三顾茅庐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古柏亭,野云庵,三顾堂,躬耕田,梁父岩,半月溪,六角井,小虹桥,一步一景,一步一个故事,一步一个传说。人文胜景,和谐统一。按说,这样的地方对我有足够的吸引力。但从一开始,我就与古隆中保持着距离。其实,我好想一次又一次地走进去,好好端详,细细品咂。
作家梁衡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历史上有无数个名人,但没有谁能像诸葛亮这样引起人们长久不衰的怀念。其实,何止是怀念,简直是膜拜。三国人物中,有两个人的身影长期遮蔽着人们心灵的视野,一个是关羽,另一个便是诸葛亮。关羽忠义,诸葛亮智慧。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与忠义比较起来,智慧等而下之。因此,供奉关羽的是庙,诸葛亮容身的地方则是祠。庙里敬的是神,祠里纪念的是人。在世界各地,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几乎都有关公庙或曰关帝庙,丝丝缕缕的香火燃烧了一千多年,而且还会燃烧下去。武侯祠也有不少,但毕竟是祠,与庙相比,少了些许香火气。既然是人,就得食人间烟火,就有七情六欲。但历经一千多年的演绎转化,诸葛亮成了一个完人,智慧大海般深邃,品德泰山般巍峨。太完美了,完美得使人不敢正视。这种完美,使我与诸葛亮之间产生了距离。每当仰望诸葛亮的时候,我都有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白居易说过,大成不能无小弊,大美不能无小疵。完美得连小疵都没有,那还是人吗?不是的,是神。是的,诸葛亮被人们神化了!作为神的诸葛亮,高居于人们心灵的视野之上。在电视剧《三国演义》和《三国》中,诸葛亮是神,又近妖。对神,我只能敬而远之。
我曾试图走近诸葛亮。诸葛亮在襄阳生活了14年,其中有10年耕读在古隆中。古隆中是襄阳的后花园,襄阳是诸葛亮的纪念碑。作为一个所谓的文人,居住在襄阳,而不能与诸葛亮成为朋友,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但我是一个有缺点的人,有很多的缺点,怎么能做诸葛亮的朋友呢。小草欲与大树试比高,纯属徒劳。我常想,如果诸葛亮像我一样,有这样那样的毛病,性情相近,臭味相投,我们一定会成为朋友的。所以,我每回想走近诸葛亮的尝试,都以失败而告终。
朋友问我,孟浩然有没有写过古隆中和诸葛亮的诗?我犹豫了一下,但还是肯定地说,没有。回家一查,果然没有。我认识孟浩然,就是因为他的诗。我熟悉孟浩然的诗,就像孟浩然熟悉襄阳山水。朋友又问:为什么呢?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孟浩然是地地道道的襄阳人,热爱襄阳,他也想像诸葛亮一样,从鹿门山起飞,展鸿鹄之志,但他没有诸葛亮那样幸运,一回一回地铩羽而归。但襄阳还是孟浩然的襄阳,孟浩然还是襄阳的孟浩然。孟浩然长期隐居在鹿门山,徜徉于襄阳山水之间,对襄阳山水爱得痴狂,岘山、鹿门山、望楚山等都以清丽的姿影进入了他的诗篇。孟浩然怎么独独忽略了山清水秀而又有“诸葛亮故居”招牌的古隆中呢?孟浩然常常登山怀古,凭吊先贤,“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勤政的羊祜,好名的杜预,孟浩然反复吟之咏之。难道孟浩然的眼中独独没有诸葛亮?是诸葛亮不贤,还是诸葛亮不才,抑或是孟浩然有眼无珠?朋友猜测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唐时诸葛亮的名气还不够大,二是孟浩然自恃有才,对诸葛亮之才不以为然,厌屋及乌。对此,我未置可否,一笑置之。我想,有一点是不能忽略的,那就是在唐朝,人们可不愿把诸葛亮当神供着。唐朝自由的空气,使人看到了人的尊严与高大。孟浩然的诗中,可以为羊祜、杜预等人留下宽庭阔院,却不能有神的立锥之地。把诸葛亮当做神,诸葛亮是走不进人的心中的。
诸葛亮只是一个传说!
那好,那就把诸葛亮请下神坛吧。当走下神坛的诸葛亮,第一回以人的姿态走进我心的房间时,我已经离开了襄阳。离开襄阳,有幸运,也有无奈。说幸运吧。离开襄阳后,我和诸葛亮的地理距离远了,心理距离却近了。我终于从神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可以平等地打量诸葛亮了。平等是一缕阳光。阳光溢满我的心房。在阳光中,诸葛亮还原为一个真实的人了。阳光使诸葛亮身上的残缺暴露无遗。当我第一回看到诸葛亮身上的残缺时,诸葛亮就以人的姿态走进我心的房间了。
于是,在广袤的时空中,以淡泊而宁静的心态,我从容地欣赏诸葛亮的残缺,对,是欣赏。
在人们的心目中,诸葛亮有一身读书人的清高傲气,一朵莲花亭亭玉立于污泥之中,清香四溢。其实不然,诸葛亮绝不是一朵亭亭玉立的莲花,充其量是一朵狗尾巴花。诸葛亮曾与襄阳的地痞流氓打得火热,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诸葛亮到襄阳来投靠的是谁?是刘表。刘表是典型的地痞加流氓,政治流氓。刘表不是襄阳人,但在襄阳混的时间长,无异于襄阳土著,说是地痞一点也不为过。地痞流氓,三教九流,豪强大族,刘表尽数纳入彀中。无论是白道,还是黑道,刘表都是襄阳理所当然的老大。在小说《三国演义》中,刘表也是一个不太光彩的角色,当面仁义,背后使绊,小人一个。而诸葛亮恰恰是在刘表的庇护下长大的。更重要的是,蔡瑁是诸葛亮妻子的舅舅,刘表是诸葛亮妻子的姨父,蒯棋和庞德公之子庞山民是诸葛亮的姐夫。蔡氏和蒯氏是襄阳地痞流氓的头子。就说蔡氏吧。蔡氏有数十处田庄,数百名婢妾,还有强大的私人武装,有奶便是娘,十足的地痞。刘表在襄阳站住脚跟,是蔡氏的功劳;曹操攻进襄阳,又是蔡氏箪食壶浆相迎。有刘氏、蔡氏和蒯氏撑腰,诸葛亮呼风唤雨,跺一下脚,襄阳不抖一下也难。在出山以前,诸葛亮长期与这些地痞流氓为伍。说得好听点,是诸葛亮心胸开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说得难听点,是诸葛亮为达到个人目的左右逢迎、投机钻营、拉帮结派。因此,论出身,诸葛亮的身上是有污点的。有人会说,诸葛亮出污泥而不染。也许是的,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诸葛亮的根子长期扎在污泥里,难免有同流合污的嫌疑。不翻老账便罢,一翻老账,就是问题。如果再来一回“文革”,诸葛亮就是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
俗话说,良禽择木而栖。凭诸葛亮的智慧,他知道哪棵树是自己的归宿。在一般人看来,诸葛亮栖落的树依次应该是:曹操,孙权,刘备。但诸葛亮既没取其上,也未取其中,而独取其下。曹操雄才大略,一代枭雄,手下人才济济,天下尽在掌握之中,太强大了。诸葛亮知道,投奔曹操是最危险的,危险就在于自己恐怕永无出头之日。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诸葛亮的狡黠。投奔孙权呢?那也不行。孙权是孙武的后代。《孙子兵法》的光芒与日月同辉。诸葛亮虽然自视甚高,但还是有自知之明的,他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遮蔽不了《孙子兵法》的光芒。在这一点上,诸葛亮是明智的。那么,剩下的便只有刘备了。在诸葛亮看来,投奔刘备是最安全的。虽然曹操对刘备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但那只不过是一句戏言,个中的挖苦与讽刺意味,想必连刘备都体会得到。刘备既无雄才,也无大略,只会挤几滴不咸不淡的眼泪,手下更是无人,只有关羽、张飞和赵云算是个人才,但都是匹夫之勇。诸葛亮知道,凭自己多年与襄阳地痞流氓打交道的经验,摆平关、张、赵等人简直是小菜一碟。于是,诸葛亮在隆中卧龙岗上端起了架子,姜太公钓鱼,单等刘备上钩。诸葛亮知道,刘备一定会上钩的。不像曹操和孙权,刘备没有端架子的资本。果然,刘备上钩了。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才好像极不情愿地出了山,其实,他的内心欢喜得很。因此,诸葛亮出山的动机值得怀疑,诸葛亮对刘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态度也需要去伪存真。诸葛亮心中想的全是他自己。说到底,诸葛亮的高尚值得打个问号。但诸葛亮太狡黠,做得滴水不漏,连《三国志》的作者陈寿都差点被他骗了。这是诸葛亮的成功,也是诸葛亮的失败。如果诸葛亮不在乎自己的利益,不顾惜自己的名声,顺应历史潮流,辅佐曹操,他的人生恐怕是另一番景象,中国历史恐怕也是另一个样子。小小的残缺,导致了莫大的遗憾。
诸葛亮娶妻阿丑,郎才女貌,琴瑟和鸣,堪称楷模。其实,这是牵强附会,乱点鸳鸯谱。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诸葛亮的婚姻是不幸的,甚至是不道德的。诸葛亮没有爱情。这可不是乱说。《三国志•诸葛亮传》引《襄阳记》说:“黄承彦者,高爽开列,为沔南名士。谓诸葛孔明曰:‘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许,即载送之,时人以为笑乐。乡里为之谚曰:‘莫作孔明择妇,止得阿承丑女。’”尽管这是一条孤证,但足以证明,在襄阳流传了一千多年的孔明择妇重才不重貌的佳话,纯属谬传。黄承彦是何许人也?黄承彦是蔡瑁的姐夫,刘表的连襟。黄承彦说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诸葛亮,诸葛亮敢说半个“不”字?这等好事,诸葛亮谢都谢不及呢。阿丑,名字丑,人更丑,黄发黑肤。如果在今天,是前卫,是时髦,但在当时,纯粹是丑。阿丑的丑,是不用怀疑的,连黄承彦都承认了,肯定不是一般的丑。至于阿丑有才,就更值得打个问号了。阿丑有什么才?相传,木牛流马是她的杰作。这纯属张冠李戴。阿丑出身大户人家,是不屑做机巧之事的。阿丑顶多会点女红,会写几首诗,就像《红楼梦》里的林黛玉。但想想看,如果林黛玉黄发黑肤,贾宝玉会爱她爱得一塌糊涂吗?诸葛亮是不会爱阿丑的。诸葛亮才貌双全,风流倜傥,爱他的女子自然不在少数。诸葛亮饱读诗书,其中,描写才子佳人的书肯定不少。几千年来,才子配佳人,是一条不变的定律。诸葛亮是跳不出这个圈子的。按说,有刘表这层关系,襄阳的佳人还不是由着诸葛亮来挑。但诸葛亮没有这个权利。诸葛亮不能爱自己所爱的人。诸葛亮这条卧龙,得驭风而起。这“风”,便是刘、蔡、蒯等人的支持。这种成功的案例,在今天,仍然比比皆是。为了政治和自己的前途,诸葛亮牺牲了爱情。诸葛亮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诸葛亮娶阿丑,对于阿丑来说,是不道德的,因为诸葛亮不爱阿丑;对于诸葛亮自己来说,也是不道德的,因为他不爱阿丑。但诸葛亮别无选择。
这些还只是诸葛亮没有离开隆中时的残缺。而且,这些还只是诸葛亮没有离开隆中时身上残缺的一部分。离开隆中后,诸葛亮还有更多的残缺。生活中的诸葛亮,本来就是有残缺的。
其实,《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早就看到了诸葛亮身上的残缺。陈寿在总结诸葛亮的一生时说:“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无数小的残缺,终于铸成了一个大的残缺。盖棺论定,诸葛亮的人生是有残缺的人生。
诸葛亮不再是一个传说!
但诸葛亮的残缺是人的残缺。有残缺的人,就像田野里的小草,尽管弱小,却拥有整个太阳。其实,这种残缺,何尝不是一种圆融。
残缺似乎是对圆融的破坏。但细细一想,并不尽然。残缺是圆融的前提,或者说,圆融是有残缺的圆融。北京的天坛,是圆融的典范,但它是人们祈天的场所,这就是一种残缺。其实,圆融是美,残缺也是美,二者相映生辉。就像有月盈就必有月亏一样。月盈则亏,月亏则盈。月盈是圆融的美,月亏则是残缺的美。一弯银月,似嫦娥的柳眉,美得自然,美得妩媚,美得生动。我们常常惊叹维纳斯的美。维纳斯的美,其实是一种有残缺的美,是美的极致。不敢想象,接上断臂后的维纳斯,会带给我们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是残缺,还是圆融?大到历史、人生,小到花草、树木、蝼蚁,都有残缺,也都有圆融。春花烂漫,可谓圆融吧,但花都要凋谢。落红是一种美,一种凄绝的美。秋天的田野,硕果累累,可谓圆融吧,但秋收过后,田野显得空旷寂寥,丑陋不堪。厚厚的冬雪下面,生命流转,可谓圆融吧,但冬雪又扼杀了多少生命。《庄子》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泽雉的故事。泽雉,一种生活在草泽中的小鸟,“十步一啄,百步一饮”,生活中,到处都是残缺。但泽雉追求天赋自由,拥有一个完整的世界。这就是圆融。人生也是如此,没有绝对的圆融,也没有绝对的残缺。正因为跌宕起伏,曲折通远,历史和人生才有了引人入胜的情节。人生不可能总是处于极巅,也不可永远处于谷底。巅峰和谷底之间,到处都是胜景,残缺的胜景,圆融的胜景。
当一个真实的诸葛亮站在我面前时,我感到了一种圆融。诸葛亮是圆融的,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真实可感。我的内心也是圆融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我终于又走进了古隆中。我终于走近诸葛亮了。这是一个夏天的傍晚。我一到襄阳,就直奔古隆中。我和诸葛亮有一个约会。天气溽热,蝉鸣不已,偶有蜻蜓掠过,我却分明感受到了一缕薄翅撩起的风,惬意无比。在小虹桥上,我看到了诸葛亮因烦躁或苦恼而来回踱步的身影。在梁父岩旁,我碰见诸葛亮时,他正在构思《隆中对》,不断地摸着后脑勺,愁眉苦脸。在躬耕田,诸葛亮披着蓑衣,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泥水里,样子笨拙可爱。诸葛亮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走出隆中,苦恼极了。看到诸葛亮苦恼的样子,我乐不可支。回到襄阳时,我站在通往古隆中的路边,端详了很久,想看看诸葛亮骑着毛驴走过时留下的脚印还是否清晰。
责任编辑 易 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