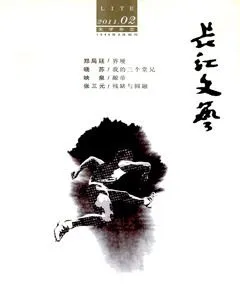怀旧
那时候,我们的住房实在太小了,住在铁路居民区的平房里,每家的实用面积都不超过二十平方米。人口少的住两间,人口多的住三间。讲起来是“间”,其实房间隔得很小,像鸽子笼,放在现在,是没法住的。没有卫生间,倒是有一间小厨房,小得连身子都转不开。那时候,家家的房门都是开着的,前门后门都开着,只有冬天例外,因为冷;即便是夜晚,也不插门。似乎从来就没有偷盗的事情发生过。
串门是常事,即便主家没有人,邻居也照来串门不误,该借什么借什么,该拿什么拿什么;不像现在,门挨着门,一年也难得进隔壁人家一两回。什么都是习惯,习惯成自然。所以,要是谁家失了窃,便是一件稀奇的事。
我们家就曾失过窃,那真是一件稀奇事。半截橱上放了两元钱,是几天的菜钱。母亲递给我钱的时候,我正在梳头,说,先放那儿吧。母亲就把钱放在了半截橱上。我的头发好硬好涩,一梳能梳半天,等我梳好了头发,再过来拿钱,两元钱已经不翼而飞了。
事情惊动了父母亲,惊动了兄弟姊妹,一家人大呼小叫的,翻箱倒柜,合力动手;尤其是父母亲,恨不得挖地三尺,闹个水落石出。当希望完全破灭后,一家人便开始了漫长的责备和声讨;大哥脾气暴,甚至要动手揍我一顿。家里人的过激行为我是理解的,只能承受。那时的两元钱,相当于现在的二三十元,或者更多。
我是一个无所用心的人,不大肯动脑子。可丢了钱,失了窃,一家人都在指责我,残酷的现实逼迫着我,使我不得不去思考……把几个经常登门的邻居挨个琢摸一遍,这时候,差不多是必然地,我开始怀疑我们后面一排平房中间一家的张巧云了。
张巧云跟我同校,同年级,但不同班,不过我们在一起关系很不错,跳橡皮筋,跳格子房,我们都喜欢在一起。巧云只有一样不好,天生好吃,曾偷吃过我家隔壁冯家的炒鸡蛋,也偷吃过我家的水煮花生。只有天生好吃的人才会偷钱,我仿佛突然开窍了,这个想法已在我的脑子里根深蒂固。
我耍了个小聪明。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往往能使人聪明起来。隔两天,在张巧云又来我家串门的时候,我把事先准备好的一元钱悄悄地放在半截橱上,然后我对巧云说,我要去上厕所了。刚才我说过,邻居来串门,主家是没有必要一直待在家里的,完全可以把家交给客人,所以我对巧云讲这句话,并没有下逐客令的意思。事实上,那时候我们根本就不懂什么叫逐客。然后我就拿了两张草纸,团在手里,煞有介事地从后门出去了。
我并没有上厕所,我只是快步从我们那排平房绕过去,从后门绕到前门,也就几十米的路程,然后就踅身在门外的窗台下。我的动作异常轻灵,影子似的,因为我瘦,营养不良。在我踅身窗外的时候,我望见同样像影子一样瘦弱的巧云,正站在外间屋的大桌子边,在那儿哼歌,似乎还在照镜子。我记得她哼的是《我爱北京天安门》。那个年代我们只会唱有限的几首革命歌曲,《洪湖水浪打浪》,也是后来才学会唱的。长方形的镜子算是我们家的奢侈品之一,有现在普通杂志那么大,由铁丝撑子斜撑着,立在桌子上,对女邻居们形成了一种心理暗示,迫使她们每天都要来我家串门,照镜子。照了一会儿镜子,巧云去了里间屋。
家里暗归暗,但我们那时候学习一点儿都不紧张,视力一个比一个好,房间又小,隔着一道只有门框没有房门的空门,我能看见巧云站在半截橱前的所有肢体动作。而且,由于她去了里间屋,我已经不必鬼鬼祟祟了,在窗台上伸长脖子,把自己伸成一只鹅的样子,反而看得更清楚。
巧云一下子就发现半截橱上的一元钱了。我从她的动作里已经清楚地看出来,甚至用不着判断。她先是够过脸去,像是想看清那张纸币。其实纸币是用不着看清的,在家家都缺钱的年代,哪怕一分两分的镍币都很耀眼,五分的镍币已是光芒四射了。一张那么大的纸币,平躺在那里,它的硕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顿了顿,巧云的手开始行动了。她的手不像她的头那样,伸得很夸张,而是羞涩地抬起,微微向前。我以为她会迅速地将一元钱攥在手里,然后胡乱地塞进身上某个隐秘的地方。可是没有,她的手已经伸到半截橱上了,突然停住,就那样愣在那里,一片犹疑。之后,竟然鬼使神差地耷拉下来。没有成功。是她自己停止了行动,制止了自己的成功。这真是奇了,巧云一下子就叫人不可理喻了。
她的犹豫真是令我迷惑不解。好在我有耐心,又没有人从门口经过,没人打搅。巧云回了一下头,勾着脖子看了看,像是看看有没有人打门口经过。我赶紧将头缩下去,心跳也同时加速,像要擂鼓。等我再探出头的时候,巧云已经不见了。
得手了!我脑子里当即一嗡,那嗡声仿佛到现在还能听见,它传递出的,是既庆幸、又懊恼的信息。在这种复杂情绪的驱使下,我奔进家里,直接奔进里间屋,去半截橱跟前,去看半截橱上那已经掉了漆的台面。一切全在我的预料之中,或者说,巧云完完整整地落入了我的圈套,那钱,已经不翼而飞了。
我追出后门,连巧云的影子都见不到。本来我是想抓一个现行的,可现在,人赃都没了。我这懊恼呀,那点庆幸的心理,早已被扫荡得干干净净!
不过,当天晚上,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就在我们铁路居民区流传开来。我说“爆炸”似乎有点过分,但你如果身临其境,你就会知道我的说法并不夸张。“张巧云是小偷,是个偷钱的小偷!”——想想看,这是多么了不得的一件事!一个初中生,一个女孩子,她竟然是小偷!她不是偷一块橡皮、一支铅笔,而是敢于去邻居家偷钱,敢于自甘堕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小偷!太可怕了!
消息是经我的口,通过我父母,通过我的兄弟姊妹,传到隔壁,传到隔壁的隔壁,就这么像传染病一样逐渐传播开来的。到第二天,已是满城风雨。
满城风雨的后果,是张巧云被她父亲揪着耳朵,乖乖地到我们家来,向我父母,向我们家的全体成员赔礼道歉,并当即退还了那一元纸币。
旧事重提,是因为我们家出了一件事。我儿子晓钢,眼看着就要结婚了,却不料,新房失了窃。倒是巧了,是在凌晨,正赶上晓钢下班,拿钥匙开门进家,盗窃的女子逃不脱,躲进大衣柜里,被他抓了个现行。所以,说失窃,其实又是不确切的,人赃俱获,并没有失掉什么。本来应该是铁板钉钉的事,想赖也赖不掉,可出人意料的是,那女子当场脱起衣服,直至脱得上身赤裸,下面只穿了一件小裤衩。晓钢慌了,忙不迭地说,你别……你别……女子见晓钢害怕了,当即要挟,说给你两条路,要么放我走,要么我就告你耍流氓!我儿子是个正直的人,从小看到大,我对他还不了解吗?见女子耍无赖,晓钢慌了,即刻掏出手机,打110。派出所很快来人了,却分不出孰是孰非,让女子把衣服穿戴整齐,将两个人带到派出所。
以上过程,是在出事以后,我儿子在派出所给我打电话告诉我的。派出所办案注重程序,讲的是“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不可能像我这样,只听晓钢一面之词。就是这个“兼听则明”在其中起了负面作用,两个人各说各的理,女子嘴巴会讲,底气倒像是比晓钢还足呢!害得我家晓钢,再也洗刷不清了。
我当即暴跳起来,在电话里骂开了。骂过了觉得不对劲,是跟儿子通电话,怎么能骂些脏话呢?
稍稍冷静了,我问儿子,她上门偷盗是明摆着的,既然明摆着,派出所干吗不处理她?儿子带着哭腔,说按她的狡辩,她虽然上门偷盗,可并没偷到东西,没偷到东西就构不成盗窃罪,而我耍流氓,已经既遂了。我说,她讲这话,就说明她是老手,既然派出所认定你耍流氓,那他们打算怎么处理你?儿子说,派出所的人一看我这样子,就知道不是耍流氓的人,可这种事情,又没有第三者在场,谁能讲得清啊!我说,那派出所也太不负责任了,各打五十大板,这算什么办案?儿子说,也不完全是这样,两位警官允许我打电话,不允许她打电话,还扣下了她的身份证和手机。
我说:“那好,派出所不让你走,你就别走,我马上过去,我倒是要看看,她到底是什么人!”
一元钱,讲起来值钱,其实也没有什么,毕竟只是一元钱。可是,出人意料的是,时隔不久,大概过了半个月吧,突然派出所来人了,来人调查张巧云。
那时候派出所民警上门,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绝不亚于现在家里发生了大要案。我们全家人都忐忑不安,我就更不用说了,面对两位登门的民警,如临大敌,慌张得就像是自己不久前刚刚行了窃。
民警把我们家里的人都支出去,打算只留下我一个。父亲说,孩子胆小,我怕她被吓着。民警说,那你就留下来吧。于是父亲留了下来。父亲讲话的声音已经变调了,由此可见,父亲的胆子并不比我大。
一位民警铺开笔录纸,做起记录。先前讲话的民警继续讲话,叫我如实反映一下半个月前我们家失窃的事。我便紧紧张张、前言不搭后语地反映了那天发生的事。这中间,民警郑重地点头,态度异常严肃。等一元钱失窃事件调查完了,民警才舒了一口气,道出了这回前来调查的原委。
原来是我们隔壁的冯家丢了自行车。如果说我家的镜子是奢侈品的话,那么冯家的自行车不知要奢侈到什么程度了!冯家在我们铁路居民区算是富裕的,永久牌自行车已经充分显露了他家的富裕;冯家老大骑着自行车,进出于我们铁路居民区的青石小路,铃声才一响起,他已经横冲直撞地驶到我们跟前,能把人吓死!平时我们很少向他借自行车,冯家老大吝啬得很,借不到车子,反而落得难堪。我终于弄明白了,冯家丢了自行车,报了案,民警下来破案了。
“你怀疑哪一个?”民警对我开导、启发,或者说,循循善诱。
“我……我没有谁怀疑,我……我不知道。”我紧张得心都快要蹦出嗓子眼了。
“不要紧,这事跟你无关,你别紧张,你只是旁证。”民警继续诱导。
父亲在一旁闭一闭眼睛,终于咬紧牙关,做出了痛苦的选择:“你们是希望我家女儿说出、说出是张巧云,是吧?可、可我们……没看到她偷人家自行车啊。”
“好!很好!”民警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我们并没让你们掌握充分的证据,我们相信你们对她以往情况的了解。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们是经过调查的,所以你们最有发言权。”
父亲痛苦不堪。父亲明知民警设的是一个小圈套,为了帮我开脱,他还是被动地钻进了人家的圈套。
调查完毕,民警该走了。他们递过来刚刚写的笔录,叫我签名。字写得不仅潦草,还特别乱,乱糟糟的,我几乎认不出几个字来。见我一脸为难的样子,父亲小心翼翼地将笔录拿过去,仔细地看。
末了,父亲谦虚地说:“这两行字,我想请你们……念一念。”
刚才记录的民警接过笔录纸,读道:“我们怀疑偷自行车的可能是张巧云,因为她是小偷,以前偷过我家的钱。”
“我们没说过、没说过这样的话。”父亲紧张异常,辩解道。
“这没事。”刚才提问的民警接过话去,从容地说,“毛主席说,允许别人犯错误,也允许别人改正错误。别人犯了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们应该勇于帮助别人。”
父亲听得有点发愣,只好接过民警递过来的笔录纸,小心地签了名。
我不敢怠慢,学着父亲的样子,颤抖着右手,也签了名。
两位民警离开我家,又去了前后几家。后来我听说,民警在调查完之后,还去了张巧云家,把张巧云带到了派出所。张巧云在派出所泪流满面,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先是不承认偷了我们家的钱,但在民警读了几份调查笔录之后,在事实面前,她不得不低下头,承认确实偷过我家的钱了。民警乘胜追击,说你既然偷过人家的钱,你为什么不能偷自行车呢?很明显,冯家的自行车就是你偷的。
这件自行车失窃案,北门镇派出所的民警们到底也没能真正地侦破,虽然抓到了盗窃者,可赃物到哪儿去了,始终是一个谜;追不出赃物的下落,即便破了案,民警们脸上也不光彩。所以民警们还是小心为妙,仅将张巧云在派出所关押了一夜,第二天就把她放回家了。
半个月后,冯家老大去派出所,自解了这个谜。原来自行车被冯家老大的舅舅骑走了。骑走之前,舅舅和冯家老大的父亲在一起喝酒,舅舅说,你家永久牌自行车,不能借给我家德胜骑一下,去乡下相个亲吗?德胜这么大岁数了,谈个对象也不容易,让他骑个车子,又是永久牌的,也让乡下的丈母娘和丈母爹见识见识!那时冯家老大的父亲醉眼迷离,摆一摆手,胡乱地就答应了。到了舅舅摇摇摆摆地推着自行车走人的时候,冯家老大的父亲已经趴在桌子的边沿上,口水淌成了一条长龙。
谜是解了,但张巧云的事仿佛成了定论。即便她没有偷冯家的自行车,可是大家在聊天的时候,聊到巧云,仍旧会想到偷自行车这件事。人的思维是有惯性的,这惯性驱使着人们,于漫不经心中认定了那自行车就是巧云偷的。
等我赶到派出所的时候,天已经大亮。
事件居然有了新进展。两位警官除了扣下女子的手机和身份证,还叫她自己动手,把身上的所有东西都掏出来。那女子掏了一些零碎东西,神色已略显慌张。两位警官发现了破绽,旋即叫来一位女警官,简单地一搜,就从女子身上搜出了一枚金戒指。我赶到的时候,那金戒指已经放置在办公桌的正中间了。
“这戒指是我的!”我迫不及待地说,“是我买给晓钢对象的!”
我不放心,拿起来,凑近了看一看:“就是这个,发票还在我那儿呢!”
收起戒指,压一压情绪,我方才顾得上瞧瞧旁边的女子。这一瞧,着实让我吓了一跳——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几十年前的一个旧邻居,弯弯的眉毛,细长眼,尖尖的鼻子,薄嘴唇,长相一点都不难看;唯一不足的是,从眉目间透露出的那股轻薄之气,是无法掩饰的——她叫什么名字呢?看我这记性,竟想不起来了!
“你打电话召人来,召人来我也不怕!”女子虚张声势地对晓钢说。
“这是我买的戒指,怎么在你身上?!”我真想抬手扇她一个耳光,“我见过盗贼,但我还没见过像你这么皮厚的盗贼呢!”
“你不要骂人哦,骂人我对你不客气!”女子发了一下愣,很快就说,“你家儿子想耍流氓,耍不成,就想栽赃!我哪知道这玩意是怎么到我身上的?我还怀疑,是他趁我不注意的时候放我身上的呢!反正我告诉你,我根本就不知道!”
我气得差不多要闭了气。瞧这女子的穿着,吊吊衫,牛仔短裤,一看就是个不正经的货色;我儿子老实,幸亏这些年有我在后面为他撑腰,不然的话,他会经常受人气的。他马上就要结婚了,怎么会对这样一个女人耍流氓?! 这一刻,在派出所里,在这样一个讲理的地方,我却遇到这么一个刁滑可恶的东西,我想保持头脑清醒都难。
我意识到我的血压迅速上升。我气急败坏地坐下来,暂时闭上眼睛。我不想跟她吵架,一切自有公断……意外地,几十年前那个陈旧的形象突然清晰起来,在我眼前现形了。那形象不仅使我想到那些陈旧的故事,甚至,我连她的名字都想起来了。
——张巧云。
我们虽然知道张巧云在派出所里泪流满面,但我们那时候尚不知晓,她的这一哭,其实已经注定了,她这一辈子都将与“小偷”结缘,要为我家的那一元钱而身败名裂。那时候虽然钱金贵,但人品比钱更金贵。
高中毕业的时候,我们那批学生统一分配,进了工厂。为张巧云,上面特地来人调查了居民委员会,又去了派出所,派出所的民警也把张巧云通知去。在派出所里,张巧云哭得很动情,很伤心,表面上虽然不及当初的泪流满面,但内心的复杂程度,肯定要比当初广泛、深刻。她嘤嘤地哭着,低语道,下次我再也不偷了,请你们相信我……相信我——可谁会相信她呢?就连冯家失而复得的自行车,在人们的意念里都是被她偷盗的,谁还有理由不把她看扁了呢?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张巧云未能分配工作,在家待着。我们那批学生,只有两个人没能分配工作,除了她,还有一个男生,是家庭成分不好的。
到了第二年,应届毕业生应该下放农村了。张巧云等待着,等着能和应届毕业生一起上山下乡。可是,连那个家庭成分不好的男生都下放了,张巧云却未能成行。开始我们一直以为,是她自己好吃懒做,不肯下放。直到后来我们才知晓,是农村不愿意要她。农民们说,成分不好不要紧,我们可以改造;可一个小偷分给我们,我们怎么对付呀,我们岂不是要遭殃了吗?乡下有一个老学究,讲话文屁屁的,说得更是难听,说,政府把一个小偷安插在我们身边,不就等于安插了一个特务呀,我们手无寸铁,怎么能对付得了一个女特务呢?
话说到这个份上,张巧云眼前的路,就等于断了。
吃了两颗随身携带的降压药片,在公安人员陆续来上班的时候,我已经有效地控制了我的血压。儿子晓钢虽然摆起架势,剑拔弩张,但我知道,要想和女子唇枪舌剑,他还差了不小的功夫。
两位警官显出很为难的样子。我知道他们办案讲求的是证据,证据只能反映偷盗行为的存在,暂时还解决不了流氓行为是否存在的问题;可这女子绝不是省油的灯,得不到满意的结果,她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半天没有说话的我,这时的思路却作了调整,或者反过来说,是对女子的攻势已成了强弩之末。我一改刚来时激越的态度,缓下声音,甚至可称作“柔和”,心平气和地对女子说:“我想问你一个人,看你是否认识。”
女子不在乎地哼一声,算是回答。
我说:“张巧云——跟你长得特别像,连声音都像。你认识吗?”
“她是我妈,我怎么会不认识?”女子虽然还是一副满不在乎的腔调,但神情上已经发生了些许变化。
我感到吃惊。虽然判断准确,但我仍为我的判断成为事实而惊讶不已。愣怔了好半天,我才终于改变主意,对两位警官说:“我们两家以前是邻居,我和她妈关系还很不错……这样吧,我们自行解决,可以吗?”
警官也甚感意外,其中一个高个子说:“你们愿意自行解决,我们当然没意见。”矮个子警官迅速在笔录纸上作两行记录,说:“那我们暂时回避一下,等你们谈好了,签个字。”
两位警官去了走廊对面的房间,直等他们出门了,我才意识到我的冲动。我瞧一眼满脸愕然的晓钢,再看了看神情淡漠的女子,突然有点后悔,感觉到我的所作所为和我的年龄实在是不相符。
此刻,外面光线很好,我和女子,和儿子晓钢,我们三个人坐在派出所楼下最东边的这间办公室里,开始了一场简单的回忆。
我告诉女子,我和她母亲曾经是前后排的邻居,我们住的是平房,那时候楼房很稀奇,叫“洋楼”,平房虽然简陋,但有一个好处,就是多远的邻居都认识,大家相处得都很不错,不像现在,还要互相猜忌。我告诉她,她母亲和我同岁,算得上是同学,我们经常来往,大家都没有心计。可有一次,她母亲拿了人家的东西,是人家放在家里的一元钱,很快就被那家人发现了,当然随后,她母亲就退还了那一元钱。可是,过后不久,为着那一元钱,她母亲受到派出所的调查,从那以后,就一直背着小偷的罪名,背了许多年。我告诉她,后来我们都分配了工作,但她母亲没能分配,就是因为那一元钱,从此走了一条与我们截然相反的人生道路。最后,我沉重地叹了一口气。我的这声叹息发自内心,相信她一定能够听出其中的真情实意来。
这中间,我隐瞒了事件中作为当事人的我自己,而是以“人家”或“那家人”简单地将我本人一带而过。
然后我说:“很多年不见了,不知道你母亲现在怎么样了。”
女子神色冷淡,近乎麻木地说:“她能怎么样?她已经死了十几年了。”
“她……死了?她怎么会死?”我震颤了一下,很剧烈。
“她凭什么不会死?她成天神神道道的,也不疯,可就是要摆出疯疯癫癫的样子。”
“她这样……就能死吗?”
“她去建筑工地,也不知道去干什么,被上面掉下来的东西砸到了,在地上躺上大半天,也没人看到,死了。”讲完了这话,女子才像是动了一点点恻隐之心,“你跟我回忆这些,是什么意思?是想跟我了结这件事,两清吗?”
我的大脑暂时处在休止状态,一时跟不上她的节奏。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表述这件事了。我的多情,我的多愁善感,我的怀旧情绪,所有这些,都转换成了女子自我防卫的武器,这一刻,我居然被她推到了一个尴尬境地。
“现在我弄明白了,我妈担着一个罪名,是因为你。”她冷静地看着我。
“不是我……你搞错了,不是我,是我们邻居。”我突然有点慌张,“我只是……怀念过去,见到你,见你和你母亲长得这么像,就想到你母亲了。”
“是你用一元钱,害了我妈,这是明摆着的!”她并不听我解释,加重了语气,“你的眼神,你的表情,你想赖也赖不掉!是你害了她,害了她一辈子!”
“你理解错了,这跟我无关……你真的理解错了。”我闪烁其词,底气明显不足,“我只是想说,其实你母亲很淳朴,就是因为淳朴,才走上了……那样一条路……那时候我们都淳朴,不光是你母亲一个人。”
“你还讲什么呀讲?!”她突然摆出翻脸的架势,眉毛的两端狠狠地朝上挑,薄嘴唇向两边一咧,更显得薄了,“你已经讲得够清楚了!你害死了我妈,你这是变相杀人!你……你们这些……!”
两位警官一直在对门观察我们的动静,听见吵声,走进来,问我们谈得怎样了,能不能自行解决。女子一副动容的样子,说:“我妈当年是被她用一元钱害死的,现在她儿子又来害我,她现在想跟我两清,你们说我能不能答应?”
晓钢争辩道:“你是入室偷盗,跟我妈有什么关系,怎么能把她牵扯进来呢?”
“我入室,我承认!我妈当年不也入室了吗?被你妈害死了。是你妈自己承认的。你现在,又来害我!”女子转向警官,面无表情,“你让她把那段历史跟你们讲一讲吧,她会讲古。你们听了就会发现,有一句话千真万确——历史,惊人地相似!”
“我不想听你们扯太多,你们谈没谈出结果来?”高个子警官已显出了不耐烦。
“结果?——算了吧,念在我们以前是邻居的份上,那谁也不找谁,两清吧。你们把我的东西还给我。”女子说得很随意。
“你的东西当然要还给你,那戒指呢?”高个子警官问。
“戒指是她的,我不要了,给她吧。”她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看也不看我,就像是在市场上成交一笔小买卖。
“这样处理,可以吗?”高个子警官转而问晓钢。
晓钢看着我。我这儿子真是没用,全无主张。
我如鲠在喉,内心却是极度的伤感,我说:“既然没丢东西,那就两清吧。”
高个子警官出门去,少顷,回来,把女子的证件和物品拿过来。矮个子警官则坐下,在先前的笔录上补充几句话,然后将笔录递给女子,要她看一看。女子接过笔录,接过钢笔,看都不看,就飞快地签上自己的名字。矮个子警官又把笔录递给我儿子。
在晓钢认真看笔录的时候,女子接过警官递给她的东西,瞥我一眼,嘴角似乎流露出一点笑意。这笑意似曾相识,又很陌生。多年前的那个女子一下子就走到了我的眼前。我以近乎绝望的口吻说:“你应该学学你母亲,学学她的淳朴。”我的声音很低,其中像是包含了羞怯,有点抖,很不争气的意思。
话音尚未结束,女子已经扭转身去,影子似的踅身出了办公室。
这结局显得仓促,是我意想不到的。我脑子里一片虚空,血压又开始上升了。
责任编辑 向 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