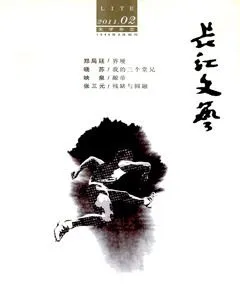我的三个堂兄
1
你问到的这张照片,是我这次回老家油菜坡拍的。你说这张照片拍得很好,我也是这么认为的。这次回到老家,我前后拍了近百张照片,要问我最喜欢哪一张,我想肯定就是这一张了。
照片上的那条板凳,你说有点古董的味道。我觉得你的眼光真厉害,它实际上就是古董,是从前吃宴席时坐的。那时候,我的老家还没有现在流行的这种圆桌,逢年过节,或遇上红白喜事,吃宴席时都用的是那种四方桌,桌子的每一方横放着一条板凳,一条板凳上坐两个人,每张桌子上坐八个人。
你说最有意思的,是坐在那条板凳上的三个人。我也觉得很有意思,那么大的三个人,并排坐在一条板凳上,看上去虽说有点挤,但显得很亲密。你看他们三个人,屁股挨着屁股,肩膀连着肩膀,手挽着手,中间一丝缝隙都没有,这才叫亲密无间啊!坐在板凳上的那三个人,都是我的堂兄。你问他们三个人的眉毛怎么长得那么像,现在我来告诉你原因,他们是一个妈生的。我这么一说,你大概就会明白,他们为什么能如此亲密地坐在同一条板凳上了。对了,他们都是我大伯的儿子。
你说坐在中间的那一个岁数最大,这是毫无疑问的,他的头发都花白了,额头的皱纹也多一些。他如今已经七十多岁了,但脸色红润,嘴唇光亮,仅从面部上看顶多六十出头。他喜欢喝点小酒,一天可以三顿都端杯。正是由于吸收了酒的营养,他的气色才保持得这么好。人当壮年时,买酒凭票,他有一次买了一瓶酒,回家路上一不小心把酒瓶落在石板上,瓶破酒泼,他就双手伏地,慌忙用嘴去舔在石板上流淌的酒,结果酒瓶渣把他的嘴唇和舌头都划破了。这个细节被我写进了一篇小说里,你可能看过,那篇小说叫《走回老家去》,小说发表后还被《新华文摘》转载了。说了半天,我还没告诉你他的名字。不过,我现在说也不迟,他的名字叫温,是我的大堂兄,我喊他大哥。
坐在温左边的那个人叫良,是我的二堂兄,我喊他小哥。他今年六十二岁,但面黄肌瘦,颧骨高耸,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一些。良的这个样子与他怕老婆有关,老婆要他向东,他不敢向西,老婆让他打狗,他不敢打鸡。其实他年轻的时候是不太怕老婆的,有一天早晨,良清早起床去打蒿,九点多钟扛着蒿捆回家时,他老婆还在床上睡懒觉,良一怒之下就将浑身只穿了一条花裤衩的老婆抱到门口土场上示众,还大声喊,大家都来看呀,她这么晚了还在睡?他一边喊一边将白花花的老婆丢在地上,一时招来好多人看稀奇。良很勤劳,也很辛苦,近几年学会了熬麦芽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熬,然后挑着麦芽糖去镇上卖,经常是天黑了才回家。你看过我那篇题为《麦芽糖》的小说,就是《小说月报》转载过的那篇,作品中主人公的原型就是良。
你问那个戴礼帽的是谁,他是我的三堂兄,我把他喊作幺哥,他的名字叫恭。恭的脸胖胖的,把礼帽一戴,就不大像个农民了,倒像一个在电视剧中经常出现的特务。那顶礼帽是我送他的,恭曾利用谐音开玩笑说,他原来是没有礼貌的,自从我送他礼帽后,他就有礼貌了。恭已经五十开外,但精神面貌还像个年轻人。他能说会道,学过一些手艺,有点艺高人胆大,办商店,开农用车,放炮炸石头,样样敢干。他热心快肠,喜欢给人帮忙,有一次,村里有个人的老婆跟人跑了,请恭陪他去河南找老婆,那人说找到了老婆每天付恭五十块钱,结果出去一个星期,老婆没找回来,恭也一分钱没得到。我这么一说,你肯定会想到我发表在《钟山》上的那篇《陪周立根寻妻》,小说中的那个郝大哥写的就是恭。
我的大伯就这么三个儿子。我想,大伯当初肯定是想生五个儿子的,然后依次取名叫温良恭俭让。但他只生了温良恭,还没来得及生俭让就过早地去世了。大伯死时我还小,记得埋他的那天,我是被一个堂姐扛在肩上去坟地的。
三个堂兄很早就分了家。大伯在世的时候,他们都住在大伯住了几十年的那个老屋场,一排老房子里住着三家。早些时候,我们家也在那个老屋场,我们家的房子在他们那排房子隔壁。后来,我父亲把我们接到镇上去了。我们家搬出老屋场以后,恭和温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也陆续从老房子里搬走了,老屋场就只剩下了良。
你问我的三个堂兄现在住得怎样,我这样给你说吧,他们现在的住房都不错,住的都是楼房,墙上贴着面砖,屋脊上安着龙凤呈祥的图案。不过,有一点我感到遗憾,就是他们三兄弟分住在三个不同的地方,有点三足鼎立的味道。平时,他们各忙各的,相互往来很少,久而久之,三个人就有些生疏了,看上去不怎么像是亲兄弟。更让我感到遗憾的是,他们三个人的感情,也像他们的房子一样隔得比较远,而且三兄弟之间还存在着一些矛盾。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再回到这张照片上来。前面我说过,我的三个堂兄坐在同一条板凳上,看上去亲密无间。但我要实话告诉你,你看到的是照片,不是生活。那天,他们是为了照像才坐到同一条板凳上来的,我举着相机,一再劝他们靠紧一点,他们才努力坐得这么近。在按相机快门时,我默默地想,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如果也能坐得这么近,靠得这么紧,那该多好啊!
2
现在,我给你专门说说恭吧,就是照片上那个戴礼帽的人。你问这顶礼帽是在哪里买的,我想起来了,是那年去内蒙古参加一个笔会,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买的。
恭比我大五六岁的样子,在我的印象中,他当初离开老屋场,好像有点迫不得已。但那时我在武汉读书,具体的情况我也不是完全清楚。
我还清晰地记得大伯留下来的那一排老房子,长长的一溜,少说也有十几间。温一家人住在西头,他很能干,也很好胜,分家不久就挨着分给他的那几间房子又盖了几间。良一家住在东头,大约有两三间屋。恭被两个哥哥夹在中间,中间有一个天井,一下雨到处噗水。恭那两年非常不幸,他的第一个老婆,也就是我的第一任幺嫂子,因为一件事情想不开就喝农药死了,给恭扔下一个两岁左右的女儿,幸亏由大伯妈帮他带着。
恭搬走的直接原因,好像是大伯妈与良的老婆关系不好。良的老婆,我称她二嫂子,人也说不上坏,但嘴巴不饶人,什么话都能从她舌头上滚出来,加上大伯妈也不是好惹的,所以婆媳俩经常闹矛盾,三天两头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吵架,骂许多不堪入耳的话,有时还动点手。后来实在住不下去了,恭就只好带着大伯妈和女儿离开了老屋场。
恭离开老屋场以后,开始住在一个破烂的窑场里。原来那儿是村里的一个烧瓦的窑场,窑边盖了一个堆瓦的棚子,后来窑破了,不能烧瓦了,窑场也就废弃了。恭把那个堆瓦的棚子修整了一下,一家三代人就在那儿暂时生活下来。
住在窑场的那段日子,生活条件虽然极差,但恭一家还过得算是温馨。记得恭那会儿还找了一个相好,我有一次放了寒假去那里,恭还把那个女人喊来煮饭我吃。那个女人姓秦,就住在窑场附近,恭站在破窑上一喊,她一会儿就来了,手上还带了一些干菜。那个女人长得还可以,煨的鸡汤也特别好喝。我发现那个女人对大伯妈和那个小女儿也好,说话轻声细语的,脸上挂点儿微笑。吃饭后,我建议恭干脆早点把那个女人娶作老婆,恭却说,人家有丈夫呢,还有一对儿子。听恭这么一说,我就对那个姓秦的女人肃然起敬,觉得她特别了不起,自己有个幸福的家,还能关心恭这样的家庭,真是难能可贵啊!
不久,大伯妈去世了。大伯妈一走,窑场也破得住不成了,恭就带着女儿借住到了公路边的村委会。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因为分田到户,村干部精减,村委会一时就空出了很多房子,许多无房可住的人都去借住。但是,借住一阵子还可以,时间一长就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恭没住多久就不想在那里住了,他不愿早晚看那几个村干部的脸色。
这个时候,我已经大学毕业,在省城参加了工作,每个月有了固定的收入,偶尔还能得一笔稿费。一次回老家,恭对我说起他的处境,说得眼泪汪汪的,我听了心里也十分难受,同情心油然而生。恭说,他打算自己在公路边盖一间房子,我一听就决定帮他一把。
我这个人,记忆力特别好,小时候的好多陈谷子烂芝麻都记在心里,尤其是那些曾经温暖过我的人和事,我更是铭心刻骨,经久难忘。在我记忆的屏幕上,与恭有关的第一个镜头是他背着我去上学。那时我三四岁的样子,我们家那会儿还住在老屋场。恭当时也只有十岁大小,正在邻村铁厂垭小学读书。有一天,恭上学时把我也带上了,说要带我去学校玩。上学的路多为上坡,走起来特别累,我走到半路上就不走了,恭只好背着我去学校。我一直记得恭那天背我的情景,他把自己的书包挂在脖子上,两只手反过来搂着我的屁服。我紧紧地伏在他的背上,像一只收拢了翅膀的小鸟。到了学校,我不敢一个人在外面玩,恭就把我带进教室,上课时让我坐在他身边。当时是两个学生共一条板凳,我坐在板凳头上,位子有点窄,恭怕我不小心从板凳上掉下去,就不时地用手扒我一下。长大以后,我经常想起恭当时用手扒我的情景,每次想起,心里都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就因为那段让我难以忘怀的温暖记忆,恭一说要盖房子,我就慷慨地送了一笔钱给他。现在,我也忘了当时到底给了他多少钱,是几百,还是上千,我真地记不清楚了。但是,有两点我却清楚得很,一是我当时对恭已尽了全力,因为我那时刚参加工作,手上的钱并不多;二是我给恭的这点启动资金,让他下定了盖房的决心,在此之前,恭由于手头没钱一直在犹豫不决。
恭一向是个说干就干的人,等我半年后再回家乡时,他的新房已经盖好,并且已住进去了。因为资金不足,他只盖了一层,也没装修,连墙都没粉刷。不过恭看上去特别高兴,不管怎样,他总算有了自己的房子。让恭高兴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这时候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和他结婚的女人。这个女人姓徐,虽说有过婚史,但她对恭却很真心,模样还端正,人也很勤快,一看就是个可以过日子的人。没过多久,这个姓徐的女人就和恭结婚了,成了我的第二任幺嫂子。
有了新房子,有了新老婆,恭的生活姿态陡然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也变得更加能吃苦,对亲人对朋友也多了一些尊敬和真诚。实话实说,在此之前,恭的为人处世,有许多地方是让人不敢恭维的,相反还会让人摇头皱眉。
不过,关于恭的好多坏话,我都是听别人说的,其中免不了有一些不实之辞。有人说他做事不愿下力,有人说他喜欢吹牛,有人说他对老辈人不讲礼节,还有人说他乱搞女人。对于这些说法,我当然有我的分析和判断,有一些指责我也不敢苟同,就说女人问题吧,他前妻去世了,又没找到愿意和他再婚的女人,恭又正当盛年,他找个把相好应该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至于不勤劳,说大话,缺礼貌等等,那肯定是恭的不对。
说到恭对老辈人缺乏礼貌,我总会想起一个细节来。那时恭还住在老屋场的老房子里,大约二十出头,还没有结婚,一次去外地修河堤回来,穿了一件白衬衣,手上还戴了一只手表,显出阔绰的样子。恭回家从我们家门口经过时,我妈正在门口洗衣服,按辈份,恭应该叫我妈婶子。但是,恭那次戴着手表从我妈面前春风得意般走过去时,居然没有叫我妈一声,戴手表的膀子一甩就过去了。恭走过去之后,我妈颇为生气地说,这个恭啊,戴一只手表就狂成这样,今后要是发了大财,那还得了?说实在的,我那次对恭的感觉也很不好,每当回忆起这一幕,心里就不是一个滋味。
但是,人是可以改变的。盖了新房子之后,恭突然之间变了一个人。听老家的人说,恭能吃苦耐劳了,也不怎么吹牛了,跟过去的那些相好也断了关系,对老辈人也毕恭毕敬了。听到这些,我从心眼儿里高兴。
恭住进新房后,不久就买了一辆手扶拖拉机,帮养路段做一些运输活。不久,恭发现公路段扩建公路需要大量石子,便决定买一台放炮炸石机。他钱不够,找我借,我觉得他脑袋灵活,善于抓机遇,就借了他几千。他借钱时说年底还我,果然我过年时一回家,他就要还我钱。我见他说话还算话,就没马上要他还,让他继续拿着周转。有一次,我问他与那个姓秦的女人还有不有来往,他说自从有了老婆就没再和她睡过。我听说,他还经常去镇上看我父母,有时提壶菜油,有时拎几十个鸡蛋,油呀蛋的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情。我母亲有一次跟我说,恭比以前懂礼貌多了。
过了一年,恭又在那栋房子上加了一层,还在墙上贴了洁白的瓷砖,把原来的木头窗户换成了铝合金的,这样一来,原先看上去不怎么起眼的房子,一下子就像模像样了。接下来,恭找到我,说他想把拖拉机换成农用车。我欣赏他的胆量,于是找到在扶贫部门工作的一个学生,帮他要到了五千块钱。开上农用车后,恭在公路段的活路就更多了,挣的钱也跟着多了起来。更重要的是,恭对生活更有自信了,原来抓着手扶拖拉机的手柄左一摆右一晃,累得吭哧吭哧的,现在坐进了农用车驾驶室,双手轻松地转着方向盘,心里陡然有了一种鸟枪换炮的感觉。
又过了两年,恭不仅还清了债务,还存了一些钱。这时,他突然又有了新的想法。那年春节,恭请我去他家吃饭,喝完酒,他对我说他想盖一栋新楼,一是想开个小商店,让幺嫂子卖些日用百货,挣点生活费,二是想给我专门留一间休息室,让我回到老家能有个固定落脚的地方。我觉得他的想法很好,既有进取心,又有人情味,当即给他鼓了劲,并答应赞助他一笔钱。我这时工资高了,稿费也多了,钱上已比较宽裕,所以出手也大方起来。
恭是春天开工盖新楼的,等我夏天回老家避暑时,他的新楼已经砌起来,只是还没装修。新楼盖在那栋旧房旁边,一共三层。恭把我带进弥漫着水泥沙浆味的新楼里,上上下下转了一圈,一一告诉我每间房的用途。我发现他幸福极了,脸上笑得红扑扑的。恭最后把我带到二楼一间很宽敞的房里,对我说,这一间就是你的卧室,你过年回来就能住了。房子当时还是湿漉漉的,可我听他这么说,心里却感到异常温暖,陡然又想到了小时候在铁厂垭小学坐在他身边的情景。
关于恭,我先就说到这里。你也许会问,我后来去他的新楼里住过没有,这还用问吗?我那年还没到过年就去住了。金秋十月,恭住进新楼时,我专门回老家去祝贺他的乔迁之喜,当晚就住在了他为我准备的那间卧室里。那是一个很温馨的地方,我还在那间房子里写过小说,你在《上海文学》上读过的那篇《四季歌》就是在那儿写的。
3
我接下来给你说一说良,就是会熬麦芽糖的那个人。什么时候,我把良熬的麦芽糖带一点给你尝尝,你肯定会喜欢吃,吃了还会纳闷,心想,照片上那样一个尖嘴猴腮的人,怎么会这样心灵手巧,熬出这么好吃的麦芽糖?
良一直住在那个老屋场,不过,他住的房子已经不是过去的那几间老房子了。那些老房子早已推掉,良现在住的这栋楼房就是在老房子的废墟上盖起来的。要说起来,我对这个老屋场充满了无限深情。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准确地说是一九七九年,我考上大学后才离开这里。离开这里后,我家的那栋老房子给村里一个人住了几年,后来因年久失修就垮掉了。
良的楼房是三年前才盖起来的。虽然只有两层,但因为这个屋场地势高,所以两层高的房子看上去也很高了。房子从外表看起来很不错,贴了墙面砖,窗户上安了玻璃,门是双开的,乍一看肯定是个小康人家。但里面就不怎么样了,墙面只是用水泥浆抹平了,顶上也是光的,也没几样家具。并不是良不愿意把里面装得和外面一样好看,主要是没有钱。要是有钱,谁不希望内外都好呢?实在不能两全其美,只好先顾面子了。
要说起来,良能盖起这样一栋从外面看上去还算不错的楼房,也真是奇迹了。一开始,村里人没有谁会想到良这辈子还能盖栋楼房住住。良老实巴交,又怕老婆,村里从前没有人瞧得起他,就连他的哥哥温和他的弟弟恭,也多少有点瞧不起他。不过,良把这栋楼房盖起来之后,人们都突然对他刮目相看了。
良盖这栋房子真是不容易,前后准备了七八年时间。要说盖这房子的钱,主要还是靠良的勤扒苦做和省吃俭用。为了攒钱盖房,良几度出门打工,去九女沟挖过矿,到神农架扛过木材,他人生得憨厚,又少言短语,不管到哪里,无论干什么,都全靠使力气,全靠流臭汗,全靠拼老命,五六十岁的人了,经常是和三十岁左右的小伙子一样挖,一样扛,有时候还要受包工头的克扣和欺骗。我好多次回老家,都没碰到良,一问二嫂子,才知道他出门打工去了。偶尔一两次,正巧碰到良从打工的地方回来,看见他瘦得皮包骨,胡子比头发还长,我心里就特别难过。这么多年来,我几乎没看见良穿过什么新衣服,身上的那几件破旧不堪的衣服,还长的长短的短,一看就知道是别人送的。
后来好几年,良没再出门打工,一问才知道是带班的人不要他,他们嫌他太老了,更担心他在打工的地方有个三长两短不好办。不能去远处了,良只好在近处找些活做,只要能挣到钱,再苦再累再危险的活他都干。有一回给一户盖房子的人家抬预制板,差点从墙上掉下来摔死了。还有一回,他帮人家掀石头砌猪栏,一个大石头砸破了他的手,有几个手指差不多已残废了。砸手之后不久,我有事回老家看见他,他那只手上还缠着纱布,血迹把纱布都染红了。恭买了放炮机以后,良有大半年时间跟着恭炸石头粉石子,因为恭的照顾,良在这段时间算是轻松一点,也安全了一些。
我事实上一直都在关心着良盖房的事。在七八年前,听我母亲说良打算盖房子,我就给他送去了一千块钱。当时良是准备盖那种老式的平房的,那会儿盖那种房子不需要多少钱,四五千就可以盖起来。但是,一晃几年过去了,良还是住在从前的老房子里。那老房子墙破梁歪,随时都有倒坍的危险,实在是不能再住了。我问良,怎么盖了几年还没把房子盖起来?良苦笑一下对我说,钱还没攒够。我说,几年前不就差不多了吗?良说,你二嫂子不想盖平房,她要盖楼房。我一愣问,你们又没那么多钱,为什么要盖楼房?良说,唉,人有脸,树有皮嘛!后来我听恭说,其实良比二嫂子还想盖楼房。他曾听见良对他老婆说,恭能盖楼房,我为什么不能盖呢?
我能理解良的这种心情,所以也支持他盖楼房,于是又送给他一千块钱。说实话,我与良的感情并不亚于我与恭的感情。实事求是地说,良比恭更有爱心,也更有同情心。也许良自己是个弱者吧,他更知道同情弱者。小时候,我跟着良上山打柴,当时流行在竹竿上绑个铁钩,再将竹竿伸到树上去勾干树枝。我那时个子矮,踮起脚尖也无法把竹竿伸到树上去。良看见我半天勾不到一根柴,就对我说,你别勾了,来捡我勾下来的吧。当时听良这么说,我幼小的心灵陡然一颤,好像有一股温泉流进了我的心田。同时在山上勾柴的还有好多大人,但是,除良之外,再没有第二个人会把自己勾下来的干树枝让给我捡。
少年时代的记忆非常重要,就因为勾柴这样的一些小事,我从小就认为良是个好人,所以一有机会就想帮他一把。恭盖第二栋楼房的时候,我还给恭说,等你把新楼盖起来后,干脆把旧的便宜点卖给良。恭开始还不太愿意,他如果卖给别人,价格肯定会高几千块钱。不过,恭也不完全只认得钱,一想良是自己的哥哥,也同意少一两千块钱卖给良。但出我意料的是,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良时,良却一口拒绝了。良说他不想住到公路边上来,觉得老屋场安静一些,所以还是一门心思在老屋场盖房。其实,良当时没有完全说出真话,后来我才知道,良主要是不想住恭的旧房。有人还给我模仿了良的原话,良说,被恭扔掉的,我才不捡呢!
在良正式动工盖房前夕,我又送了两千块钱给他。不过,这次我没有用我的名义,当时老家的好多亲人都在准备盖房,其中有些人以为我是印钱的,动不动找我借钱,个別人还狮子大开口,所以我就不想让良知道这两千块钱又是我给的,担心他喝酒之后说漏了嘴。我先把钱交给我的一个从城里来的朋友,然后把良叫到朋友身边,说朋友要赞助他两千块钱盖房。良接过钱后对我的朋友千恩万谢,我的朋友忍不住笑说,别谢,这是应该的。直到现在,良仍然不知道这笔钱是我给他的。
良盖房遇到了很多不顺心的事,几次都差点停了工。我在前面说过,温原先住在老屋场西头几间老房子里,那几间老房子都是土坯房。温搬走之后,那几间土坯房就闲在那里了,他想以五千块钱卖出去,但价格偏高一直无人问津。良盖新房时,先要推掉自己的老房子,所以必须先找个地方暂时住下来。良自然就想到了温空着的那几间土坯房,他想借用一段时间。温一开始是同意的,良已经搬一些东西进去了。但是,临到开工前几天,温却突然变了卦,他提出把土坯房卖给良。良当然不想买,他马上就要盖楼房了,还买那几间土坯房干什么?温见良不想买,就有意为难良了,说不买算了,但也不借,还说有人可能要马上买。温这一下把良难住了。就在这个时候,我回到了老家。良找我说到这事,我听了也感到为难。后来,我只好把温和良叫到了一起,建议良还是买下来,同时劝温看在兄弟的情份上只收三千。温当即同意了,可良还是不买,说他盖新房的钱都还没凑够呢,哪有钱买温的土坯房。我觉得良确实有他的苦衷,就突然大发慈悲地说,你就买下吧,我送你三千块钱!说完,我当场就数了三千块钱给良。因为我的帮助,良总算可以按时开工盖房了。
平心而论,恭在良盖房的过程中功劳很大。老屋场交通不便,大车去不了,建筑材料大都是恭用他的农用车拉去的。还有,恭在外面关系多,人活泛,良遇到的许多关口都是恭出面打通的。但谁也没想到,房子盖到一半时,恭却撒手不管了。原因是,良跟着恭炸石头粉石子那段时间,恭一直没有给良发工资,说先记在账上,等良盖房时恭再拿出来。良的房盖到一半时,恭说良的工资买材料已买完了,要良掏钱进下面的材料。良却说,凭他记的账,工资还没用完,认为恭把账记错了。恭认为良说话没有良心,便一气之下不干了。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良突然打电话找到了我,要我做恭的工作。无可奈何,我只好打电话给恭说,看着兄弟情份上,先別算账,等把房子盖好再说。恭还算听我的话,才又接着往下盖。
良的房子前后盖了差不多一年,总算盖好了。房子盖好后,我想,良乔迁新居时,肯定会请我去喝酒。听说,良攒了七八年的钱都用光了,还欠了一些债。我打算去喝酒时再给他一点钱。但是,良请客喝酒时没有请我,我因此对良很有意见。后来见面后,我埋怨良,良说时间是他老婆请一个姓陈的风水先生定的,来不及通知我。我听了哭笑不得,觉得他真是太怕老婆了。我一直认为,如果一个男人怕老婆,还不如不要老婆!
说到这里,你大概已经知道良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了。总的说来,良是一个忠厚老实的人,但是,他并不是一点心计都没有。你知道良为什么一定要把房子盖在老屋场吗?根本原因是,那儿有一股泉水,良觉得那是个风水宝地。你看过我的那篇《龙洞记》吗?写的就是这股泉水。如果你没看过,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二零零五年第二期的《长城》,或者二零零五年第六期的《小说月报》。
4
最后,我该给你说一下温了。其实在说良的时候,我已经说了不少关于温的事。这里只是补充说一说上面没说到的,或者没说清楚的。你从照片上看温,可能会认为他是一个特别有福的人,其实,他也遇到过一些不幸,不过从照片上是看不出来的。
温在十几年前就从老屋场搬走了,搬进了位于公路边的一栋楼房里。温那么早就能住上楼房,与他的大儿子有关。温有四儿两女,也说得上是多子多福了。大儿子在县城工作,是个特别孝顺的孩子,他觉得父母住在老屋场太偏僻了,就和温的小儿子合起来在公路边盖了一栋两层的小楼房。温和大嫂子住一楼,他的小儿子一家住二楼。盖那栋房子时,温好像没出什么钱,最多也就是负责买了点烟酒茶。这都是我听说的,具体情况我不是很清楚。
温住的那栋房子与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是说,他盖房时我一分钱也没给他。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温不需要钱,二是我那会儿手头的钱也不多,还有一个原因不太好说,就是我母亲对温有些意见,不主张我在温身上花什么钱。母亲对温的意见由来已久,那时母亲还带着我们兄弟生活在老家。父亲在镇上工作,母亲在老家种田。刚分田到户时,我们家分了一块稻田,那年大旱,秧苗栽上不久,稻田就没水了。老家门口有一口堰塘,是我们几家共着用的,平时主要由温管理。温当时有点霸道,放水抗旱都得让他优先。有一天,我母亲刚放了一会儿水,稻田还没打湿,温就不让放了,他要继续往他稻田里放水。母亲当时气坏了,泪水在眼里直打转。母亲是个记仇的人,离开老家几十年了,还一直把这件事情记在心里。
其实温也不是母亲想的那么坏,作为一个靠田吃饭的农民,有时私心重一点是不足为怪的。我这个人喜欢读书,大学毕业后读书更多,书读多了,心胸就变得比较宽广,能够宽容很多事情,不愿意把一个人老往坏处想。我多次劝母亲想开一点,母亲一开始却怎么都放不下,后来老了,才把过去的事情看淡了一些。要说起来,温进入老年以后,对从前的某些做法也是心怀歉意的。温的辈份虽说比我母亲低,可他的年龄比我母亲还要大好几岁,但他后来对我母亲十分尊重,见面后一口一个婶儿,喊得亲切极了。我看得出来,温在我母亲面前表现的亲切不是装出来的,完全是发自肺腑。
从性格和趣味上来说,在三个堂兄中,我与温更接近一些。温读过私塾,受孔孟之道的浸染很深,知书达理,礼仪周全,是远近闻名的知客先生。还有,他热爱民间文化,会诵经,会写对联,会打花鼓子,会唱皮影子戏,还会哼许多黄色小调。他思维敏捷,头脑灵活,表情丰富,口齿伶俐,语言幽默,说话风趣,巧舌如簧,出口成章,既能喊五声子,又能攒四句子。我非常喜欢与温在一起玩,一起吃饭,一起打牌,一起走人家。跟温在一起,你会觉得开心,你会觉得有趣,你会觉得快乐,你能把嗓子喊嘶,你能把肚子笑破,你能把哈哈打得跟倒核桃一样。
温也很喜欢我的小说,我大学时代的习作他都看过。后来出版的书,他都要找去读,我小说中的许多细节,他都能复述出来,讲得有鼻子有眼睛。温还特别喜欢听我朗读自己的新作,有时候,我带着刚刚写出来的作品去老家征求意见,先喊一群人坐在身边,再由我读了大家听,然后让听众提意见。开始读的时候,大家听得还比较认真,但过一会儿,很多人就走神了,有几个还打起瞌睡来。但温却与众不同,一直静静地听,默默地想,等我读完后再娓娓地发表高见。每到这个时候,我就更加喜欢他。
因为喜欢温,一旦温提出要我给他帮点什么忙时,我都会满口答应,并竭尽全力。恭开始盖新楼时,温悄悄地找到我,说他与小儿子住一栋楼矛盾重重,想找个地方和大嫂子两个人单独住。我一听就明白了他的意思,知道他想买恭的那个旧房。我问,你和恭是亲兄弟,怎么不直接跟他说?温说,你给他说,他可以便宜点儿。我说,好吧,我去帮你打听一下。
在这以前,我建议良买恭的旧房,良已明确说不卖了。我去问恭,恭说已经有人来看了房,答应出两万四。我对恭说,温想买,你优先卖给他吧。恭也很精明,马上说,他找你出面,肯定是想压价。我说,你们兄弟嘛,卖给他肯定要比卖给别人便宜点儿。恭想了一会儿说,他这个人把钱看得太重,说实话我真不想卖给他,但你发了话,我就听你的,你说几个钱就是几个钱。恭一向很给我面子,在我面前从不说不。我听他这么表态,心里非常高兴。
事情也凑巧,温找我的第二天,良也找到了我。良找我,是想让我出面,要温把他闲在老屋场的土坯房借他用一段时间。我问良为什么不直接找温,良说温太不好说话。我于是答应帮忙说说。我很快找到了温,温说借他还不如卖给他。我问原因,温说,借住一段时间,坍塌了一分钱也卖不出去了。我问温打算卖多少钱,温说卖别人五千,卖良只要三千。
当天晚上,恭请我吃饭,我让他把温和良都喊来了。我想把他们三个人之间的事情放在一起说说。按说,他们三个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而且岁数都比我大,我没有必要为他们之间的事操心着急,说得不好听,还有点多管闲事的味道。但是,我想到我读过大学,是一个知识分子,就觉得自己有责任帮他们搞好关系,让大家相互关心,彼此照应,尽量把生活过得好一点。所以,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只要他们需要我出面,我就会不顾一切地挺身而出。
那晚酒过三巡,我先说,我们兄弟之间不要把钱看得太重,应该有点感情在里面才行!接下来,我就谈了我的意见。我说,恭的房卖别人两万四,现在温要买,就少三千,卖两万一。温的土坯房,卖给别人五千,就三千卖给良。说到这里,我故意停了一下,其实我还有重要的话在后面。我停下来看了看他们三个人的表情,除温之外,另外两个好像不大愿意。我问,你们认为怎么样?温说,我同意!良和恭一起看着我,不说话。这时,我才把刚才没说完的话接着说,为了更加体现亲情,我以前借给恭的三千块钱就不要了,恭再给温免三千,温只给一万八就可以了。温呢,作为关心良,那三千块钱也免了,只当把土坯房送给了良。我一说完,三个人都明白了。他们一起对我说,那就让你吃亏了!我说,我吃点亏不要紧,只要兄弟之间感情好就行。那顿饭吃得非常好,大家都喝了个满脸春色。
可是,没过两天,温突然找到我,说他的几个儿子开了个家庭会,坚决不同意他搬出来单独生活,所以就不买恭的房子了。我听了说,不买没关系,恭还可以多卖点钱。温这时涨红了脸说,我既然不买恭的房子了,那我个土坯房也不能白白送给良了,我倒无所谓,可几个儿子不同意。我一怔问,那你想怎么样?温说,良至少要付我三千,否则不能用。
接下来的事情,我在前面已说过,我给了良三千,让良买了温的土坯房。
温后来还是和他小儿子一起住。住了一年多,矛盾更激烈了。温这时又提出搬出来单独住,但恭的旧房早已卖给了别人。温的大儿子没有办法,就只好另选了一个屋场,决定再给温盖一栋小点的楼房。温的大儿子忙,不能回来招呼,温就只好亲自负责盖房。
温的新房刚砌好一层,不幸的事情发生了。那天往楼上抬预制板,村里的一个小伙子踩虚了脚,从墙上一头栽了下来。送到医院抢救,可抢救无效,小伙子一会儿就断了气。死者才二十九岁,妻子二十几天前刚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还差三天才满月。一个多月后,我才知道这件事,听说赔了死者家属十万块钱。
不久,我回老家办事,特地去看望了温。当时,砌了一半的新房被迫停了下来,温每天坐在工地上的一个简易木板房里,看守着工地上杂乱无章的水泥和砖头。温一下子老了四五岁,一点精神都没有,像一个刚从医院里出来的人。我掏出一千块钱送给他,嘱他自己去买点补品吃。温双手接钱时,实然把我的双手也接过去了。他紧紧地捧着我的双手,话还没出口,泪却先出来了。
说到这里也该打住了。有关他的故事,我在好几个作品中都写到过,比如你在《小说选刊》上读过的那篇《金碗》,其中的一个名叫老温的人物,实际上就是我的大堂兄温。
5
以上,我把我的三个堂兄依次给你说了一遍,拉拉杂杂,啰啰嗦嗦,絮絮叨叨,你听了该不会厌烦吧?
最后,我还想回过头来,再说一说你看到的这张照片。这张照片,是在那天吃了晚饭之后照的,所以光线显得有点暗。本来在饭前我就提出要给他们照,但他们不愿意坐到同一条板凳上。我看得出来,他们之间好像有些矛盾。在饭桌上,我让他们把心中的不快都说出来,开始他们还不好意思开口,喝了几杯酒之后,他们才把话匣子打开。
温先开口说,良买了我的土坯房,可他至今都没把那三千块钱给我。我问良,为什么没给?良对我说,你送我的那三千块钱,我先垫上去盖房了。我问,那你打算什么时候给温?良说,能不能再少点?我实在拿不出那么多钱来。我还没回答,温先说,不能再少了,我卖别人五千呢!我看看良说,你就给他三千吧,我过两天补你一千。良说,那就太感谢你了!
我问良,你还要说什么吗?良说,我与恭的那笔账到现在还没弄淸,按他记的账,我还欠他的,可按我记的账,他还欠我的。我说,那你们两个人肯定有一个人把账记错了。良说,我肯定没记错。恭马上说,我也没记错。我听了一笑说,那就是我记错了!这样吧,你们就扯平算了,如果谁亏了给我说,我再想办法给你们补一些。我这么一说,良和恭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过了一会儿,恭扭头看了看我,好像有话要说。我说,你还有什么说吗?恭想了想对我说,其实我不想说的,但你要我说,那就随便说一件事。我那栋旧房,开始有人要出两万四买,温说要买我就没卖,结果温又不买了,害得我后来少卖了两千,只卖了两万二。恭一说完,温马上睁大眼睛对恭说,要我赔吗?恭笑笑说,我只是随便说一说,谁要你赔了?我苦笑一下说,好了好了,既然不赔就别说了!
从酒桌上下来,我再次让他们坐到同一条板凳上照个像,他们这才坐下来照了这张合影。开始他们坐得很开,我让他们显得亲密点,他们才坐拢去。
你说照片上像古董的这条板凳,是我好不容易从一个废弃多年的地窖里找出来的,如今油菜坡,已经很难找到这种老式板凳了。
责任编辑 吴大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