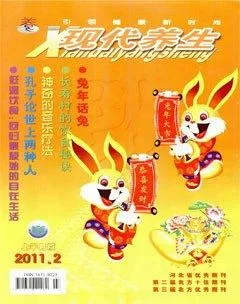古代医学名著中的气功(三)
《巢氏病源》,即《诸病源候论》,由隋代巢元方等撰写于大业六年(公元610年)。该书在论述疾病病因、病理与证候的同时,论治不载方药而专附导引,是中医气功疗法体系基本成熟的重要标志,在气功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古代之导引有广、狭两义:广者包括动功、静功在内的整个气功,也就是郭沫若先生所说的“古人所说的道(导)引,即今人所说的气功”(《奴隶制时代》);狭者仅指动功,即王冰所说的“导引,谓摇筋骨,动肢节”(《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巢氏病源》的导引为广义的导引。
一 “补养宣导”的临证应用
1 导引的辨证应用与对症应用
辨证施治是中医学的核心,在气功疗法中称为辨证施功,《素问(遗篇)·刺法论》虽有相关的论述但系宋人所补。真正意义上的辨证施功始干《巢氏病源》,书中的导引法均附于相应的病证(候)之后。其中不少体现了辨证施功的特点。如《卷一·风四肢拘挛不得屈伸候》谓:“此由体虚腠理开,风邪在于筋故也……其经络虚,遇风邪则伤于筋,使四肢拘挛,不得屈伸……养生方导引法云:手前后递,极势三七,手掌向下,头底面心,气向下至涌泉、仓门,却努一时取势,散气,放纵。身气平,头动,髆前后欹侧,柔髆二七。去髆井冷血,筋急,渐渐如消。”这是一例素体虚弱、复感外邪而致四肢拘挛的“中风(中经络)”案,案中临床表现(“四肢拘挛不得屈伸”)、病因病机(“经络虚……风邪则伤于筋”)、治则治法(“散气……去……冷血、筋急”)、操作方法(“养生方导引法云……”)等,辨证施治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基本俱全。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候”案的病机有“虚”,但在治疗时没有直接补虚,这是因为该患者的主要临床表现为“四肢拘挛不得曲伸”,根据“急则治其标”的原则,当以祛风而使四肢得以曲伸为先。此外,还有对症选用导引法的实例,如《卷十二》:“正偃卧,展两足,鼻纳气,自极七息,摇足三十过止。除足寒厥逆也。”这种导引法专为“足寒厥”之症而设,是对辨证施功的必要补充。全书类似的记载还有多处。
2 导引的应用范围与作用特点
《巢氏病源》中的导引法主要集中在前三十六卷,就病证而言,则以内科为主(其中又以内伤杂病为主),兼及外科、妇科、五官科,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作者对导引法应用范畴的认识,应该说这与目前业界比较公认的气功疗法适应证基本吻合。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在卷一至五,卷十、十四等处,反复强调:“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表明巢氏论治只附导引法,并不是反对“汤熨针石”等治疗手段,而是由于为人们熟知的这些治法“别有正方”,而“补养宣导”在当时可能还不十分普及,故需“附于后”,以方便读者参阅应用,这在同类医著中是绝无仅有的。
《巢氏病源》中导引法的作用,主要体现为补、和、通三大特点。其中的“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具体导引法中“补”的直接表述。如“养神”、“补虚劳”(《卷一·候》),“补气”(《卷三十·候》),“津润六腑”(《卷十四·候》)等。二是通过“候”病因病机中的“虚”间接表达。全书附有导引法的“候”,其病因病机中绝大多与“虚”有关,如:“脏腑虚”、“体虚”、“偏虚”,病邪“随其虚处而停滞”、“荣气虚”、“气血虚”、“人体虚”等。根据“虚者补之”的治病总则,可以推测这些“候”下面的导引法,均有补益作用。书中对“和”的应用仅次于“补”。如:“调和”(《卷一》),“去来和谐……去腰背前后筋脉不和、气血不调”,“能除口苦,恒香洁,食甘味和正”(《卷三》),“调和心气”(《卷四》),“去五脏不和”(《卷五》),“五味调和”(《卷五》)等,涉及和脏腑、和气血、和阴阳等多个方面。至于“通”,有“(使)气流通”(《卷九》),“通脉”(《卷二十七》),“除瘀血、结气”,“除两胁下积血气”(《卷三十六》)等,体现出了导引所具有的疏通经络、行气活血作用。
二 承前启后的导引方法
1 继承和创新导引(功)法
《巢氏病源》对导引(功)法的传承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完整地保留一些优秀功法,如六字诀;二是将古代气功中的某些要素保留在相关的“导引法”中,即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如“蛤蟆行气,正坐,动摇两肩……”(《卷三》),“以两手承辘轳倒悬,令脚反在其上元”(《卷二》),分别融入了五禽戏(《养性延命录·导引按摩篇》),“熊戏者,正仰,以两手抱膝,举头……蹲地以手左右托……”、“猿戏者,攀物自悬……以脚拘物自悬……”的成分。再如行气之“瞑心,从头上引气,想以达足之十趾及足掌心……谓上引泥丸,下达涌泉是也”(《卷一》)中,继承了战国文物《行气玉佩铭》“……天几舂在上,地几舂在下”的铭文经意。《卷十五》的“思脾黄光……心内赤光……肝内青绿光”,继承了晋代《黄庭内景经》中的存想法。
《巢氏病源》对功法学的贡献,还体现在该书对后世功法创编的启示。隋以后直至近、现代的许多优秀功法,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巢氏病源》的影响,特别是至今仍然广受欢迎的八段锦、保健功中的一些操作明显地与《巢氏病源》导引法有关,国家体育总局组织创编的健身气功功法中也可以找到许多《巢氏病源》导引法的“影子”。
2 丰富和发展“三调”操作
形体、呼吸与意念的调整与锻炼(即“三调”),是气功锻炼的三大基本要素。《巢氏病源》除了收集、保留前人多种“三调”方法外,还在不少方面有所发展、创新。如在多处强调的对呼吸次数规定的调息方法,是它书少见的;调心中还有一种特殊的调心方法:“存心念四海神名三遍,辟百邪止鬼,令人不病。东海神名阿明,南海神名祝融,西海神名巨乘,北海神名禺强。”(《卷十》)这是一种意念专注所念词句、“以一念代万念”的调心法,与未经刘贵珍氏调整的“原始”内养功极为相似。如果能将其中过于浓重的宗教色彩加以适当地处理,完全可以用于如今的气功养生与临床。
三 古法导引的经典论述
如上所述,《巢氏病源》完整地保留了六字诀等传统导引法并将其应用于具体的病“候”。此外,该书还从理论上对此类导引法的应用作了论述,且丝丝入扣,堪称经典。
六字诀是一典型的传统导引(功)法,其渊源可追溯至《庄子》的“吹啕呼吸,吐故纳新”;作为独立功法的六字气诀始见于《养性延命录》:“纳气有一,吐气有六。纳其一者,谓吸也;吐气有六者,谓吹、呼、唏、呵、嘘、呬,皆出气也。”并指出:“凡病之来,不离于五脏,事须识根,不识之者,勿为之耳。心脏病者,体有冷热,呼、吹二气出之;肺脏病者,胸背胀满,嘘气出之;脾脏病者,体有游风习习,身痒疼闷,唏气出之;肝脏病者,眼疼愁忧不乐,呵气出之。以上十二种调气法,依常以鼻引气,口中吐之,当令气声逐字吹、呼、嘘、呵、唏、呬吐之。若患者依此法,皆须恭敬,用心为之,无有不差,愈病长生之术。”(《服气疗病篇》)但对这段文字脏腑与六字的对应关系表述不太明朗,从字面上看,脏与字的对应关系分别为:心——呼、吹,肺——嘘,脾——唏,肝——呵;与公认并沿用至今的心——呵、肝——嘘、脾——呼、肺——叫、肾——吹、三焦——嘻(即唏)不一。其实不然,两者完全一致。《巢氏病源·卷十五》曰:“肝脏病者,愁忧不乐,悲思嗔怒,头旋眼痛,呵气出而愈……心脏病者,体有冷热。若冷,呼气出;若热,吹气出……脾脏病者,体面上游风习习,痛,身体痒,烦闷疼痛,用嘻气出……肺脏病者,体胸背痛满,四肢烦闷,用嘘气出……肾脏病者,咽喉窒塞,腹满耳聋,用呬气出。”这里隐含了五行生克理论及“实者泻其子,虚者补其母”治则对于导引临床应用的指导作用。先从五行相生看,肝(木)为心(火)之母,“肝脏病”属实证者,治应泻其子(心)之火,呵为心之本字,故用呵以泻心冶肝实;肺(金)为肾(水)之母,由于“肾脏病”多为虚证,治应补母(肺金),呬为肺之本字,故用呬以补肺实肾(应用时应注意遵循《老子章句》中“呼吸精气,无令耳闻也”的操作要点,和《圣济总录》之“出不可过,过则伤正气”的告戒);“心脏病”中的“若冷,呼气出”的用法,也是这个意思。次从五行相克看,肺(金)为克肝(木)之脏,病理状态下可以发生肺(金)遭肝(木)反克的相侮为病(木火刑金),“肺脏病”而兼见“烦闷”即为木火刑金所致,嘘为肝之本字,用嘘泻肝木以减轻对肺金的过度克乏而治肺,所谓“衰者行其克己字泻之”(素问玄机原病式》);“心脏病”时“若热,吹气出”,其理同。再从三焦学说来分析,中医的三焦学说非常难懂,上海中医药大学凌耀星教授认为,它包含了两个系统,其中之一为气化系统,与水谷精气津液的生化、布散、调节以及废物的排泄等整个代谢功能有关。(凌耀星·论三焦的两个系统,见:王庆其,周国琪主编,黄帝内经专题研究,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2002:108)“脾脏病”出现“痛”、“痒”、“闷”,系水湿困脾胃所致,与三焦有关,嘻为三焦之本字,用嘻激荡三焦的气化功能,以治疗脾湿之病。
总之,《巢氏病源》所收载导引法数量之多、临床应用之广、理论阐述之深,对后世影响之大,在同类书中可谓“绝无仅有”。
(未完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