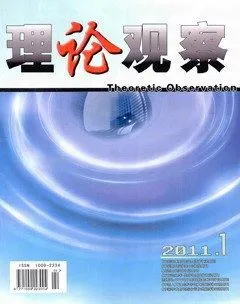价值认同\\知识路径与经验差异
[摘要]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张之洞和张謇兼具君主立宪思想。以政治文化认同为视角,从价值观、知识路径和实践经验三个层面比较两者君主立完思想。儒家心态与近代追求共同构成张之洞与张謇君主立宪思想的价值基础。由于知识途径差异,二者对君主立宪思想,尤其是议会思想的理解同中有异。张之洞君主立宪思想较张謇更具流变性,这很大程度上源于二者思想的不同形成路径。
[关键词]政治文化认同;张謇;张之洞;君主立宪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11)01-0035-03
政治文化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方法。一般认为所谓“政治文化”是指政治系统赖以生成的文化条件或背景,亦即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的集合,主要表现为个人对政治系统以及自我在政治系统中所担任角色的心理取向。政治文化与政治系统互为因果,是个人政治行为和选择的主观的决定性因素,并对政治运行施以影响。学者费根和塔克在政治文化研究中着重强调“行为”的重要地位。按照费根的观点,政治文化是与重复发生的明显行为方式相关的个人思维模式的集成。塔克同样认为,政治文化术语的运用应借用人类学方法。因而文化概念既包括隐在心理,又包括显在行为。这阐释了政治文化研究视角的两个基本层面。价值观是政治行为主体隐在心理的主要构成部分,实践经验则作为显在行为也体现行为主体的政治文化认同。本文选取价值观、知识路径和实践经验三个层面比较张謇和张之洞君主立宪思想。
一、儒家心态与近代追求-张之洞与张謇君主立宪思想的价值基础
儒家心态与近代追求共同构成张之洞和张謇君主立宪思想的价值基础。作为由科场举业进身的士人,张之洞和张謇都体现一种“原儒精神”。二人都经历了人生道路大转折,张之洞由坐而言道的清流健将到起而行之的洋务重臣,张謇由重名节的政坛名士到务实干的实业中流,同时他们又有近代追求。儒家心态与近代追求的交织使他们终生都在超越自我但又未能彻底超越。
张之洞自幼读“经书”,从父辈那里又深染卫道精神。他经历曲折,科举仕途上充满艰辛。1875年他写了《輶轩语》一文,“儒者自有十三经教人为善、何说不详。果能身体力行,伦纪无亏,事事忠厚正直,自然行道有福,何用更求他途捷径哉!”由此可见他早年是用儒家仁、义、忠、孝来维护自身人格。1881年他被调任山西巡抚,从此“究心时政,不复措意于考订之学”。当时俄侵伊犁,日占琉球,激发他研究御敌保边方法,并得传教士李提摩太帮助,有机会阅读西方书籍,“对西方之认识加深,而功利主义之念益强”。1894年出任两广总督,通过与中外人员接触,他发现洋务问题症结所在。与一般庸俗官吏不同,他虽讲仁义,但更强调务实。中法战争后,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开办汉阳铁厂,为湖北近代工业作出贡献。据幕僚辜鸿铭说:张之洞是一个“革新主义者”,他的改革政策,成为中国一股政治潮流,“它最初阻碍了,然后抑制了,最终摧毁和消弭了李鸿章粗鄙的自由主义及其寡头政治集团”。但他的革新一定程度上是其“忠君爱国”思想的延伸。他希望中国经济独立自主,但又怕失去政治方向。所以“他的起点和终点都维系在大小不等的政治利益上”。经济力量与工业实体都绝对从属政治。面对清朝末世,他忠君爱国,尊孔重儒,面对现实他主张革新政治,发展实业;既要维护中国传统,又要追求近代化;主张学习西方,又反对完全“欧化”。儒家心态与近代追求构成张之洞君主立宪思想的价值基础。
儒家心态与近代追求同样构成张謇君主立宪思想的价值基础。他一生以兴办实业著称,在其投入实业之初,即以务实才干和实业精神得到张之洞欣赏。马关条约后,张之洞命张謇为其代拟《条陈立国自强疏》,集中体现张謇兴办实业、振兴国家的设想。他同样步入了科举金字塔顶端,终身以儒者自居,跻身工商界数十年亦未有动摇,有“言商仍向儒”名言传世,身上同样体现一种“原儒”精神。他曾自述:“下走自弱冠至今,三十余年中,受人轻侮之事,何止千百,未尝一动声色,以图报复。唯受人轻侮一次,则努力自克一次,以是至于今日。”他背负着实业兴国的近代追求,又极力保持传统儒士精神定位,儒家心态与近代追求的交织使他既忠君又追求革新。
张之洞与张謇深受儒家政治文化影响,处在晚清国家衰败形势下,为维护君主制,主张顺应近代潮流兴办实业振兴国家,进而又从经济层面振兴实业提出开议院、行宪政的政治主张。因而儒家心态与近代追求共同构成张之洞与张謇君主立宪思想的价值基础。
二、知识途径与观念分殊-张謇与张之洞对君主立宪思想认识的同与异
张謇与张之洞对君主立宪思想的理解,尤其是议会思想的理解同中有异,这源于二者知识途径差异。
由张謇参与起草的奏稿以及为《宪法义解》、《日本议会史》等书所写序文可看出他有关君主立宪的见解:首先,他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政体才能挽救国家危亡;其次,在各国宪法中中国应取法日本。他特别强调“日本以帝国为政策,统于一尊”,即立宪后仍保持“万世一系”的天皇制;第三,极力保证立宪后君权不会削弱;第四,对立宪作了初步规划。他所作《变法平议》最突出的是中央设议政院、府县设议院,但他所指议政院不同于西方议会,议员不由民选而由大臣自辟;权能也只限于提出章程分付行政、司法官员“次第举行”,无监督权,充其量是个咨询机构。府县议会权力较大,有权决定地方税收及财政预算,但人数只限于5人(含议长)。“议政院”的功能是:“采辑古今中外政治法之切于济变者,厘定章程,分别付行法、司法之官次第举行,随时斟酌损益。”这似乎有些三权分立意味,但不仅议员并非来自民选,且议政院“不必专事督促,复蹈操切之辙”。可见它所厘定的“章程”并未要求必须实行,且对“行法、司法之官”也无约束力。议政院实际上是一个无权的咨询机构,并非直正立法机关。府、县议会作用比议政院稍大一些,“其议事草案由知事令交付所议之事会决之,其府、县事以地方税支办者,豫算之额数、征收之方法会决之;可否视同议者多寡,可数多者,数同则决于长。”这似乎像西方的地方议会,但各府、州、县每个议会的议员连议长加在一起也只有五个人,且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仅限于“有家资或有品望者”所以张謇在《变法平议》中提到的议政院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议院。
张之洞君主立宪政体思想主要包括:一是有议院;二是人民可以通过议院议政;三是有健全法制,人人必须遵守法律;四是朝廷(君主)可以凌驾于议院与政府之上。他对议院的认识较张謇进步,“尝考西国之制,上、下议院,各有议事之权,而国科、总统亦有散议院之权。若国君、总统不以议院为然,则罢散之,更举议员再议。君主、民主之国略同”。“外国筹款等事,重在下议院,立法等事,重在上议院,故必家有中赀者,乃得举议员”。他谈及议院四要素:一是议院的功能,有议事与立法之权;二是议院的议政程序,作为国家元首的国君或总统可行使最后否决权;三是议员的资格,必须是有一定财产的人;四是议员产生的方式,应当是选举。这些认识虽不是很完整,但都较为准确。
二者对议院认识的相同之处有:在提出设议院时都维护君权,张謇强调中国应效法日本,即立宪后仍保持“万世一系”的天皇制,张之洞强调朝廷(君主)可以凌驾于议院与政府之上。另一点相同之处是对议会议员都有资格限制,《变法平议》中所拟定各府、州、县每个议会的议员仅限于“有家资或有品望者”,张之洞理解的议会议员也必须是有一定财产限制的人。但同中存异,张謇所指的议政院不同于西方议会,其议员不由民选而是大臣自辟,充其量是个咨询机构。张之洞所指议院议员由选举产生,有议事和立法之权。张之洞列议院的认识更接近西方议院精神。他们观念分殊源于知识途径差异,张之洞了解西方政治途径较多,比如在丁未年他接到进京谕旨后,即要蒯光典到上海邀严复为“顾问”,并亲自致电端方拟调时任上海黄浦疏浚局坐办的辜鸿铭“随同进京”。严复、辜鸿铭都是当时西学权威人物,张之洞通过他们了解西方政治应该比较准确。而张謇作为实业家,更多从经济层面认识西方,其君主立宪思想源于经济实践中产生的对制度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认识。
三、思想变迁与路径差异-从实践经验看张謇与张之洞君主立宪思想
张之洞君主立宪思想较张謇更具流变性,这主要源于二者君主立宪思想的不同形成路径。
(一)张之洞君主立宪思想较张謇更具流变性
张謇君主立宪思想有一个从初期到中期不断明晰化过程,除在辛亥革命前后较短时期内有所游移外,总体来看,思想轨迹较连贯一致。而张之洞则一度在保守和开明之间游走,表现出流质易变特征。
维新变法时期,强学会成立标志着帝党与维新正式联合。张謇作为帝党骨干分子,与维新派也开始联合。《辛丑条约》后,清廷决定推行新政,向各地督抚征求意见。为此刘坤一特请张謇等就“变通政治”事宜,“各为条议”,寄给张之洞参考。张謇写成《变法平议》全面阐述其政治主张,论证变法必要性与紧迫性,把变法内容区分为三大端:一是“必先更新而后旧可涤者”;二是“必先除旧而后新可行者”;三是“新旧相参为用者”。1906年预备立宪“国是”确定,清廷中顽固势力反对,立宪派决心发动全国各界人士向清廷施压,成立预备立宪公会,郑孝胥为会长,汤寿潜与张謇为副会长。1907年清廷谕令设立资政院作为正式议院的基础,各省筹设咨议局。1908年张謇正式筹办江苏咨议局。他在国会请愿运动初期起了重要倡导作用,联合各省督抚及咨议局要求召开国会和组织责任内阁,但反对过激行为。请愿代表向都察院递交请愿书要求朝廷一年内召开国会。但上谕仍坚持九年预备立宪,请愿失败。1910年江苏咨议局在张謇主持下开会再次作出速开国会决议,第二次国会请愿运动再次发起,可清廷仍拒绝提前召开国会,立宪派再次碰壁。张謇则有思想准备,他说:“设不得请,至于三,至于四,至于无尽。诚不已,则请亦不已。”他们很快发起第三次请愿。清廷在各方压力下宣布提前于1913年召开国会,并答应预行组织内阁。张謇在请愿高潮中本打算亲自到北京,但得知上述消息后立即表示“此行可免矣”。这可看出他思想没有太激进变化。尽管清廷宣布提前召开国会,但要求立即召开国会的潮流并未低落,东三省发起第四次请愿,清廷则谕令各省督抚严禁请愿运动,施以高压逼迫立宪派和许多赞成立宪的地方官员走向对立面,立宪派内部不少已转向革命,但张謇仍支持君主立宪,并未改变一贯主张。他向内阁提出三点建议:1.赶快发表正式政见;2.实行阁部会议;3.广开幕府,征辟英才。辛亥革命后张謇还托江宁将军铁良代为奏请立即实行立宪。清军迫于形势命袁世凯组织责任内阁,张謇得此消息颇受鼓舞。虽有一个短暂游走于共和的时期,但紧后他就支持袁世凯,希望袁世凯掌握中央政权,继续提倡君主立宪主张。纵观张謇君主立宪思想,除了辛亥革命前后较短时间游走外,基本上较稳定。
与张謇不同,张之洞则一度在保守和开明之间游走,表现出流质易变特征。维新变法起初他赞成变法,但后期就转向对立面。预备立宪前,他虽对西方宪政有深刻认识,却不主张速开议院。他的《劝学篇》有“暗攻”康、梁维新派意图,其中《明纲》、《正权》等被选进保守派言论文集《翼教丛编》即是明证。庚子年间清廷发布改革上谕,开启清末新政。张之洞在与各督抚大臣商议复奏过程中,思想一度颇为激进,主张“大变西法”,并倡言“必政事改用西法”。思想虽激进,但仍只提倡先仿行上议院。在官制改革中,他态度保守,主张“京官少改,外官缓改”,试图用“真立宪”思想攻击袁世凯借改官制以揽权的“立宪”变异行为,他说,“今日预备立宪,只须合立宪之用意,不必求合于海外立宪国之官制”。他举证同是君主立宪国的日本和德国,其官制也并不相同。“立宪本意在于补救专制之偏。日本立宪之要语曰:‘万事决于公论’。果能事事虚衷咨访,好恶同民,虽官制仍旧,无害其为立宪政体。”张之洞反对改官制并非反对立宪,反而有追求“真立宪”意味。丁未年(1907)是张之洞政治生命中又一转折点,他被慈禧太后召见,在奏对中,他提出“速行立宪”主张,不仅态度坚决,还有具体内容。由此可见张之洞君主立宪思想一度在保守和开明之间游走,表现出流质易变特征。
(二)形成路径差异
张謇是由帝党官员通过兴办实业而成为资产阶级上层代表,更多关注实业发展。张之洞却是老练的洋务官员,权力斗争对他影响更大,他办实业既有经济、更有政治着眼点,朝廷和国家的巩固和自强的政治目的先于经济目的。所以与张謇自下而上从创办实业既而发展出政治主张相比,张之洞有着更高的对政局的综合把握。
甲午战争后,张謇除忙于创办大生纱厂外,还从事其他促进民族工商业发展的社会活动。张之洞多次邀他讨论商务,询问统捐利弊,张謇乘机倡议会同通海地方官员和商人议行“认捐”。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后,张謇正式办理认捐,首先是去说服张之洞,而背后支持张謇的乃是“万目睽睽”的各个行业商人。他在《变法平议》中所列举条目除设议院等政治主张外,还包括银行用钞票、国家应作预计(预算)、改税目、行盐法、定折漕等,这都反映他对实业的关怀。从1901年到1903年,他除了巩固和发展大生纱厂外,还投入通海恳牧公司和通州师范学校创建工作,极力主张在学校中传授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和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但仍未能完全摒弃旧的传统伦理教育,对于当时许多新学之士宣传的自由、平等学说,他更是难于理解和接受。虽有这些局限,但通过兴办教育,他对传统教育有突破,也为他的政治思想奠定基础。总的来说,张謇是以实业家身份发展政治认识和政治态度。他到后来也仍坚持君主立宪,反对革命,这与他的实业思想有很大关系,因为发展实业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愿望,又决定他思想的革新性,而不是传统的封建保守性。
与张謇相比,张之洞办实业更注重政治利益,这使他与张謇从经济到政治向度的思考有所不同。对维新变法的态度体现了权力斗争对张之洞的影响。在维新变法前途未卜时,他绝不会在坚决反对变法、且掌有朝廷实际权力的后党和力图借助维新派力量争取执掌国柄、振刷朝纲的帝党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抉择。他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保持一种双方都可接受的折中形象,将有利于自己在仕途上发展。他在维新运动的成败关键时刻作《劝学篇》,公开表明自己与维新派的根本分歧,目的在“预为自保计”。戊戌政变后张之洞保住了原有地位。辛丑条约后,清廷决定推行新政。张之洞“断以己意”写成三个奏摺:《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摺》、《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摺》、《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两法十一条摺》,奏摺的内容主要包括崇节俭、破常规等老生常谈的条目。据张謇记载,张之洞论立宪的情形是“其论亦明,其气殊怯”,他虽主张立宪,却态度谨慎。因为朝廷对立宪的态度尚不明朗,甚至予以压制,故张之洞一再作谨慎之态。他在清末立宪运动中的思想动态和行为都反映了清廷内的权力斗争。张之洞反对官制改革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与袁世凯的权力斗争。庚子事变后,张之洞成为第一号地方实力派人物;但与此同时他又面临政坛新贵袁世凯的挑战。张之洞1903年进京修订学制时有“人枢”之说,即因奕劻、袁世凯势力排挤而未能如愿。就官制改革而言,袁世凯曾被召进京直接参与此事。袁世凯大有凌驾于张之洞之上的架势。张之洞明白官制改革正是袁世凯进一步控制朝廷大权的极好机会,所以他对官制改革持保守态度。他试图以“真立宪”思想攻击袁世凯借改官制以揽权的“立宪”变异行为。权力斗争对他君主立宪主张有很大影响,与张謇不同,他更多从政治层面考虑问题,二者君主立宪思想的形成路径差异较大。
本文以政治文化认同为视角,从价值认同、知识路径与实践经验三个层面比较张謇与张之洞君主立宪思想。儒家心态与近代追求共同构成张之洞与张謇君主立宪思想的价值基础,由于知识途径差异,两者对君主立宪思想,尤其是议会思想的理解相同之中又存在差异,张之洞对议院的理解更接近西方议院精神。从实践经验看,二者君主立宪思想的形成路径有所不同,张謇作为实业家,是从振兴实业的经济层面上升到政治层面的革新,而张之洞办实业既有经济、还有政治着眼点,甚至可以说,对于他和整个洋务运动而言,朝廷和国家的巩固和自强这种政治目的先于经济目的。所以与张謇自下而上从创办实业既而发展政治主张相比,张之洞有着更高一层的对政局和朝廷权力格局的综合把握。从这三个层面可以看出,张之洞与张謇君主立宪思想同中有异。
[参考文献]
[1]R.R Fagen.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ultureinCuba[M]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