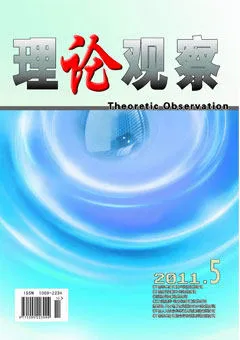韩国古代诗学的中国情结
[摘要]国古代诗学在其结构形态、批评对象、诗学理念及审美追求等诸多方面,与中国古代诗学有着与生俱来的亲缘纽结,因此整个韩国古代诗学中流溢着无法抹却的中国情结。虽然二者存在着众多相似、相类之处,但韩国古代诗学绝非中国古代诗学的简单移植与翻版。韩国古代诗学接受中国古代诗学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对中国古代诗学进行“主体间性”批评的过程。二者之间是一种共同参与,一种主体的分有、共享或一种共同创造的关系。
[关键词]韩国古代诗学;中国古代诗学;中国情结;主体间性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1)05 — 0065 — 04
朝鲜朝中期的诗学家洪万宗在其《旬五志》中,概观韩国古代文学的文脉历程时曾经说到:
我国自殷太师歌《麦秀》以来,世幕华风。文学之士前后相望······北学中原,得师友渊源之学;既东还,延引诸生,奖论成就······至我朝,文章日振,比肩接武,视罗、丽而尤盛,亦不可一、二计也······近世东溟郑公立帜词擅,振耀一代,西汉之文,盛唐之诗,于斯复见。〔1〕
《麦秀》是韩国古代最早发生的文学文本之一,从那时起,韩国古代诗人就“世慕华风”。自高句丽、新罗至高丽的数百年间,“文学之士前后相望”,皆“北学中原,得师友渊源之学”,并传之于后辈。到了朝鲜朝时期,文学之士更是“比肩接武”,与中国文学的互动,尤胜前朝。即便是在其“近世”的诗歌创作中,仍可欣赏到“西汉之文”与“盛唐之诗”的风采神韵。这足以说明韩国古代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的亲缘关系。
韩国古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在创作上的“形似”,其根源在于二者深层的文学理念上的“神似”。换言之,韩国古代文学之所以“形似”于中国古代文学,是由于韩国古代诗学“神似”于中国古代诗学。因此,我们可以说韩国古代诗学有着浓浓的中国情结。
一、结构形态的中国化
韩国古代诗学的形式与体制深受中国传统诗学的“召唤”,同时这种“召唤”也深深地契合了韩国古代诗学的审美“期待视野”,进而造成韩国古代诗学在感性直观上始终彰显出一抹靓丽的中国色彩。
其一,诗学话语。韩国古代诗学自其发生之日起,阐释与倡扬其诗学思想的话语就一直使用汉语,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5世纪中叶韩国本民族语言文字创生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汉语言文字始终是韩国古代社会共同的书面语,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韩国古代诗学主导的话语形式。因此,韩国当代著名汉学家李炳汉曾言:“从很早以前,我们的祖先就使用汉语言文字来写文章和作诗,并且欣赏和评论用汉字创作的诗文,建立了真正的韩国汉文学史的传统。”〔2〕
其二,诗学体制。韩国当代著名诗学家赵钟业曾言:“韩国之诗话起于高丽中叶,实蒙宋诗话之影响者也。”〔3〕纵观整个韩国古代诗学的演进历程,韩国古代诗论的结构形态深受宋代诗话的启蒙,特别是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六一诗话》的体制结构是语录体式的,即由一条条在内容上互不相涉的论诗条目连缀而成。每一则论诗条目,往往只论一人一事,有话则长,无话则短,长短随宜,应变而制,富有弹性,优游自在。如其第10则云:
孟郊、贾岛,皆以诗穷至死,而平生尤自喜为穷苦之句。孟有《移居诗》云:“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乃是都无一物耳。又《谢人惠炭》云:“暖得曲身成直身。”人谓非其身备尝之,不能道此句也。贾云:“鬓边虽有丝,不堪织寒衣。”就令织得,能得几何?又其《朝饥诗》云:“坐闻西床琴,冻折两三弦。”人谓其不止忍饥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4〕
韩国古代诗家对这种论诗体制颇为青睐,从高丽时期李仁老《破闲集》、崔滋《补闲集》、李奎报《白云小说》与李齐贤《栎翁稗说》,到朝鲜朝时期徐居正《东人诗话》、成伣《慵斋诗话》、李济臣《清江诗话》、梁庆遇《霁湖诗话》、洪万宗《小华诗评》、南龙翼《壶谷诗话》、洪重寅《东国诗话汇成》、金昌协《农岩杂识》等等,都沿袭了中国古代诗话(特别是《六一诗话》)的论诗体制与方法,几乎没有什么新的变化与发展。如李仁老《破闲集》中有一则曰:
还康先生日用欲赋鷺鷥,每冒雨至天寿寺南溪上观之,忽得一句云:“飞割碧山腰。”乃谓人曰:“今日始得古人所不到处,后当有奇才能续之。”仆以为此句诚未能卓越前辈而云尔者,盖由苦吟得就耳。仆为之补云:“占巢乔木顶,飞割碧山腰。”夫如是一句置全篇中,其余粗备可也。正如珠草不枯,玉川自美。〔5〕
高丽诗家对欧阳修论诗体制的仿效,即便到了朝鲜李朝时期也没有多大的改观,徐居正《东人诗话》言:
文章所尚随时不同。古今诗人推李、杜为首,然宋初杨大年以杜为“村夫子”,酷爱李长吉诗,时人效之。自欧、苏、梅、黄一出,尽变其体。然学黄者尤多,江西宗派是已。高丽文士专尚东坡,每及第榜出,则人曰:“三十三东坡出矣!”〔6〕
中国学者蔡镇楚先生在论及中韩诗话的关联时指出:“中国诗话论诗条目的组合方式,大致有并列式、承返式、复合交叉式、总分式等四种类型,而朝鲜诗话论诗条目的组合方式,则比较趋于单一化,大致采用并列式的条目组合。如徐居正的《东人诗话》,凡143则,大致按时间顺序编排论诗条目,无须起、承、转、合,随手述录,与宋人初期诗话一脉相承。”〔7〕这说明《六一诗话》所开创的“以资闲谈”的随笔式的论诗传统,作为一种“召唤结构”,暗暗契合了韩国古代诗学的审美期待,并使之在韩国古代诗学的文化语境中相续相禅,生生不息,遂成为一种历史文化的积淀。
其三,以诗论诗的习尚。“以诗论诗”是东方诗学独有的文学批评形式,古代的中、日、韩等国均有此风习时尚。韩国古代诗学如李奎报《论诗》、金时习《学诗》与《感兴诗》、洪良浩《诗解》、申纬《东人论诗绝句》与金正喜《论诗》等等,无不承袭了杜甫《戏为六绝句》与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之以诗论诗的批评样式。
二、诗学内容的中国元素
韩国古代诗学不仅在形式上有着浓烈的中国情结,而且其诗学内容的阐释与衍展,同样有中国元素的大量存在。
其一,专论中国古代诗家。韩国古代诗家在阐释其诗学思想时,往往把中国古代的诗人诗作作为他们的论诗对象。如李仁老《破闲集》在研讨“琢句之法”时云:
啄句之法,唯少陵独尽其妙。如“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萍”、“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户砧”之类是已······及至苏、黄,则使事亦精,逸气横出,啄句之妙,可以与少陵并驾。〔8〕
在此,李仁老认为在汉诗创作上,雕琢诗句的功夫当首推唐代大诗人杜甫,能“独尽其妙”。惟有宋代的苏轼与黄庭坚可与之比肩。
朝鲜朝李瀷《星湖僿说》论李白、杜甫、韩愈等中国诗人的条目,水准颇高,多有自得之见。其“李、杜、韩诗”条云:
屈原之作《离骚》,其志洁,故其称物也芳,兰蕙、菌荪、揭车、杜蘅之属,烂然于齿颊之间,其芬馥便觉袭人,所以为清迥孤绝,能泻注胸臆之十怨九思也。后惟李白得其意,就万汇间取其清明华彩馨香奇高陶铸为诗料,一见可知为胸里水镜,世外金骨也。苟非其物,虽原、白异材,亦何缘做此口气乎?凡诗之能事,多在五字。〔9〕
李瀷对屈原《离骚》“其志洁,故其称物也芳”的认知,其实就是承袭了中国古代诗学所强调的“文如其人”、“诗品出于人品”的伦理批评取向。为论证和强化这一理念,李瀷列举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杰出诗人并结合其诗作来加以阐明。如此的论诗方式,在韩国古代诗学批评中,不胜枚举。
其二,论韩国古代诗家时兼及中国诗人诗作。韩国古代诗论虽时常可见中国的“影子”,但其论诗的对象大多还是以本国、本民族的诗人诗作为主。由于中韩两国文化上的渊源,许多著名的韩国古代诗家不仅曾到中国游历,而且有的还师从中国诗人与学者,耳濡目染,师承递传,因而使得中国的诗学传统渐染于韩国古代诗坛。故此,韩国古代诗家在评论韩国汉诗时,常常与中国古典诗歌进行比较,这样既标示了韩国古代汉诗与中国的渊源,同时又试图指出二者的异同。“李奎报《白云小说》、成伣《慵斋丛话》、金安老《龙泉谈寂记》、李济臣《清江诗话》、申钦《晴窗软谈》、朴永辅《绿帆诗话》等,每论朝鲜‘汉诗’,便涉于中国诗人、诗歌、诗风,论述精到。”〔10〕这在韩国古代诗学中是极为普遍的。高丽时期的崔滋非常推崇李奎报的诗歌,甚至认为李奎报的诗与唐代大诗人李白不相上下:
今世之为警句者,殆未免辛苦之病也。然庸才欲率意立成,则其语俚杂。俚杂之捷,不如善琢之为迟也。善琢苟至于极虑,恐见崔融借髓而死。文顺公(李奎报)《北山亲题》云:“山人不出山,古径荒苔没。应恐红尘人,欺我绿萝月。”此诗置李白集中,未知孰是。〔11〕
又如徐居正在《东人诗话》中,把朝鲜诗人崔恒《咏黑豆》与苏轼《咏海棠》及黄庭坚《咏茶蘼》相较:
古之诗人,托物取况,语多精切。如东坡《咏海棠》云:“朱唇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以妇人譬花也。山谷《咏荼蘼》云:“露湿何郎试汤饼,日烘荀令炷炉香。”以丈夫譬花也。崔文靖恒《咏黑豆》云:“白眼似嫌憎俗意,漆身还有报仇心。”以文人烈士譬黑豆,用事奇特,殆不让二老。〔12〕
其三,使用与中国古代诗学相类的范畴。任何一诗学思想的成熟与诗学体系的完善,其最为鲜明的标志,就是用以阐发诗学理念的范畴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认同。韩国古代诗学所使用的范畴,几乎与中国传统的诗学范畴没有多大差别。如崔滋《补闲集》言:
新警。如文顺公《万日寺楼》云:“渡了几人舟自泛,噪残孤虎鸟犹鸣。”
含蓄。如芮学士乐全《闲居》云:“万里行装春已暮,百年计活夜何长。”
精彩。如文顺公《甘露寺》云:“霜花照日添秋露,海气干云散夕霏。”
飘逸。如陈补阙《江上》云:“风吹钓叟帆边雨,山染沙鸥影外秋。”
清远。如皇祖《北山圣居寺》云:“别洞白云欹枕送,到山明月卷帘迎。”
感怀。如文顺公《病中》云:“病忆故人空有泪,老思明主若为情。”〔13〕
以上品评文学风格的诗学范畴,在中国古代诗学批评中是极为常见的,韩国古代诗家借以品鉴本民族的诗人诗作,这既体现了中、韩古代诗学的亲缘关系,同时也是中国传统诗学范畴的生命力在韩国古代诗学语境中的绵延,体现了中韩传统诗学的互动。这也从另一层面说明,中国古代诗学范畴在融入韩国古代诗学语境后,它不可避免地被植入了韩国本民族的文化色彩。
其四,“使事”、“用事”的中国元素。“使事”与“用事”是指在文学创作中援引前人的典故,以增强文学艺术表现力的一种创作技巧与手法。此法在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由来已久,至唐宋达于顶峰,如唐之李商隐、宋之苏轼、黄庭坚等可谓代表。韩国古代诗家在创作中也十分讲究“用典”,徐居正《东人诗话》言:
古人作诗,无一句无来处。李政丞混《浮碧楼》诗:“永明寺中僧不见,永明寺前江自流。山空孤塔立庭际,人断小舟横渡头。长天去鸟欲何向,大野东风吹不休。往事微茫问无处,淡烟斜月使人愁。”一句、二句本李白“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四句本韦苏州“野渡无人舟自横”,五、六句本陈后山“度鸟欲何向,奔云亦自闲”,七、八句又本李白“总为浮云蔽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句句皆有来处,妆点自妙,格律自然森严。〔14〕
由此可见,韩国古代诗家作诗讲究“句句皆有来处”,但其所来之处往往源于中国典故。对此,崔滋言:“凡为国朝制作,引用古事,于文则六经、三史;诗则《文选》、李、杜、韩、柳。此外诸家文集,不宜据引为用。”〔15〕这在韩国古代诗歌创作中,几成共识。诗人作诗要“使事”或“用事”,而所使、所用之“事”,以中国典故为准的。
三、诗学理念的中国趋向
古代的中、韩两国同处于东亚文化圈,也都深受儒、道、释哲学的影响。由于都以儒、道、释精神为其文化哲学的主干,所以中、韩两国的古代文化在思维习惯以及文化价值取向上有着诸多相似之处。虽然我们不能否认韩国古代诗学是在接受了中国古代诗学影响的前提下发生和发展的,但我们绝不能因此就完全抹杀韩国古代诗学的客观存在及其应有的民族品格。
法国当代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言:“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存在,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16〕雅斯贝尔斯认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在古希腊、印度、中国及以色列等地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最为关切的根本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例如古希腊有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老子与孔子,以色列有犹太的先知们,以他们为中心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经历两千多年的发展已成为各自文化圈内人类文化的主要精神财富。
基于此,我们认为韩国古代诗学在理念及方式上虽与中国古代诗学有诸多交叉之处,但绝不能简单将韩国古代诗学看成是中国古代诗学的复制与翻版。韩国古代诗学与中国古代诗学理念上的趋同,恰好说明了韩国古代诗学与中国古代诗学有着无法抹却的亲缘关系,这种亲缘关系就是韩国古代诗学理念所呈示出的中国趋向。
其一,儒化的诗学观。古代韩国自古就有尚儒尊孔的传统,故此,韩国古代诗学往往强调文学的“美刺”功能,注重诗品与人品,追求文学的人性美。这与中国古代儒家的诗学理念一脉相承。徐居正言:
吾东方之文,始于?三国,盛于高丽,极于盛朝。其关于天地气运之盛衰者,因亦可考矣。况文者,貫道之器。六经之文,非有意于文,而?自然配乎道。后世之文,先有意于文,而或未?纯乎道。今之学者,诚能心于道,不文于文;本乎經,不规于诸子,崇雅黜浮,高明正大,则?其所以羽翼圣经者,必有其道矣。〔17〕
韩国古代诗学的儒化诗教观,体现于韩国古代汉文学的方方面面,对韩国古代汉文学的创作与繁荣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
其二,抒情言志的文学本质观。中国的诗学传统强调诗歌的艺术本质与审美特性在于“言志”与“缘情”,韩国古代诗学对此也极为认同。
诗者言志,虽辞语造其工,而苟失意义所归,则知诗者不取也。〔18〕
夫诗言志也,如善辩者,悠扬反覆,融解无难······〔19〕
诗者,志之发也,有语有意,意深而语浅,故语可了而意不可穷。〔20〕
吁!诗者,出自情性虚灵之府,先识夭贱,油然而发,不期然而然。非诗能穷,人穷也,故诗自如斯哉。但有才者,天亦猜之,于世人又何尤焉,惜哉!〔21〕
夫诗发于情也。古人云有声画,信哉言乎!盖诗与画何异哉?有画其性情者、画其身世者、画其形容者、画其者焉。〔22〕
由此可见,韩国古代诗学所主张的抒情言志的思想与中国传统诗学如出一辙,体现出韩国古代诗学在关于文学本质问题的认识上与中国诗学传统的趋同。
其三,诗宗唐、宋的风尚。诗分唐、宋是中国文学史上持久的论争话题,同样,它也常常影响着韩国古代诗学的审美与理论取向。自新罗后期至高丽初,韩国诗坛崇尚唐诗,推崇的诗人有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等。如李仁老极力盛赞杜诗,曾言:“啄句之法,唯少陵独尽其妙。”“自雅缺风亡,诗人皆推杜子美为独步。”高丽中后期,韩国诗坛则转而大兴宗宋之风。尊崇的诗人主要有苏轼、欧阳修、梅圣俞及黄庭坚等。特别是苏轼声望最重。崔滋云:
近世尚东坡,盖爱其气焰豪迈,意深言富,用事恢博,庶几効得其体也。今之后进,读《东坡集》,非欲仿效以得其风骨,但欲证据以为用事之具,剽窃不足道也。
可见,苏诗的气韵与风骨甚至被高丽诗坛尊奉为诗的典范。徐居正《东人诗话》云:“高丽文士专尚东坡,每及第榜出,则人曰:‘三十三东坡出矣!’”尚苏之风在韩国刮了数百年,声势之浩荡,一直蔓延至李氏朝鲜。由南龙翼《壶谷诗话》言李朝“文体专尚东坡”、金万重《西浦漫谈》亦云“国初承胜国之绪,纯学东坡”,可见一斑。
时至近世,韩国诗坛由于受明代七子“诗必盛唐”复古思潮的影响,崔庆昌、白光勋与李达携“三唐诗人”的盛誉乘势而起,柳梦寅言:“近来学唐诗者皆称崔庆昌、李达。”当时的韩国诗坛日益表现出尊唐黜宋的审美取向,如所谓“似唐”、“法唐”、“逼唐”、“不减唐人”、“可肩盛唐”、“盛唐风格”等批评话语不绝于耳。与此同时,鄙视宋诗的声音亦此起彼伏。“诗至于宋,可谓亡矣。所谓亡者,非其言之亡也,其理之亡也。”〔23〕至李朝英祖、正祖年间,韩国诗坛又流露出青睐清代乾嘉诗风的倾向,于是又掀起了“唐宋兼宗”的热潮。
关于唐诗与宋诗的不同,韩国古代诗家亦有自己独到的认知,如申钦在《晴窗软谈》中指出,唐诗与宋诗各有千秋,理应分别视之:
唐诗如南宗,一顿即本来面目;宋诗如北宗,由渐而进,尚持声闻辟支尔。此唐、宋之别也。〔24〕
同时,申钦也严正地批驳了诗分唐、宋(尊唐抑宋或尊宋贬唐)思
想的偏执:
世之言唐者斥宋,治宋者亦不必尊唐,兹皆偏矣。唐之衰也,岂无俚谱?宋之盛也,岂无雅音?此正钩金与薪之类也。〔25〕
对唐诗、宋诗如此公允的品评,即便在中国诗学批评史上也颇具价值。
四、韩国古代诗学对中国古代诗学的“主体间性”批评
韩国古代诗学虽然在诸多方面都流露出血亲似的中国情结,但韩国古代诗学绝不是中国古代诗学的照相式的复制,相反,韩国古代诗家在汲取中国古代诗学精华时常常秉持着清醒的民族自我意识,从众多韩国古代诗家著述的书名,如《东人诗话》、《海东诗话》、《东国诗话》、《东人论诗绝句》、《东诗话》、《东国诗话汇成》、《东诗丛话》、《海东诸家诗话》、《朝鲜古今诗话》、《小华诗评》等等,即可见一斑。至于诗学话语中所宣称的“吾东”、“我东”、“我东人”、“吾东方”、“吾东国”、“东诗”等等称谓,更是随处可见。由此,我们可以断言,韩国古代诗学对中国古代诗学的接受绝非简单、机械地受容,而是一种“主体间性”的批评。
主体间性的主要理念是研究或规范一个主体是怎样与完整的作为主体运作的另一个主体互相作用的。认为文学实践主要表现为人与人之间所进行的社会交往活动。这种“主体—主体”关系所体现的是互为主体的双方间的“对立、对峙——对话、交流”。这种主体之间的交流首先是一种共同参与,一种主体的分有、共享或一种共同创造。它强调相互间的投射、筹划,相互溶浸,同时它又秉有一种相互批评,相互否定,相互校正、调节的批判功能。在此基础上展开了主体间本位的广阔天地,不断达成主体间的意义生成。〔26〕我们所谓韩国古代诗学的中国情结,实质上就是韩国古代诗学对中国古代诗学的主体间性批评,这种情形不是只体现于韩国古代诗学与中国关联的某一方面,而是体现在二者关联的所有层面。
前苏联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巴赫金认为,碰撞后的不同文化必定会保有其各自的文化主体性,即文化自我首先必须是一个“我”,否则就不能称其为文化。所以,他更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性、对话性,认为交流与对话是文化的基本存在方式。同时,文化之间的交往本质上不是独白,不是一方向另一方的灌输与强制接受,而是在平等、民主的对话交流中进行卓有成效的理解,进而造成意义的增殖与再生。〔27〕对于韩国古代诗学的中国情结,我们亦应作如是观。
〔参考文献〕
〔1〕赵钟业.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4卷)〔M〕.首尔:太学社,1996:640-641.
〔2〕郑判龙.韩国诗话研究〔M〕.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1997:22.
〔3〕赵钟业.中韩日诗话比较研究〔M〕.台北:学海出版社,1984:227.
〔4〕欧阳修著,郑文校点.六一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9.
〔5〕赵钟业编.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1卷〔M〕.首尔:太学社,1996:49.
〔6〕赵钟业编.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1卷〔M〕.首尔:太学社,1996:444.
〔7〕蔡镇楚.比较诗话学〔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272.
〔8〕赵钟业.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1卷〔M〕.首尔:太学社,1996:49.
〔9〕赵钟业.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6卷〔M〕.首尔:太学社,1996:715.
〔10〕蔡镇楚.比较诗话学〔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274.
〔11〕赵钟业.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1卷〔M〕.首尔:太学社,1996:102.
〔12〕赵钟业.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1卷〔M〕.首尔:太学社,1996:500.
〔13〕赵钟业.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1卷〔M〕.首尔:太学社,1996:108.
〔14〕赵钟业.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1卷〔M〕.首尔:太学社,1996:416.
〔15〕赵钟业.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1卷〔M〕.首尔:太学社,1996:107.
〔16〕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4.
〔17〕徐居正,等.东文选:卷一〔M〕.首尔:民族文化促进会,1982.3.
〔18〕赵钟业.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第2卷)〔M〕.首尔:太学社,1996:525.
〔19〕赵钟业.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第3卷)〔M〕.首尔:太学社,1996:604.
〔20〕赵钟业.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第6卷)〔M〕.首尔:太学社,1996:668.
〔21〕赵钟业.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第2卷)〔M〕.首尔:太学社,1996:534.
〔22〕赵钟业.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第3卷)〔M〕.首尔:太学社,1996:596.
〔23〕许筠.覆瓿集·卷四·宋五家诗序〔M〕.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80:251.
〔24〕蔡镇楚.比较诗话学〔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289.
〔25〕邝健行,等.韩国诗话中论中国诗资料选粹〔M〕.北京:中华书局,2002:107.
〔26〕金元浦.文学解释学〔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254.
〔27〕巴赫金.巴赫金全集中文版(第4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370.
〔责任编辑:李允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