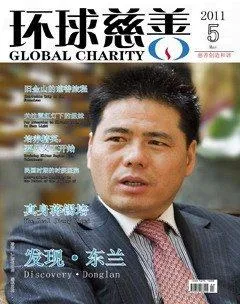纯静的山 纯朴的人
带着期待去,带着满足归。东兰之行令人难忘。
此前,东兰对我来说不过是一个毫无概念的地名,四天后,我却不由自主地留恋起这个小小山城。它给人的感觉是纯朴和清新,景色如是,人亦如是。
南宁到东兰好几个小时的辗转,到达时已是天黑,兴奋好奇的心情难免有些疲惫了;此时的东兰也早已笼罩在黑夜之中,平添了一份神秘感。没有车水马龙、灯红酒绿,这里的夜是寂静的,十点左右,县城的大路上已少有人活动。只有道旁树上的七彩纸球和路上方横拉的彩旗,在昏黄的路灯下依旧醒目,让小城呈现出一种含蓄的喜感。
宁静淳朴的小山城
翌日早起,有机会细细打量这个新鲜的小城了。与其说这条九曲河穿城而过,不如说县城本是傍河而建。河两岸的房屋错落有致,流淌清水的河上架起数座彼此相望的桥梁,两翼又都伴着苍翠的高山,居民悠闲地往来其间,颇有几分世外桃源、怡然自得的景象。
小城,小而宁静,小而和谐。此次大型的铜鼓节庆典无疑是小城的盛事,不知大量而来的各色外地客会不会打扰居民们的宁静,又在他们眼中留下怎样的印象?而我作为一个外地人,却记住了他们的纯朴和善良。
他们的纯朴特质,常常是“刻”在脸上的。岁月和劳作刻下的皱纹,见证着他们的勤劳和汗水,还有那发自内心的朴实的笑,都立刻给人一种亲近的安全感,让人不由得想要上前去打声招呼,攀谈几句。这感觉,是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里难得有的“奇怪”心情。
背孩子的妇女,卖绣花鞋的老太太,摆摊的中年男子,跟你笑起来全是咧着嘴,又含着些许难为情,有时用手捂起来,这也许叫“憨态可掬”。两个完全陌生的人,在这样的笑容里,瞬间就消却了隔膜。
看得出来,小城里的居民把这少有的盛典也当成了自己的节日。当然,在外地人面前,他们则更多地表现出来作为本地人的热情。随便问个路,打听个什么情况,不但被问的人会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热心指引,旁边听到的人也都会走过来补充,让我们这些外地人确是受宠若惊。
我想,在规规整整的大城市生活惯了的人,会不会尤其不适应这样的热情和纯朴呢?就像突然走进了这里美丽的崇山峻岭,绿水田园,除了初见的新鲜感,还能否留下些深入内心的印记呢?
东兰,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地方,这里的人们又是怎样的一群人?在其后的两三天里,我更细致地去感受和聆听,也得以更深入地认识东兰。
革命圣地,烈士之乡,将军之乡,这是关于东兰的过去。于是我知道,纯朴之外,东兰人更是有自己的性格和追求。是怎样的魄力让这里的先辈勇敢站起来追求自己的幸福和自由,又是怎样的风骨,让他们能团结一致,为理想不惜生命?遥想当年,在亲切之余我油生敬意。
边远地区,贫困地区,这是东兰的现实。远离行政中心,交通不便,石山多,耕地少,让东兰的发展面临不少阻力。所幸我在当地人的脸上所看到的更多的是自足和自得,这不妒不争、努力创造,何尝不是与革命精神相通的豁达。
东兰还是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占全县人口百分之九十,民族特色在城乡随处可见。妇女们用包袱皮把孩子背在身上、又用花布把孩子蒙头蒙脸盖起来的背法,以及老太太们的穿着,都透着浓浓的西南少数民族风情。
在县城西边山上的烈士陵园广场,其时距纪念革命先烈的活动开始还早,忽听得不远处的一棵大树下,三五个妇女在休憩的间隙就唱起来山歌,那么的生活化,却也那么的动人。
那原汁原味的调子,清脆而温馨。虽听不懂歌词,我也远远地听得入了神。同去的一位同仁老师大概也颇为所动,等她们唱完,意犹未尽又请她们再来一曲。
并无扭捏,她们只互相笑了笑,歌声又起。也许在她们看来,生活就应该如此,快活自在,歌声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没有惺惺作态,外人也无从干扰;她们岂是再唱一首给我们听,她们就是继续在自己的人生里放歌而已。
历史悠久的铜鼓文化
说到东兰,不得不提铜鼓;而说到铜鼓,更不得不提东兰。“铜鼓之乡”名不虚传,这也正是我此行的最大目的。忘掉统计,忘掉宏观,我所见的,已足够证实铜鼓在东兰人生活中的地位。
瑶寨的铜鼓表演固然令人心动,铜鼓节的百面铜鼓齐鸣更是震撼。而最能打动我的,是东兰的普通百姓对铜鼓的珍惜和津津乐道。
三卡屯41岁的瑶族老乡黄建民在表演铜鼓后接受了我的采访,他告知我,牙叼铜鼓表演看来精彩,学来却颇为不易。
铜鼓几十斤重,却只用牙齿咬着边缘拎起来,我们头一回看的人觉得像杂技,黄建民却告诉我这是他小时候忍痛练习的结果。但他与他的老乡们乐在其中。铜鼓就是他们的信仰,是传家宝,这里的男女老少个个都会敲铜鼓,“在我们屯,不会敲铜鼓是很难交到朋友的,”黄建民说。
逢年过节,红白喜事,铜鼓是重要的乐器。有时候,却也是游戏的道具:在他们屯里,男人女人会敲铜鼓比赛,赌些手帕、香烟之类的小玩意,谁能持续快速敲鼓谁就能胜出。
居住在县城的韦万义老先生告诉了我他与铜鼓的故事。如今83岁的韦老,在自家的房子里摆放着二十多面大小铜鼓。每有客至,他总是不知疲倦地介绍他的收藏,并“不失时机”地表演上一小段。平日里,他也会常常敲起心爱的铜鼓。
“从小就喜爱铜鼓,一听到铜鼓的声音,心情就好。”这或许就是所有东兰人民对于铜鼓的感情寄托吧。
在韦老所有的铜鼓中,除了有三面是祖传的,其余都是他花了多年心血从各地收来的。1976年,韦老开始了自己的收藏之路。那时他恰巧在一个废旧物品回收站看到了三面铜鼓,便出价买了下来。共花了180块钱,这是当时他全家一年的收入。他甚至还去云南等地农村回收铜鼓,才有了他现在的收藏。爱鼓如命,名副其实。
与铜鼓文化节同一天开门迎客,陈耀灵先生的私人铜鼓博物馆,则更体现了铜鼓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不同造型,不同年代的铜鼓,共同阐述着东兰人民与铜鼓的亲密关系。
青山秀水亦多情
人文与山水总是相联。有幸,此行我游览了东兰的人文盛迹,也见识了那里的山清水秀。
为了见识久闻大名的红水河“第一湾”的晨曦,我们摸黑出发,天蒙蒙亮就到达了。车到山前无路处,只见脚下薄雾间一湾碧水在峰峦叠翠间静静流淌,好似仙境。
沿着盘山公路步行下至河边,登船,沿宽阔的河面前行。两岸山形变幻,雾气缭绕,翠色葱茏,空气清新宜人,俨然身在梦境,又好似穿行于一幅无边的水墨画卷里。船头相谈欢笑,乐之至也,而纵有诗情,言辞难表。
船沿着河行了一个上午,其间经过多少山,拍了多少照,到后来都已朦胧难记,回想起来的,只有那淡淡的山水雾气,黑白的临水小镇,俊美的跨梁和飘逸伟岸的凤尾竹。
随后,又来到被月亮河与凤尾竹环抱的长寿之乡江平村,风光与豪情并存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等胜迹,一天下来,虽是走马观花,也足以流连忘返。其间大巴在险峻的盘山公路上穿行,却不像第一次那般担忧,多了份从容。不知是耽于这迷人的风景,还是浸染了革命先辈的胆魄?
临走时最是难舍。因为我不知何时还能遇到这样纯静的山水,这样纯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