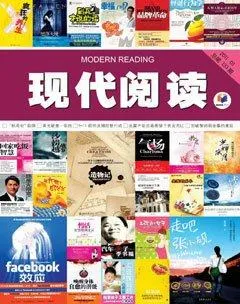郭嵩焘 中国第一个驻外大使的惨淡际遇
引言 1876年,因滇案签定的中英《烟台条约》,其中一条是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并任驻英公使。
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互派大使,这是近代国际交往的惯例和常礼,但中国从来以“天朝上国”自居,从无派大使到“属藩”之说。而近代以来却又屡遭西方列强侵略,一方面感到与“蛮夷之邦”的“洋人”打交道有失身份,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屈从列强的压力和横蛮要求。这种对“洋人”既鄙视又恐惧的心理与坚持传统“礼仪”、中外从不互派大使的观念紧紧纠结一起,更不愿派出驻外大使。互派大使,那意味着承认“天朝上国”的崩溃。所以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争论最大、咸丰皇帝和王公大臣最为痛心疾首的一条即外国公使驻京。1858年中英天津谈判时,中方代表曾表示皇帝宁可一战也绝不让步。但在英国代表“与其将来北京挤满了外国军队、不如现在就痛快答应”的武力威胁下,咸丰皇帝最终勉强同意此点,批准了《天津条约》。
同意外国公使驻京的消息传开,清廷大员一片怒斥,认为撼动国体。咸丰皇帝则又强调外国公使驻京是只准暂住,而且“一切跪拜礼节,悉遵中国制度,不得携带眷属”;如果英、法两国以条约为依据一定坚持其公使常驻北京,则他们“必须更易中国衣冠”。同时又要中方谈判代表改订部分条款。英、法侵略者拒绝改订条约之议,决心以武力将其公使“送入”北京。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焚烧圆明园,咸丰皇帝仓皇出逃,不得不接受侵略者的全部要求,外国公使“史无前例”地开始常驻北京。但是,以后的十几年中,中国仍一直没有外派驻外大臣。对此,西方列强一直不满,认为这表明清政府仍以“天朝上国”自居。所以在中英因“马嘉理案”谈判时,英方一直坚持中国要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并任驻英公使。
《烟台条约》规定中国必须派高官出使英国,但派谁出去却是清政府的一大难题。因为当时人们不仅将出洋视为畏途,更将离开“礼仪之邦”到“蛮夷之邦”视为一件奇耻大辱,出洋者将名声扫地,很难找到愿意出洋的高官。同时,出使者又必须懂“洋务”,在清政府的高官中懂洋务者实在太少。
选来选去,清廷决定派在政坛几起几落的湖南人郭嵩焘担此重任,因其向以懂洋务著称。早在1856年春,他随曾国藩帮办军务时到过上海,对西方的种种器物和某些制度有了感性的了解,并认真研读了使他惊讶不已的《日不动而地动》等自然科学图书,倾心西学,后来一直参与洋务。他曾大胆提出由商人办理近代企业,在当时被人视为惊世骇俗之论;在洋务派与顽固派的斗争中,他以自己的学识不遗余力为洋务派辩护,成为洋务派的重要一员。
1875年初,辞官在家闲居8年的郭嵩焘在李鸿章的推荐下,又作为懂洋务的人才奉诏来到北京,并被慈安、慈禧两太后召见。
郭嵩焘被任命为出使大臣的消息传来,他的亲朋好友都认为此行凶多吉少,为他担忧,更为他出洋“有辱名节”深感惋惜。更多的人甚至认为出洋即是“事鬼”,与汉奸一般,还有人编出一副对联骂道:“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当时守旧氛围极浓的湖南士绅更是群情激愤,认为此行大丢湖南人的脸面,要开除他的省籍,甚至扬言要砸郭宅,而李鸿章却对他出洋表示鼓励、支持。为了表示“平衡”,清廷又任命了坚决反对洋务运动的顽固派刘锡鸿担任副使。
在强大压力下,郭嵩焘几次以告病推脱,但都未获准,终在1876年12月从上海登船赴英。行前,朝廷应总理衙门之奏请,诏命郭嵩焘将沿途所记日记等咨送总署。此正合郭氏之意,他早就想将自己所了解的西方富强之道介绍给国人,使国人从“天朝上国”、视异域文明为异端的迷梦中惊醒。经过几十天的海上航行,他于1877年1月下旬到达伦敦,立即将这几十天极为详细的日记题名为《使西纪行》寄回总署。在日记中,他不仅客观记述了所见所闻,而且对这些见闻做出了自己的评价。他希望尽可能让国人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摆脱夜郎自大的状态。但总理衙门刚将此书刊行,立即引来朝野顽固守旧者一浪高过一浪的口诛笔伐,一时间群情汹汹,有人痛斥他对外国“极意夸饰”,有人上奏,认为应将郭嵩焘撤职调回。由于找不到合适人选,清廷未能将他召回,但下令将此书毁版,禁其流传。
但在朝野的一片反对声中,李鸿章却对郭嵩焘的《使西纪行》表示支持。郭嵩焘出洋后,李鸿章与他密切通信。
李鸿章的支持,对面临巨大压力的郭嵩焘当然是莫大的鼓励。但在驻英大使内,郭嵩焘还面临着与自己的副手刘锡鸿愈演愈烈的“窝里斗”。刘得到清政府中一些大员的支持,暗中监视郭的一举一动,从一开始就不断向清政府打郭嵩焘的“小报告”,列出种种“罪状”。清政府担心内斗会影响外事工作,于1877年4月改派刘锡鸿为驻德公使。刘与郭同为公使,使刘气焰更高,对郭的攻击更加猛烈,甚至达到“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程度。如有次参观炮台中天气骤变,陪同的一位英国人将自己的大衣披在郭嵩焘身上。刘锡鸿认为“即令冻死,亦不当披”。巴西国王访英时郭嵩焘应邀参加巴西使馆举行的茶会,当巴西国王入场时,郭嵩焘随大家一同起立。这本是最起码的礼节礼貌,但刘锡鸿却将其说成是大失国体之举,因为“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国主致敬”!更严重的罪状是说郭嵩焘向英国人诋毁朝政,向英国人妥协等等。由于朝中有人支持,刘接连上奏朝廷,发函总署及南北洋大臣,诬陷郭嵩焘。对刘的陷害,郭嵩焘当然备感愤怒,竭力为自己辩诬,并且退意渐浓,多次上奏要求调回国内。
对郭刘之争,李鸿章当然支持郭嵩焘。1877年11月初,李鸿章致书郭嵩焘,密告朝廷将以李凤苞取代刘锡鸿出任驻德公使,要郭不要称病乞退,同时劝郭千万不要公开与刘决裂,让外人见笑。由于清政府外派大臣事宜渐次开展,一时人才奇缺,于1878年2月底又任命郭嵩焘兼任出使法国钦差大臣。然而,刘锡鸿等人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于5月6日列举郭嵩焘十大罪状,洋洋数千言,大到造谣说郭嵩焘总“向英人诋毁时政,谓中国将作印度,或被吞并于英俄”,小到郭嵩焘不用茶水而改用银盘盛糖酪款洋人、想学外语等等全都是罪过。其用心之刻毒、言辞之激烈严峻,超过以往。
这些“罪状”,总理衙门无法核查,不能全信,又不敢不信,左右为难;同时,面对驻外使臣间势同水火的矛盾,总理衙门也感到难以调和处理,几次征求李鸿章的意见。李鸿章当然是为郭嵩焘辩护,并借他人之口指责刘锡鸿。但是,朝廷内外反郭力量甚强,纵然李鸿章权倾一时,他的免刘保郭之论根本不可能为清政府接受,只能暂时维持郭、刘现状。但结果仍然是驻英与驻德大臣二人的关系势同水火,满城风雨,无法调和。在郭、刘二人“内耗”日甚一日、反郭拥刘者众的情况下,清政府决定将郭免职调回,不少人还想将郭嵩焘查办治罪。
1878年8月25日,清政府下令将驻英公使郭嵩焘、驻德公使刘锡鸿同时召回,由曾纪泽、李凤苞分别继任。在这一纸“公平”对待郭刘二人的命令下,潜藏着两大政治力量的激烈较量,是经过了一番角力后才达到这种“平衡”的。
1879年1月末,郭嵩焘离开伦敦,启程回国。到达上海后,他心力交瘁,请假归乡。5月回到故乡长沙时,等待他的却是全城遍贴揭贴,指责他“勾通洋人”。不久,朝廷便诏允其休。这样,他在一片辱骂声中离开了政治舞台。以后他仍时时深忧国事,常向友人倾谈自己对社会、政治的种种看法,一些开明之士对其学识也盛赞不已,对其不为朝廷所用深为惋惜,但他终不再被朝廷起用。
(摘自山西人民出版社《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 作者:雷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