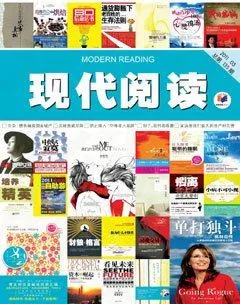孙健 从国务院副总理到机械厂总经理
“文化大革命”结束已经30多年了,他离世也已整整10年,人们还记得他吗?
他叫孙健。1975年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经周恩来总理提名,他和大寨农民陈永贵同时被选为国务院副总理。当时社会上流传这样一种说法,周总理到天津视察,市委工业书记孙健汇报工作时头脑清晰,各种数字烂熟于心,立刻获得了总理的好感。
孙健于1951年进入天津内燃机厂学翻砂,成了一名地道的铸工,他曾连续7年没回家,凭着苦干、实干加巧干,一步步走上生产组长、班长、车间主任的职位,后来成为厂党委书记。不久,他被提拔到机械局当了负责抓生产的“革委会”副主任。局里派人到他的老家调查,发现孙健的父亲和妻子儿女都在农村,住一间土改时分的破房,冬天透风,夏天漏雨。父亲病重,妻子上侍候老,下照顾小,还要下地挣工分,积劳成疾,身体很虚弱。调查者回到局里,向领导汇报:“只有孙健才能忍受这种困境,再不解决就要给社会主义抹黑了。”他的家属这才得以调进天津,妻子庞秀婷成了一名工人。
后来,孙健在“选拔接班人”时成了市委书记,1975年又当选国务院副总理。
这位铸工出身的副总理,平时愿意干实事,也能吃苦耐劳,却不懂得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也为属下争取些“利益”。
同是副总理的谷牧曾问他:“怎么不把家属接来?”孙健说:“你这当师傅的还不知道有这么一条规矩吗:学徒期间不许带家属。”他把自己当成了国务院的学徒工。但他的心情却不像说话这样轻松。当上市委书记不久,他就患上了失眠症,升为副总理后失眠症愈发严重了,有时整夜整夜睡不着觉。
“四人帮”垮台后,他在副总理的位子上又干了两年。1978年夏天他正在外地检查工作,突然接到电话,通知他停职检查。才40多岁的他要求回天津。回到天津后,孙健要求回内燃机厂,市里管分配的同志却叫他去天津机械厂,这个厂对他不熟悉,估计麻烦会少一点,但仍有些不放心,问他:“内燃机厂的人会不会到天机厂贴你的大字报?”
“不会。”
“你这么肯定?”
他说不出具体理由,但他估计得不错,后来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走进内燃机厂,3小时内都出不来。工人们都愿跟他说几句话,但从不问他到底犯了什么错误,他也从不讲过去的事。
孙健最终还是被送到天津机械厂接受“监督改造”,上级允许他与妻子庞秀婷见一面。他对善良、温顺、胆小的妻子讲了三条:“一、我不会自杀,我对自己心里有底。二、相信现在的政策。三、你从来都是我的靠山,这次更得依靠你,听见别人说我什么也别当真,带着孩子好好过日子。”
孙健从不给人以强者的印象,他顺从自然,默默地接受和理解命运。机械厂的工作很快吸引了他。严重的失眠症在被监督劳动中却一下子好了,不要说晚上睡得踏实深沉,就是中午,饭碗一放,或躺或坐,不消10秒钟就能入睡。
他每天从家里带一盒饭,早晨吃1/3,中午吃2/3。有时在厂里吃午饭,他总是买一碗豆腐脑、4两大饼或4两馒头,花费不到2角钱。工人们问他:“你怎么老吃这个?”他回答得很坦然:“这对我的胃口,也符合我的经济条件。”
一次,他去起重设备厂买吊车,厂长正在接待外国客户,听说孙健来了,叫供销科把他扣住,非要请他吃饭。这位厂长过去在机械局生产处工作,有一次到市里开会,散了会已是晚上8点多,大雨如注,他和另外两名基层干部饿着肚子在门洞里等待雨停,被孙健撞见,孙健让司机先送他们3个回去,自己等在宾馆的门洞里。小事一桩,孙健记不得了,别人却记得很牢。此类事情还有不少,他“倒霉”以后开始收到回报。
1985年初,上面来了精神:孙健可以当中层干部。厂长把被称为“天机厂重点的重点,天机厂的未来和希望”的一个工程——投资4000万元,全部引进德国设备,两年后成批生产摩托车发动机——交给了孙健。孙健要求办公室人员每天提前10分钟上班,晚10分钟下班,他自己则每天提前半小时进厂,工作紧张时就吃、住在厂里。孙健丢掉所有的心理负担,以一个业务员的姿态,每天脚不拾闲,上至市政府、各部委、区局等大机关,下至厂矿、街道、个体商贩、农村包工队,到处都有他的身影。
上级机关里有不少孙健过去的上级、下级和熟人,他忘记了过去,以基层办事员的面目出现,反而受到大家欢迎。谁也不会忘记他曾是本市管工业的书记,曾是国务院副总理。
孙健的妻子摔断了腿,无人照顾,他每天赶回家做饭,服侍妻子吃完饭再骑车赶回工厂。工作又苦又累,他却浑然不觉,反而觉得比过去轻闲得多。他一直在第一线,从没松过套。当天津市委工业书记的时候,他跑下去看过近600家企业,是第一线的书记。进京后第一次参加国务院会议,周总理给副总理们分工时说:“孙健最年轻(当时他39岁),多到下面跑跑,花3年时间掌握情况,便于今后工作。”他仍然是第一线的副总理。现在,孙健用了1年多的时间,盖起了近2万平方米的3层主厂房,并安装好全部设备,天津机械厂又一项拿人的产品——摩托车发动机正式投入生产。机械局基建处的同志说:“这个大楼有一半是孙健的。”
不久,孙健被调到中国机械工业安装总公司天津开发区公司做“经营总经理”——多么时髦的头衔,每月的工资也升到了97元。我在一个炎热的下午去拜访他。那是一大片地震前盖的老楼群,我找到77号,向站在楼洞口的一位老太太打听孙健住几楼。老太太尚未开口,一楼的一个房门开了——是孙健听到声音迎了出来。他们住着一个偏单元,阴面儿的小房间10平方米左右,搭着一张大床,有几件旧式家具。阳面儿的大房间约14平方米,收拾得像个简单的小会议室。除了墙角的两个小书架(里面放着马、恩、列、斯、毛、刘、周、朱等经典著作和《二十四史》)和另一角上的冰箱,其余的家具全是沙发,一对三人大沙发,一对单人沙发。沙发上罩着套子,扶手和靠背处在套子外又垫了毛巾,用大号别针固定着。屋里很整洁,水泥地面一尘不染。我问孙健:“你难道经常在家里召开会议?”
他说:“我自己家人口就不少,到我家里来的人更多,特别是家乡的亲戚朋友,来天津旅游、订货送货、做买卖,不愿住旅馆,都在我家里安营扎寨。白天,这间屋里可以吃饭待客,晚上打开沙发是两张大床。”
他们夫妇都是河北省定兴县人,乡里乡亲自然少不了。孙健说:“我没有什么太大本事,几十年来就混下了一个好人缘儿。”
这是一句实在话。
1987年初,天津机械厂召开表彰大会。厂部给为数不多的几个厂级先进人物准备的奖品是纯羊毛毯。当厂长念到孙健的名字时,全场鼓掌。大礼堂里响起《运动员进行曲》,先进人物上台领奖,当孙健从厂长手里接过奖品的时候,工人们为他鼓掌了好长一阵子,热烈程度在工厂大会上很少见。有人还站起来喊:“应该!”“孙头儿,你这个先进名副其实!”
他又站在台上了,又面对着热情的群众。他没说一句话。抱着奖品毛毯,他感到很暖和,把前胸都焐热了。人民的记忆就是历史。群众一直在关注着他。
同事们有时和他开玩笑:“你是上去得糊涂,下来得也糊涂。”他自己解嘲:“糊涂到家就是明白。”
(摘自广东人民出版社《历史深处》 主编:王家声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