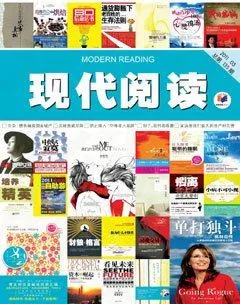被权力活用的制度
引言 真正决定制度执行与否,执行好坏的是私底下的衍生权力。既然人是活的,衍生权力也是活的,制度也就“活”了起来。
北宋的监狱里有一条规矩:新到的犯人,须打一百棒“杀威棍”。据说这是为了镇住那些暴徒凶犯的嚣张气焰。“杀威棍”是北宋司法系统的一项法定制度。
那么这项制度执行得怎么样呢?北宋末年徽宗年间,打虎英雄武松杀了西门庆,被发配到孟州牢城营,就面临着杀威棍的威胁。武松一到牢里,早有十数个一般的囚徒来看武松,说道:“好汉,你新到这里,如果有关照的书信或者使用的银两,赶紧拿在手上,一会差役就要来提你,你送给他。如果书信关系过硬或者银两多,可以免去‘杀威棍’,即便免不去,打的时候差役们也会轻些。如果没有人情书信、银子给他们,你就等着皮开肉绽吧。”可见,监牢中已经衍生出了一套逃避“杀威棍”的制度,可以用监牢外面的关系、用银子来免去一顿打。
可偏偏武松刚硬得很,最恨暗地里蝇营狗苟的事情,不屑于使用什么人情书信或者银子,偏偏要去见识一下“杀威棍”的厉害。监牢管营的问道:“新到囚徒武松,你来的路上可曾得了什么病?”武松回答:“我一路上什么病也没有,酒也吃得!肉也吃得!饭也吃得!路也走得!”管营自顾自说道:“这厮肯定是途中得病了,我看他面相不好,就不打他这顿‘杀威棍’了。”武松一时没明白过来,两边拿着木棍的差役低声提醒他:“你快说有病。这是大人关照你,你还不快承认。”武松恨的就是这些私底下的黑暗,闻言嚷了起来:“我没病,我没病!快打我‘杀威棍’,我不要什么照顾!”这一闹,满堂的差役都笑了起来,管营也笑道:“我说你得了病,你果然是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胡言乱语地发起疯来了。来啊,把他带下去,关在单身牢房里。”在这里,武松是法定制度的坚定拥护者,坚决要求“依法办事”,强烈要求打自己一百棍子。可执法者却坚决不依法办事,法定制度自然就成了一纸空文。
可见,法定制度并不牢靠。它看似是死的,但执行它的人是活的。执行者执行法定制度,这是他的法定权力。可法定权力早已经被各种衍生权力缠绕,并不决定现实;真正决定制度执行与否、执行好坏的是私底下的衍生权力。既然人是活的,衍生权力也是活的,制度也就“活”了起来。
“丁忧”是古代的一项人事制度。官员遇到直系长辈逝世,必须辞职回乡守孝,一般是三年。三年时间,对仕途来说很重要。某个官员可能正处于仕途上升期,突然什么职位都没了,要等三年才能复出当官;而三年后安排给复出官员的职位,一般都不如之前的职位重要。所以,丁忧是横亘在所有在任官员头上的一把利器。然而,清朝时期,满族京官丁忧只需回家百日,限满后即可回署当官。为什么呢?因为清朝官制分满汉,满族编制多,可用之人少,为了避免缺员过多,朝廷允许满族京官象征性丁忧一百天就复出。当然,朝廷的“理由”是满族京官的田宅、家族都在北京城里面,做官地就是故乡,可以“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工作。这个“例外”,打开了“丁忧制度”的缺口。清朝后期,汉族官员纷纷援引满族京官的例子,要求恩准“化悲痛为力量”,免于丁忧。如袁世凯就没有丁忧,母亲死后一直在当官,还不断升迁。有了先例之后,拒绝丁忧之风盛行。许多汉族官员接到家里的噩耗,只是请假一个月回家料理完丧事就回官署办公。“丁忧制度”的出发点是“孝道”,关系到“以孝治天下”的王朝主流意识形态。如此重要的制度都能够形同虚设,更不用说其他制度了。
“捐官”就是捐钱买官,这是清朝重要的财政收入,盛行一时,弊端多多。《辛丑条约》签订后,国家多难,朝廷下令施行新政。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趁机奏请废除“捐纳实官”。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光绪下圣旨,声明以后无论什么原因,都不准捐纳实官,从降旨之日起,就永远停止。并且要求一个月内各地、各系统将卖官的数据汇报到户部,不能延期。
我们就以“永停捐纳”为例子,看这个以圣旨形式确立的制度是如何被一点点击破,最后变为一张废纸的。
圣旨规定一个月内报数截止,那也就是说在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之前的买官卖官行为依然有效。于是,各地的捐纳机关开足了马力,展开最后的、疯狂的捐纳行为。地方督抚纷纷亲自出马,为最后期限内的买官者奏请官职。比如在截止日期之前,山西巡抚岑春煊称云南人解秉和捐银一万五千两给山西省,奏请任命解秉和为道台,分配到山西省,而且是“尽先补用”。为了表示自己没有违抗一个月前的圣旨,岑春煊解释说解秉和捐款日期是上谕颁发之前。浙江巡抚任道镕也奏请任命捐银一万三千两的两浙盐商为实官。他也解释说这些盐商是在上谕颁发前就捐了钱的,只是因为路途遥远,现在才解到杭州。对于这两封以时间差为由的卖官请求,朝廷都批准了。
上谕要求一个月内上交卖官数据。凡在上报数据内的捐纳情况,朝廷都承认,不在其内的自然就不算数了。可是,各省、各系统以各种理由迟迟不上交数据。八月底,闽浙总督许应骙上奏,福建新海防捐“已遵旨停止”,但具体数据请求延迟上报,理由是福建距京遥远,运输名册需要时间。湖广总督张之洞以清理数据为由,请求将上交时间拖延到第二年的二月。在此期间,各省其实还在暗中大肆卖官。
朝廷的户部是捐纳行为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各省捐纳所得的一定比例要解送户部。所以,户部也不愿停止捐纳。户部奏请延长审核数据的时间,因为各地上报捐册为了遵守期限而连夜赶造,造成了颇多错误,而且数据很多,核对也需要时间。这就变相地延长了捐纳的生命。同时,户部还在捐纳票据上做手脚。曾任吏部考功司主事的胡思敬透露:“七月,皇上下诏停捐实官。各地办事官吏倒填月日,收捐如故。”除倒填日期外,还有预支空白凭证、滥发凭证,等等。朝廷和地方通融作弊。
偷偷摸摸在日期和数据上做手脚,毕竟成不了规模。于是,相关利益者就思考着在制度上对上谕进行“修正”。八月,户部专门奏了一个“停止捐纳具体执行意见”。意见先重复了上谕的意思,义正词严地表示要一律停止捐纳实官。接着,它就提出几项“例外”:第一是不属于实官的衔封、贡监、翎枝等项捐纳,请求继续进行;第二,提出“初捐实官者”和“加捐实官者”,认为要加以区别,今后不允许百姓捐纳实官,但已经有官衔在身的人可以继续加捐;第三,朝廷曾经发行“股票”(其实就是卖官的债券),继续进行;第四,地方官绅如果“报效”巨款,可以由地方官员奏明朝廷,经皇上特旨恩准的可以“较寻常捐纳之员班次更为优异”。户部的意见打开了巨大的卖官口子:非实官可以继续买卖,已经有官衔的人可以继续捐官,而第三、四两条意见则完全保留了两种捐官形式。这个意见甚至连折中都算不上,只能说是限制了一般老百姓直接捐纳实官的道路,增加了捐纳的形式难度而已,本质依然。这个意见竟然获得了批准。
至此,禁止捐纳实官的圣旨被冲击得四分五裂了。一年后,户部又奏请对“报效”巨款数万的人特旨奖励,如果是正途出身奖给正印实官,如果本身就是正印实官立即升官。这就强化了第二和第四条具体执行意见。同年,各地督抚纷纷哭诉财政危机,要求恢复捐纳实官。朝廷考虑到圣旨墨迹未干,不好开禁,做了折中,把第二条意见中的“有官衔在身的人”扩大到“有功名在身的人”,极大地扩大了允许捐官的对象范围。于是,山东借口河工、广西借口剿匪、奉天借口筹边,纷纷奏准重开捐官。口子一开,捐官不可遏制。
五年后(光绪三十二年),“停止捐官”的呼声再次响起,户部再次奏请“停止实官捐输”,得到光绪批准。这只能是对愈演愈烈的捐纳大潮的暂时限制而已,口子依然留着。
捐纳实官主要表现为专折奏奖、皇帝特批。各省财政依然困难,科举正途又在1905年停止了,大量的人只能涌入捐纳异途,捐纳盛行。富贵人家穿着开裆裤的幼儿,就隶名官员名册,甚至还在肚子里的婴儿也成了朝廷命官,开始了宦海沉浮。
到了宣统二年(1910年),朝廷干脆奏请专折奏奖、皇帝特批的捐纳实官形式从“或准或驳”改为“一律特沛恩施”,完全将捐纳实官变为例行公事了。九年前光绪皇帝“永远停止”的话完全烟消云散了。
(摘自浙江大学出版社《泛权力:透视中国历史上的权力法则》 作者:张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