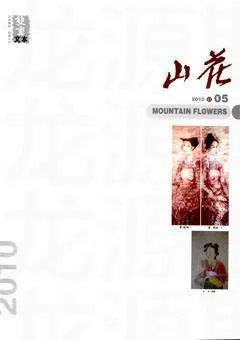论魏晋六朝散文的主体空幻意识
魏晋六朝散文有着特殊的贵族气息,绮丽花巧之外,是浓重的主体空幻意识。刘大杰认为:“魏晋时代,无论在学术的研究上,文艺的创作上,人生的伦理道德上,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解放与自由。”这种解放与自由是对生命现状的关怀,却不是超越生命局限以后真正的“任自然”。很大程度上,那只是寻求出路的尝试,及其过程中无法隐藏的困顿。陆机也感叹“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世阅人而为世,人冉冉而行暮”。士人们看到了世事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固性,这种变幻常常又集中体现于山河易主和个体生命的脆弱。
一、对王朝易变的观照
对文人最有打击性的当是王朝易变,故国凋零。文人常以忠君济世为生存的总价值,当朝堂突然易主,文人即刻面临价值抉择。如另择朝而仕,则忠心不再。不能适时入世,就只好隐于方外了。所以故国覆亡对传统文士的打击是致命的。然而,一切如梦幻泡影却又是万古不变的真理,佛经中说:“所说如幻,如梦,如响,如光,如影,如化,如水中泡,如镜中像,如热时炎,如水中月,常以此法用悟一切。”意思是,所谈到的一切都无一实在,此时还有,倾刻俱灭。又云:“世谛之法,皆如幻化。是故经云:‘从本以来,未始有也。’”魏晋六朝玄学佛学盛行,这种观点深植于文人的心灵,但并不一定每人都可参透。所以文人常常表现出悲情意识,世事一旦易变,心灵就显得摇摇欲坠了。
庾信作为国势变换的亲历者,其《哀江南赋》序云:“粤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盗移国,金陵瓦解。余乃窜身荒谷,公私涂炭。华阳奔命,有去无归。中兴道销,穷于甲戌。三日哭于都亭,三年囚于别馆。天道周星,物极不反。傅燮之但悲身世,无处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文中极用“哭”、“泣”、“涕”等字眼,将这种击碎理想的悲情传达而出。其实他也明白这是一种必然,但仍免不了发出悲叹,“呜呼!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凄怆伤心者矣。”这种悲叹是与生命的实质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是他主动地思索世事变迁的含义。
同是南北朝人,鲍照也亲眼目睹了世道之乱而以辞抒怀。南北朝是一个动荡多难的时期,各个朝代的存在时间都很短,动辄为他所代,所以黎民饱尝苦难。文人在经受这种苦难时,还涉及生存价值上的刺激,所以言之所至,难掩悲怆。据说东汉汉阳太守傅燮被敌围粮尽,其子劝其告老还乡。他说,生乱世,何处求生?那是生存理想被击毁的年代,无可奈何。世道既乱,人早已无暇关心自己这个个体,但社会的实际情况的确又刺激了个体感时伤事。对世事乱离,恐怕没人比鲍照更有切身体会了,其文日:“通池既已夷,峻隅又已颓。直视千里外,唯见起黄埃。凝思寂听,心伤已摧。”鲍照最后死于乱军,可以说自身即做了世事空幻的注脚,他曾在《登大雷岸与妹书》中描绘出了一个完美的隐居所在,“隐心者久矣”,终还是“空华泡影”。
国势变换必然伴随以战争,战争是对生命最残酷的践踏。某种程度上讲,文人的生命价值是依附在政权上的,生命理想的幻灭,必然刺激文士观照自身的存在。反思生命存在的价值。
二、对生命现状的关照
政权更迭过程中,大批文人不明所以就做了牺牲品。吴质《答魏太子笺》云:“何意数年之间,死丧略尽。臣独何德,以堪久长?”个体生命在此时显得尤为脆弱。尤其是以文才思想见称者,“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
这不是简单的物伤其类,生命脆弱的感受离谁都那么近。人生本就短短数十年,庄子说它如“白驹之过隙”,但若这数十年中又命途多舛,则又是悲叹造化。更有甚者只能空托留连难舍之心,在回忆里寻觅痕迹,而回忆则又更空幻虚无了,如向秀《思旧赋》,嵇康、吕安都是向秀的好友,二人“各以事见法”,二人是当世名士,这种结局就会引起更多人的深思。活生生的生命。几日前都还在一起饮酒作诗,转瞬间就有无妄之灾,生死离散,自己都在疑其真假了。而这种痛苦却是实实在在的,当听闻邻居吹笛时,不自觉地“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虽然佛教告诉人们,“是身如野马,渴爱疲劳。是身如芭蕉,中无有坚。是身如幻,转爱报应。是身如梦,其现恍惚,是身如影,行照而现的。是身如响,因缘变失。是身如雾,意无静相。是身如电,为分散法。譬如幻者。见幻事相。”所有人的生命现象都是虚幻的,故嵇康,吕中二人的生命形象不过是个虚构物而已,不但这种可见的形象是假的,连人的“真实感受”也是虚幻的:“五阴(色受想行识)如梦,如响,如光,如影,如幻,如炎,如化,终不可得。”然而,对个体生命形态的超越绝非必然以生命的终结为其代价,只不过,生命在向秀的眼中的确太脆弱了。
另外,生命的空幻感不仅仅因灾祸而生。当比之于茫茫太虚,个体的渺小就无法回避。被称为“天下第一情种”的王羲之在《兰亭集序》里表达的就是这种悲情。“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说王羲之是情种并非男女之情,而是一种关怀生命的悲情。吴楚材,吴调侯认为,《兰亭集序》“通篇着眼在‘死“生’二字。只为当时士大夫务清谈,鲜效实,一死生到齐彭殇,无经济大略,故触景兴怀,俯仰若有余痛。”王羲之是晋代文人的代表,从其自身的经历看,他对生命有着深刻地思考。兰亭集会,众名流贤士一如既往地谈玄论道,纵情山水。但王羲之突然被心底的悲情触动,转而伤怀。看看大家都还“不知老之将至”,而“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人很快就会接近死亡,本来极富生命活力的事物,转瞬间就变得老化。什么是永恒呢,找到生命的永恒价值是件大事,而他却还找不到。庄子是说过死和生,寿长和寿短都一样,可是自己分明体悟不到这一层次,所以怀疑它就是“虚诞”、“妄作”了。看得出王羲之心中对生命的最本源是存在困惑的,所以“此《序》廖廖数言,托意于仰观俯察宇宙万江,系之以感忆,而报于死生之痛。”
三、超越中的困境
时代所产生的生命难题,集中体现在个体生命追求超越时步入的困境。个体生命因其局限性而缺乏永恒价值,故而每一个个体都尝试着与生命本体链接。某种程度上讲,将生命理想寄托给君主或国家,就是个体生命对永恒价值的依附的尝试。这种依附抑或链接在各个时代的表现又不尽相同,如在更古老的春秋,孔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实是突破物利,与天命合一的。庄生也从道的视角来看:“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生死都统摄于道。于是,有限生命就有了永恒价值理想的支撑,个体就不至于困扰于现实状况。
六朝散文的精神本就是一股对现实的决裂力量,力图回归于生命的终极世界。嵇康《释私论》云:“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但是从嵇康醉心于丹药,且开罪于司马氏的事实来看,他并不能在心性上彻底超脱现实的局限,做到“越名任心”。实质上,不止嵇康,六朝的总体风气都是醉心于空苦,即使是市井平民也以哀怨为美。且早在汉末就有了这种风气。应劭《风俗通议》就记载了桓帝元嘉年间,京城妇女们以愁眉、啼妆为美的风气。而王羲之尤能代表魏晋士人,王谢二姓是晋朝显贵,可谓一时春风得意。但他的话中还是透露了人们追求超越过程中的心灵困境,“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生命的价值所在,以及如何超越生死,仍然是摆在六朝文人面前的首要问题。
自由,同时就是价值观多元,以及多元背后生命信念的非唯一性。寻找心灵的归止是时代的前沿追求,任何一个朝代都有人喑哑在这个主题里,晋代这类人尤多。他们常以人格的反叛,放浪形骸来感觉生命的存在,《世说新语》中多有记载。刘伶嗜酒,妻子哭着要他戒掉,他说必须准备酒肉祭神发誓才能戒,其妻果然备好。刘伶誓言是:“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醒。妇人之言,慎不可听。”然后酒肉入肠,不久醉去。阮籍也是个放诞阔达之士。他有个卖酒的邻居是绝色美女,每次阮籍醉酒后都随心倒在女老板旁边酣睡,但从没有什么过分的举动。另,王子猷出京,听见有人吹笛。吹笛人是桓子野,当时两人并不相识,王子猷让人去请桓子野来奏一曲。当时桓子野已经成名,他也听过王子猷的大名,就下车来到王子猷处,为他奏了三支曲,奏完后,起身离去。两人始终没有说过一句话。
魏晋风度,各人行为有雅有俗,但本质上都是在与现实中的礼法决裂,从而寻找另外的方向。这些行为往往特立独行,读后令人拍案叫绝。“然乐极则哀集,至盈必有亏,故曲终则叹发,宴罢则心悲也。”读者都清楚这些行为的背后是一种困境。任何一个时代都有找到出路者,但大多数是挣扎在途中的,这种挣扎的轨迹往往化为一篇篇绝美的文章在历史中引起很多人的共鸣。
综言之,魏晋的背景非常特殊,可以说是一个以贵族为主流的时代。文士经历了国事和心灵双重挫折,推动了自身思考寻求出路的进程。但即使时事乱离,士大夫风气体现之普遍却是前后俱无。氏族们仍在热衷解玩山色,随心任行。当这种“乐”接近尾声,“悲”适时而来。当时玄学和佛学的兴盛似乎并没有引导士人们走出困境,反而更愈衬托出个体生命的空幻,魏晋散文则浸透了这种空幻的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