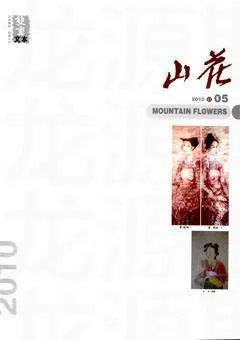爱默生对艾立森之影响研究
拉尔夫·华尔多·艾立森(Ralph Wald0 Ellison)和拉尔夫·华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分属美国文学史上两个不同世纪的文坛殿将。一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红大紫的黑人作家,一位是19世纪著名的哲学家和诗人,在美国文学史上极具影响力的巨人。以爱默生为殿将的超验主义思想是新大陆精神的滥觞,难怪老艾立森以他的名字来为儿子取名,以表达对儿子寄予的厚望。不管艾立森对爱默生这位文坛泰斗是否像其父辈那样顶礼膜拜,但是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标新立异,开创文学新传统。对宗教的怀疑以及明显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反理性倾向,都表现出爱默生的影响痕迹。
一、独领风骚、开刨文学新传统
爱默生是19世纪美国超验主义的鼻祖,浪漫主义高峰之殿将。作为美国文艺复兴的领袖和一代散文大师,爱默生的文艺思想及创作风格影响着从19世纪的麦尔维尔、惠特曼到20世纪的罗伯特·弗罗斯特、华莱士·史蒂文斯等几代美国作家。正是这些卓有成绩的作家的共同努力,才使得美国人的思想和文学创作日益走向独立和繁荣,从而开始形成具有鲜明特征的美国民族文学。爱默生主张破除传统习俗的限制,使美国人的思想得到极大解放。使文学创作在文体和主题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和建树。他说:“我们依赖旁人的日子,我们师从它国的长期学徒时代即将结束。”他呼吁美国作家不再局限在欧洲的传统当中,一味模仿旧大陆的陈腐,而是将目光转回到美国这个新兴而有生命力的大陆上,开始描写新大陆的人、新大陆的事及新大陆的思想。因为“模仿不能超过它的模特儿,模仿者注定是要做毫无希望的平庸之辈。模仿就是自杀”。
艾立森自幼生活在种族歧视比较缓和的环境,缺少赖特由自身经历而形成的对白人种族主义的仇恨,否定了暴力是黑人生活的重要事实这一观点,从而离开了理查德·赖特以黑人抗议为主题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他的作品中对黑人的社会处境、黑人运动以及黑人的前景等并没有作过多的深入描写和思考。艾立森的代表作《看不见的人》尽管写的是一个美国黑人的经历,这部作品还是被誉为“二战以来最优秀的美国小说”,是当代美国文学的一部扛鼎之作。究其原因,不难看出小说虽然主要写一个疲于奔命的黑人青年对“自我本质”的探寻,但是它所表达的人类性却如此鲜明,以致各种肤色的读者都能与之产生共鸣。正如故事结束时主人公所说的“谁能说我不是替你说话,尽管我用的调门比较低”,所以作品展现的是现代人探索生存、寻找自我的主题,从而唤起了广大美国人民对自身价值和命运的关注。这个主题在当代西方社会,特别是经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普遍感到在物质力量与社会异己力量的压迫下产生了一种失落感,急切想了解和探寻自我在这个社会中的角色和定位的氛围中,有着广泛的共鸣基础。因此,小说巧妙地触及了一个相当敏感的社会问题,主人公的经历和感触似乎已经超出了肤色的范围。也许正因为如此,这部小说才引起了更多人,特别是文学评论界的兴趣。小说没有刻意渲染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对立,而是开始探讨黑人与白人如何相互理解融为一体:不再仅仅控诉白人种族歧视的罪恶行径,而是进一步思考现代黑人要改变自己的处境本身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不再仅仅关注黑人的身份和处境问题,而是由此推展开去,思考整个人类在现代日益复杂的社会中的异化问题,从而开创黑人文学新传统。正如爱默生所强调的那样,“不打破习俗就不会成为一个有作为的人”,无论是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人,他必须不能随波逐流。任何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都凝聚着作家对主客观世界的审美新发现。《看不见的人》是美国黑人作家写美国黑人经历的作品,但其意义却远不限于此。艾立森在《影子与行动》的引言中说,作为作家,“我的任务是通过作品去揭示人类所共有的东西,但其意义却远不限于此。这种共性蕴藏在白人和黑人的创境中。通过它,我试图追求一种能够超越种族、宗教、阶级、肤色和地域障碍使人类得以进行交流的艺术方式。”这部小说塑造了一个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艺术形象,在展现主人公的成长过程时,艾立森向我们揭示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但最突出的主题却是现代人对自我的探索和发现。《看不见的人》的问世标志着黑人文学脱离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文风,迈入了现代文学的殿堂。
二、宗教怀疑论
爱默生出生于宗教世家,自小受家族环境的熏陶,对宗教有着盎然的兴趣,哈佛神学院毕业后任波士顿第二教堂牧师。爱默生很早就开始了对加尔文教的批判,担任牧师后,接受唯一理教的同时也发现了其中的古板仪式和僵化成分的消极作用,认为丧失了满足人们精神情感需要的能力,放弃了真正的宗教体验——直觉感觉和神秘,代之以理性、常识和规则。人脑被动地接受知识、印象。然后机械地加以组织、分类。人们的宗教事务因此成了诵经步道的活动,而不是直接与上帝通灵,感受上帝的存在1832年毅然辞去牧师职务,并将自己与唯一理教的分歧公诸于众,张贴在教堂门口,表现出无比的勇敢和坚定。他在《论自助》中说,如果完全生活在宗教里,那又怎么来处理传统中神圣事物呢?这些冲动来自现实社会,而不是来自虚无缥缈的天国。爱默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对宗教提出否定和质疑,这种“离经叛道”的勇气在当时实在令人汗颜。艾立森骨子里对宗教的叛逆让人们时隔多年后又目睹了爱默生当年的叛教风采。
艾立森饮誉世界文坛的名作《看不见的人》通过对黑人牧师霍默·A·巴尔比的塑造,表现出艾立森对黑人教堂持批评和能够的态度。巴比尔是一个来自芝加哥的访问教长。他被勾画成“一个奇丑无比的家伙。肥胖不堪,短短的脖子上安着一个子弹头似的脑袋,极不相衬的大鼻子上架着一副墨镜。”他的演讲热情有力,感人肺腑。然而,当得知把比尔牧师是一个瞎子时,叙述者被他的演讲所激起的所有积极力量和希望都被大打折扣。黑人教堂这样一个社会机构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在他的笔下竟只成了一个具有否定意义的象征——把比尔“胡言乱语”和不着边际的盲目。艾立森对黑人教堂的描绘采用了简单化的方法,倾向于否定的态度。这与社会学家萨拉·埃文斯和哈里·伯伊特对非裔黑人社区黑人教堂的历史和作用做了如下积极评价形成鲜明的对比。埃文斯说,纵观整个黑人历史,黑人教堂的远见卓识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始终处于被称为反抗文化的中心,这种反抗文化构成了针对占主导地位的白人文化所包含的价值观及耻辱的一种选择。而且,在这一反抗文化内部孕育了渴望民主的热情与向往,那就是不仅要生存,而且要实现更加广泛的社会领域内的全面变革。小说中艾立森只描写了黑人教堂的一方面,却根本没有提到那些献身事业的黑人教士们,他们在无比艰难的岁月里领导和指引了他们的教民。《看不见的人》中也找不到任何暗示来说明无论是过去还是在将来黑人教堂或许会对促进美国民主改革起积极的作用。
三、个人主义
以爱默生为首的超验主义者强调独立自主的自我,认为个人是社会中最重要的元素,社会的发展是通过个体的发展来实现的,因此,个体的自我完善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理想的个体应是自立的个体:人可以通过超越物质世界获取自我完善。他在《论自助》中表现出明显的个人主义,“赦免你自己,你将会得到世界的宽恕。先应该为自己而活……”,“在所有反对意见面前,一个人可能会认为世上万物除了他自己以外,好像都是虚妄和易逝的。”无独有偶,艾立森在他的代表作《看不见的人》中透露出明显的个人主义,他强烈拒绝一切社会和政治活动。诚如爱默生所说,社会中到处都是引诱社会中每个人抛弃自己勇气的陷阱,社会也是一个的合资公司,每个人为了获得更好的利益,总是牺牲自己的自由和文化……艾立森对各种社会组织和一切形式的集体活动抱有根深蒂固的怀疑,这些使他的创造力和思想模式陷入了一个永远未能逃脱的困境。同爱默生一样,在艾立森的笔下,社会始终是“一个各成员之间相互倾轧的阴谋。他的个人主义在《看不见的人》这部小说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凡是叙述者与之接触的人群、社会机构和政治活动,他一概予以否定的描述。在艾立森的笔下,社会集体活动未使叙述者获得自由,实现自我;相反,它却冲击他的自主,控制他的声音,把他推向世俗的浊流,阻止他发现自身的价值所在。艾立森始终怀疑组织和集体,认为参加社会和政治活动会与他的艺术追求格格不入。在《看不见的人》里,工会组织只不过是让人惧怕、躲之唯恐不及的一个社会结构,代表着威胁个人幸福的一种势力。艾立森的强烈反工会情感不仅与麦卡锡时代的主流情感一致,同时也与他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观有吻合。以自己的政治声誉,尤其是在黑人社会中的声誉为巨大代价,艾立森整个生涯选择了脱离社会积极主义和政治活动,为的是能够全身心投入到艺术创作。这选择的动机在于他对小说创作的深厚执着的热爱,而最根本的原因却是他盲视的思想模式,是这一思想模式阻止了他在《看不见的人》之后创作出另一部伟大作品。
四、反理性倾向
从哲学的视角,超验主义被界定为“对人自身存在的那种通过直觉而通晓真理的能力的认识”。因此,作为一种人生哲学,超验主义主张人在自然的启发下感悟超灵的指导,降低物质需求,注重自我提高和独立地寻求人生意义。超验主义思想强调直觉在认知中的重要性,把理性摆在了次要的位置,这种反理性的倾向同样在拉尔夫·艾立森的美学思想中可见一斑。
艾立森自幼生活在种族歧视比较缓和的环境,缺少赖特由自身经历而形成的对白人种族主义的仇恨,否定了暴力是黑人生活的重要事实这一观点,从而离开了赖特以黑人抗议为主题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19世纪60年代后期。艾立森遭到了包括一些白人评论家在内的社会活跃分子的非议,认为他回避了作为深受种族歧视的黑人的责任,背叛了黑人文学的传统。对此艾立森回击道:“我是一个人,不仅仅是理查德·赖特的继承人。反省我的经历可以有很多种方式,远比‘抗议’这两个字体现的意思复杂得多。”和其他黑人作家不同的是,艾立森一再强调自己的创作不受政治立场和民族情绪等的影响。早在1953年,他在回答《巴黎评论》的采访时说过:“假如一个黑人作家,或者任何其他作家,他想为自己所希望(的东西)而写作,那么就好比没有上战场就败下阵来一样”。因为他坚信“最优秀的艺术可以造就最出色的政治,但是出色的政治却难以造就优秀的艺术。”他的代表作《看不见的人》固然因为主题意义的普遍性而饮誉世界文坛,但是作家致力于超越种族事实,超脱政治的企图却不容忽视。这一方面表现出艾立森与以前黑人作家的与众不同,另一方面,他“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律令”其不是象牙塔中的乌托邦吗?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殿将马尔库塞在《审美之维》中所标榜的那样,“艺术不能为革命越俎代庖,它只有通过把政治内容在艺术中变成元政治的东西,也就是说,让政治受制于作为艺术内在本性的审美形势时,艺术才能表现出革命。”朗吉努斯在《论崇高》中强调作家的心智,重视内在灵魂的涵养提高。艾立森文学创作中的美学追求似乎迎合了朗吉努斯所谓的崇高。但是作为黑人作家,种族问题永远是不可回避的事实,而且种族总是跟政治纠缠不清,藕断丝连,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经典著作《政治无意识》表明任何文化文本都积淀着政治无意识,即文化文本(或文学文本)容纳的是个人的政治欲望:“一切文学,不管多虚弱,都必定渗透着我们称为的政治无意识,一切文学都可以解作对群体命运的象征性沉思。”毋庸讳言,艾立森这种回避种族和政治,希望借艺术弱化政治,艺术万能论的理想所折射出的非理性倾向便昭然若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