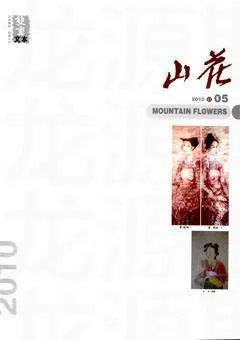论鲁迅散文\\小说中的报刊符号
目前学界对鲁迅与传媒关系的研究可谓方兴未艾,大致上分为如下几方面。第一,研究鲁迅的编辑思想。河南大学朱燕萍的新闻学硕士学位论文《论鲁迅的期刊编辑思想》考察鲁迅的办刊实践,对其办刊思想、编辑理念、编辑形式和风格、对编辑业的贡献等方面论述比较系统,但大致停留在编辑学层面,缺乏对鲁迅文化传播启蒙思想的深层挖掘。另外的论文也有此局限,如孙继国的《鲁迅的编辑精神》(《沈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傅安辉的《学习鲁迅当好编辑》(馈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李明山的《鲁迅的版权观念与实践》(《史学月刊))2002年第11期)等。第二,研究鲁迅的报刊编辑出版及其文学活动的关系。大多是资料的集合,如李霁野等编辑对鲁迅与报刊的回忆或评价,又如,罗淑芳《三十年代鲁迅的编辑和文学活动》(《咸阳师范专科学校学报综合双月刊》,1999年第2期),再如,黄轶《有关(河南)几个问题的辩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5期)等。第三,相对外在地研究鲁迅及其创作与传媒的关系。如李欧梵的《“批评空间”的开创》,探讨鲁迅《伪自由书》等发表在《申报·自由谈》的作品如何相对自由地谈论以及其与文网的斗争,但太注重所谓的“公共空间”以及不注重历史语境是此文的弱点;周海波的《文化传播视野中的鲁迅文学创作(上)(中)(下)》(《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一至三期)比较全面地论述了鲁迅的小说和杂文对报刊传媒的适应,他的文体、思想与文化传播的某些关系,又如,朱寿桐《鲁迅与(新青年)文学传统的创立》(《暨南学报>>2006年第2期)认为鲁迅对《新青年》的主要贡献在于积极主导建立《新青年》的文学传统,这从文学体式的建立、相当的文学成就及其标志性影响等可以看出。不过以上论文更多的是从外部着眼,没有提到鲁迅作品内部的传媒符号;郝亦民的《立于时代思想之巅的呐喊与战斗——关于鲁迅的传播学研究》(《鲁迅研究月刊》1997年第5期)注重的不只是传媒报刊,更多的是鲁迅的文化身份与其启蒙思想;吴小美等的《析鲁迅的传播角色及其传播环境》(《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也不注重报刊的具体研究,更多的着重其传播身份、手段以及文网的严密,等等。由上可知,上述从传媒角度看鲁迅的论文,无论是具体研究还是总体研究,都是较为外在的研究,它们回答的大多是鲁迅的传播活动、角色、环境、观念以及鲁迅对报刊的适应,而对鲁迅作品中传媒(报刊)符号的研究则至今还甚少人留意,没有发现以及回答鲁迅作品中究竟为什么出现那么多的报刊符号,它们与鲁迅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与鲁迅的文化传播思想有何联系,这些报刊符号的性质怎样,为何选择这些符号,选择它们表达了什么启蒙含蕴,如何表达。换言之,没有回答报刊(符号)如何内化为目的、意义、精神和形式,以及它们在内化的过程中如何被鲁迅化、文学化、启蒙化,而这个“内化”正是本文的研究空间,也正是本文的创新之处。
(一)
众所周知,鲁迅杂文中的报刊符号可以说在鲁迅整个作品系统中占绝大多数,涉及的报刊符号最丰富,最全面,也最深刻,最有力,总的来说,是动态化的,重批评,重议论,重抗争,是攻守的手足,是匕首和投枪,是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
但是比较而言,鲁迅其他文类的报刊符号特点则有所不同。
首先是散文。翻遍整本《野草》,只有最后一篇《一觉》牵涉报刊符号,鲁迅回忆起《浅草》、《沉钟》,并借这两种报刊符号慨叹社会的混沌与阴沉,也为青年的灵魂被磨砺得“粗暴”而欣悦,因为他从中看到生的力量、人间的力量。为何《野草》只有一篇涉及报刊符号?因为《野草》是鲁迅精神的独vyxb0CwNvxdHVY5J+E/x2w==语,是孤独者的生命体验与深层思考,虽然其中有一些现实影子游荡飘忽,但因为经过变形与艺术化处理,仍然适合“独语”的氛围与风格;而报刊联系着广阔的现实世界,意味着现实世界的直接或粗暴介入,必然影响独语之“独”,独语是“唯有排除了‘他人’的干扰,才能径直逼视自己灵魂的最深处”,所以《野草》极少报刊符号,不愿外在的现实直接入梦,即使是《一觉》中的报刊符号也是在独语氛围中怀旧与默想。相比之下,《朝花夕拾》作为精神的絮语,作为“从记忆中抄出来”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朝花夕拾·小引》)的心灵印象,其中出现报刊符号的文章比之《野草》要多出不少,于十篇之中竟有七篇,大概因为回忆与闲话的风格与现实世界互涉甚多,而且需要读者与之交流。只不过因为文章浸透了回忆的汁液,报刊符号往往流溢念旧的、平静的、苍凉的叹息,或者在这种叹息中讽刺也被减弱、冲淡了,而很少杂文中那种剑拔弩张、金刚怒目的呐喊。《朝花夕拾》的报刊符号用其小引的话可分为“纷扰”与“闲静”两种气氛,或者“纷扰”与“闲静”交织;或者从《儿童世界》刊物落笔,将中外儿童用书的“粗拙”与“精美”对比,流露重视儿童教育与悲悯儿童的情思(《二十四孝图》);或者以无常“并没有在报上发表过什么大文章”赞扬鬼世界的公正与可爱,顺带对正人君子之流的伪善刺了一下(《无常》);或者对抱着“医能医病,不能医命”观点的中医陈莲河“做中医什么学报”加以嘲讽,批评中医(庸医)害人与思想保守落后,内中应该也不无对父亲的死的感叹与悲痛(《父亲的病》)。以上大都是“为别人”的报刊符号,回忆中添加了讽刺。《朝花夕拾》还有几篇文章的报刊符号是“为自己”居多,几乎完全是一种生命的回忆:如《琐记》中有《时务报》、《译学汇编》、“报纸”等符号,意在回忆矿路学堂求学时看新书报的风气与青春气息,兼及新旧派之争;又如,《藤野先生》用“本校的杂志”“日本报纸”符号回想日本留学生活,痛感自己的被怀疑(作弊)与被轻蔑(弱国低能);而《范爱农》集中了多种报刊符号,如《朝日新闻》、“报馆”、“报纸”、“日报”等,旨在回味东京留学时学生看报情况,与范爱农合作办报等的交往情况,在闲静中有悲痛,在悲痛中是苍凉。总括起来,《朝花夕拾》的报刊符号是对旧日意味的深情回眸,是对生命的感叹与悲悯,是对死亡的沉思默想。其他没有结集的回忆性抒情性散文也有一些报刊符号,与《朝花夕拾》意味相近,只是有时燃烧着悲愤的怒火,这些散文有《纪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忆韦素园君》、《忆刘半农君》、《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我的第一个师父》、《死》等,此不赘述。总之,鲁迅散文中的报刊符号满浸着闲静、苍凉、孤独与悲悯,以回忆的笔调,与杂文的战斗反抗文字一起,共同描绘了鲁迅深邃丰富的心灵世界。
(二)
如果说在鲁迅散文中,提及的报刊是真实存在的,是回忆的点缀,那么在鲁迅小说《呐喊》、《彷徨》(因《故事新编》绝少涉及报刊符号,此略)中的报刊符号却大多是虚构的,是一种结构性因素,与人物的境遇、性格相关。
在这些小说中,《风波》颇为特别,它只字不提报刊的名称,但设置了与报刊相关的因素,是三个关键词:“时事”、“消息”和“新闻”。且看——
(1)从他(七斤)的祖父到他,三代不捏锄头柄了;他也照例的帮人撑着航船,每日一回,早晨从鲁镇进城,傍晚又回到鲁镇,因此很知道些时事:例如,什么地方,雷公劈死了螟公精;什么地方,闺女生了一个夜叉之类。他在村人里面,的确已经是一名出场人物了。
(2)七斤嫂这时从直觉上觉得事情似乎有些不妙了。因为咸亨酒店是消息灵通的所在。
(3)七斤既然犯了皇法,想起他往常对人谈论城中新闻的时候,就不该含着长烟管显出那般骄傲模样,所以对于七斤的犯法,也觉得有些畅快。
(4)此后七斤显然是照例日日进城,但家景总有些黯淡。村人大抵回避着,不再来听他从城内得来的新闻。
从例(1)可知,城市是乡镇人企盼、羡慕和捉摸不透的对象,城市俯视乡镇,代表着新鲜性、正确性与权威性,在统治权之外更有着话语权,所以七斤从城里带回的“时事”虽然荒唐无稽,但不影响他成为村中的“出场人物”。但也正因如此,城中消息可以成为他出名的诱因,也可以成为他恐惧的根源,如例(2)。而例(3)、例(4)呈现着一种以城压城的模式,即以城市新闻的话语权压制七斤的城市经历(身份),归根到底是对政权和话语权的双重危机感或恐惧感,即使它们还是一种新闻与想象,但造成的心理压力比亲历时更大,所以七斤家觉得“忧愁”与“危急”,而村人大抵“回避”;当然另一方面也透露了村人的冷漠与幸灾乐祸。总之,“时事”、“消息”和“新闻”这三个关键词有连接情节、塑造文化的作用,也有透视心理的作用。
《幸福的家庭》和《伤逝》通过报刊符号传达的都是一种深深的无奈与困惑。前者是穷困的“他”写作时把投稿的地方定为“幸福月报社”,一方面是生活的压力,另一方面是纸上的理想与安慰,再一方面是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反差,是无奈中的自欺欺人与自暴自弃。后者则多次以为《自由之友》译、作之事,折射出“不自由”的束缚与悲苦。以及“无友”的孤独无告,正好与《自由之友》形成鲜明对比。显现出主人公的生存困境与爱情困境,暗示着人的被抛状态,被社会、单位、家庭、爱人抛弃,被抛向一种绝望与虚无之境。与之相比,其他几篇跃然纸上的是一个“假”字。《肥皂》是把所谓《孝女行》连夜送到报馆去,化欲望为正经,化卑劣为庄严,所谓国粹之文、“移风”之文却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道貌岸然。《高老夫子》亦似于此,以高尔础在《大中日报》上发表的《论中华国民皆有整理国史之义务》以及仰慕高尔基而改名生发。讽刺其虚假嘴脸,自命不凡却无甚才华,欺世盗名,张冠李戴,所谓严肃实为守旧与下流(看看女学生而矣)。《孤独者》却以《学理周报》、《学理七日报》和《学理周刊》反讽了报刊文人的“无学理”,不过是见风驶舵罢了,足见人情冷漠,世态炎凉,呈现了现实的“冷”、知识的“冷”与人心的“冷”。《弟兄》借用报上关于时政的消息,播下了小说突变的种子,也发掘了兄弟情之下潜隐的自私虚伪,但这种表里不一来自生活的压力与对家庭的关爱,却也体现了沛君人性的复杂。
这就是鲁迅散文与小说中的报刊符号,它们有与鲁迅杂文中报刊符号相同之处,即讽刺,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杂文笔法对其他文类的介入:但也有不同之处,即散文中的独语、沉思、回忆,情感的苍凉、孤独与闲静,小说中符号的虚构性、结构性因素与性格心理透视作用。它们与杂文一起,共同构筑鲁迅的精神世界,表达鲁迅“灵魂的深”;与此同时,也共同构建鲁迅的报刊符号世界,突出鲁迅写作的报刊文化背景与社会背景的广阔性、丰富性与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