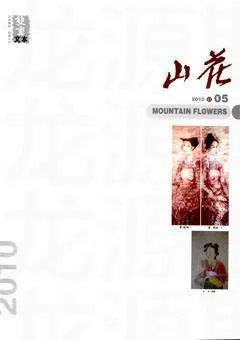麦子的流年(二章)
出生地
我在认识文字之后,就开始琢磨这个问题,如果我换一个地点出生是个什么景况呢?当沉重的包谷或者麦子压在我稚嫩的肩膀上的时候,我会在灼热的阳光下想,如果我出生在一个富裕的人家,那我一定是会在树荫下吃西瓜,还要冰镇过的那种。其实,我在没有进城之前,都不知道西瓜是什么样。但,我同时也会想,如果我出生在动荡不安的中东,那我背的可能不是粮食,可能是一件企图挡住尖锐弹片的行李了。于是,我觉得我幸福,又蹬蹬蹬努力在山路上前行,如果能在累得快倒下的时候恰好遇到一块可以歇脚的大石头,就欢喜得不得了。
周末放假,大家都要饿着肚子爬几座山才能回家。山间有一条宽阔的大路,虽然它拐过一个弯就看不见了,但是我们都知道,路的那一头就是城市。我就想,如果我父亲能把房子修到城市里那多好呢,那我肯定就不会这么辛苦地跑几十里路上学了。别说把房子修进城里,就是城郊也行;别说是城郊,能够再接近城市一点的地方也好。我出生在离县城很远的一个小山村,如果在村口小河沟里撒泡尿,它至少要流经三个县都还能闻到臊味。于是,我经常幻想着,如果我爷爷能够把房子修得靠近城市一点,我父亲再修得靠近一点,那多好啊。
对于城市,我在十五岁之前的认识是模糊的。我在十五岁之前没有到过县城,就连村子二三十公里外的小镇也很少去。城市的印象全来自村民们的闲谈和偶尔一场的露天电影。再后来,黑白电视机进村后,城市就变得生动起来,但是没有色彩。直到彩电和录像机也进村后,城市对我的诱惑更加强烈了。如果要说有什么梦想,那首先就是进入城市,进入更大一点的城市,城市有实现梦想的一切机遇。虽然多年之后,我才发现这原本是个错误,但当时是城市以及城市里的一切美好在引诱着我。
其实,我爷爷完全有机会把房子修得靠近城市一点。因为我爷爷是个正儿八经的国家人,准确地说,是民国时期的小学教员。我在我家正房的木楼上翻出来过,一张蜡黄的破了边边角角的草纸上,有个大红印章,是一个叫何本初的县太爷委派我爷爷到一个叫柘坝的地方任教的公函。后来,我才知道,柘坝是我时常撒尿方向的另一个县的一个小镇。就在我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我对何本初这个人产生了兴趣,于是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查到了一段话:何本初(1900-1956)陆军中将。四川永川人。1928年任四川省蒲江县县长。后历任彭山县、邛崃县、岳池县、仁寿县、夹江县、叙永县县长,1945年任四川省第14区(剑阁)行政督察专员兼少将保安司令,1947年春,任四川省第16区(茂县)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1950年3月3日在四川茂县率部起义,旋在赴成都途中叛逃,任川康边区反共救国军中将副总指挥,1953年5月。在西康阿坝被俘。1956年在成都于关押中病逝。然后,我又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我爷爷的名字,却都名是人非。唉,除了我,还有多少人记得他呢?我家保存着一份花名册,是当年剑阁师范的,毛笔工整地写着我爷爷的名字和其他我不认识但非常感兴趣的人的名字和他们的出生地。我也因此知道了鹤龄、金仙、公兴等这些陌生的地名。
我想,如果我爷爷不那么早地回到村上,如果我爷爷不遇上六十年代的大饥荒,他肯定至少会把房子修在我们周边哪个离城市更近一点的地方。虽然我老家的房子曾经是一个四合大院,有高高的华丽门楼,有粗壮的油漆柱头,有雕花的石质磉礅,但由于它离城市太远,我一直不曾留恋。我知道,我爷爷能在乡下修好那么气派的房屋,他肯定也能在城市修几间小房。可是,他并没有这么做,他是不是没有我这么有远见卓识昵?我不能埋怨谁。那场大饥荒,从此改变了一切,让我们这个家庭的发展轨迹停顿了下来。我想到这里,觉得命运极其偶然,一场饥荒,就轻易地改写了人生。虽然有人说那场饥荒其实可以避免,如果我要兴师问罪,我该去找谁呢?我知道,在巨大的洪流中,一滴水的命运只有随波逐流。
现在不少乡下的教师都在城里买下了房产,我相信,我的这个要求对我爷爷来说并不算高。然而爷爷过早地把生命终止在了六十年代的某个凄苦夜晚,让我的一切幻想停留在我家门前不远的山坡下。我每次经过那边,都要望一望树丛中那个长满了青草的小小土堆。爷爷去世的时候,我父亲十三岁,我二爸七岁,很快改嫁的奶奶又让我的梦想再度受挫。孤苦伶仃的父亲自身难保,当然没有办法去实现我的梦想。
由于爷爷占据了那一小块土地,于是那个村子便成了我的出生地,也就是我现在的故乡。我想,这又是多么偶然。如果我爷爷不在我们那个村子结婚生活,那我父亲的出生地和我的出生地又不知会在什么地方,或许只能说祖籍是在那个叫彭家的村子,就像我们现在说的我们的祖籍在湖北麻城孝感乡一样,到那时,彭家对我将会是与麻城一样的遥远。
从彭家到我现在居住的小县城,不足八十公里,我却整整跋涉了二十年。如果我爷爷当年就着手行动,如果没有世道的变故,如果没有命运的突变,他完全能够像我一样,把出生地变成自己的故乡。虽然我父亲自力更生,苦心经营,却不能超过常规地把自己生活的圈子与城市靠近一点点,但是在我能昕懂话的时候,他就时常告诫我们几姊妹:要投奔大城市。我的姐妹通过婚姻早早地变更了户籍所在地,而我却没有那么容易,我前后足足花了二十年。父亲朴素的愿望与我当年的幻想一样,如果要说得直白一点,我只能这么说,那就是追求幸福和自由,这当然也是人类共同的理想。
二十年后,我进入了一个小县城,在水泥制品间来来回回为生计忙碌,我怀抱梦想,比如,一次美丽的相遇,一个成功的抵达,一回欲望的满足……可是,现实比水泥还坚硬。我不得不说服自己,放弃一个又一个理想,在知足中让自己快乐。除了出生地,还有学历、背景、性格、经历、人际关系等重重阻碍,不得不让我几近麻木地生存下来。我从农村追寻梦想到了城市,才发现自己走进了一个更大的黑洞。
虽然,我现在能如此舒服地坐在电脑前,想想我的出生地和我的故乡,这其实是难得的片刻超然时光。我觉得,我们这三代人,就像三张布,哪里破了,就补上去一块,缝在一件叫家族的衣裳上。只不过有的布大、有的布小、有的布精美,有的布粗糙。男孩子,就补在自己家族的衣裳上,如果是女子,就换件衣裳。这些衣裳就这样花花绿绿、新新旧旧,在时光中流转,在人世和阴间轮回。
我不知道我爷爷是个什么样子,我不敢问我的父亲。我悄悄问过村里别的老人,他们说我爷爷高高大大,面宽脸白,笑声可以传出好远。我只有时常张望那个叫登家窝的小山坡,聆听茂密的草木间传出的风声和不远处山沟里哗哗的水声,想象爷爷的样子。至于我爷爷的爷爷、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对我来说他们只是三个汉字,在屋后的石碑上还能找到。如果再往上数几辈,我知道的只是湖北麻城孝感乡了。我想,自湖广入川后,我的上几辈人一边守望自己的老家,一边生息在这块土地上,自始至终,他们的人生在精神上也是完整的。
小时候,我参加过家族的一些喜事与丧事,翻过几座山,从中午走到天黑,在热闹或悲泣中,听长辈们讲述家族的故事。多数是我们家族的女儿嫁到另一个家族,或者另一个家族的女儿嫁进了我们家族,于是许多我不认识的人转弯抹角成了亲戚。面对一个个陌生的面孔,我知道我们血管里有一部分血液是相同的。但如果不是这些红自喜事,我们则是陌生的路人;在这些红白喜事过后,我们基本上也还是路人。对于一个必然远嫁的女儿,故乡,或者老家,都是独有的,但也是暂时的。所以,当我听说“一辈亲,二辈表,三辈四辈认不到”的俗语时,感到非常无奈和悲伤。
我出生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就是我的故乡,那里有我的祖坟,那里有我的祖业。所以,湖北麻城对于我只是一个传说。然而,我的女儿出生在这个小县城,我的故乡她至今都没有回去过一次,她以后还会把我的故乡认作她自己的故乡吗?我不知道。但可以肯定,再过几辈人,彭家也会与湖北麻城孝感乡一样,成为我们这个家族一个遥远的传说。
不容置疑,对于故乡这个概念,自从我离开家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们这一代将会有一个精神的断层。我的出生地与我的栖息地把我的精神世界分成了两块,无论在哪里,出生地那一块总是厚实地铺在最底下。然而对于我的女儿来说,她将必然在我的引导下,在这两个层面间奔跑,不管是记忆或者是遗忘,对她来说,肯定都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她也将有她自己的精神空间,在两个不同的精神空间交错,必然有冲突和妥协。
许多人将在自己出生地与栖息地之间辗转往返,思考,汇入芸芸众生,一直向前,让出生地的传说一个章节一个章节往下传,或者一个片段一个片段地遗失,消融到这个星球的每一个角落。
纵然,站在另一个星球上看我们的出生地,还没有一粒尘埃那么大:站在历史的长河边,讲述我们的出生地,完全无足挂齿,可是,我们却永远属于它。
我的出生地,也就是我的故乡,叫彭家,就是一粒尘埃那么大的一个地方,就是除了我,别人都毫不在意的一个地方,就是我千辛万苦最终逃离却永远也走不出的地方。
麦子的流年
乡下五月,雪亮的镰刀把山上山下的麦田麦地逐一清理,将那些头头脑脑带走之后,身首异处的麦子便东倒西歪的留在荒郊野岭,等待着最终的了断。
夜幕一层一层地盖下来,光秃秃的麦地便在越发浓厚的灰暗中迎接最后的涅槃。烈日暴晒下的麦茬脆弱难当,于是便成了火的猎物。那些麦茬再也不必盖房搭棚了,再也不必烧火煮饭了,再也不必沤粪当肥了。于是,麦田便成了麦茬天然的祭坛。
村里的青壮年全外出打工去了,剩下的全是老弱病残,如同这些缺肢少腿的麦茬。年迈的老人和年幼的孩子们再也无力把麦子像早年一样从根部割断,然后成捆地背回院坝晒打。他们只有孤单地拿着带齿的割镰,一大早带上幼小的孙子慢慢上路,经过一个山湾再经过一个山湾,到地里割下那些有芒或者无芒的麦穗,然后慢慢背回,或者直接在麦地边铺张塑胶布,把割下的麦穗摊在上面晒一天,傍晚的时候再用连枷打下那些干瘪或饱满的麦粒,然后背上半背连着麦壳的麦粒回家。
当年割麦打麦这类需要多人合作的重大农事,竟然就这样简化成单枪匹马的独角戏。
早年,乡下人丁兴旺,麦收时节,家家户户都要排好轮次请乡邻或者亲戚过来帮着收麦。早餐过后,七八个男男女女就背上背枷,拿上镰刀走向几里外的麦地,一路说说笑笑,欢欢喜喜。到了麦地,三五个女人在麦地边一字排开,俯下身子伸手挽过一把麦子,然后在根部狠狠一刀,哧哧声中,麦子齐刷刷地倒在女人们的臂弯里,仿佛静静地睡去。女人们把割下的麦子放在一边,身后的男人便过来用水泡过的稻谷草将这些倒地的麦子捆扎成把,丢在空地里。其余的男人们则坐在地边的石头上抽烟喝茶,讲些有关男人女人的段子给大家提神。女人们埋头默默地割着麦子,偶尔笑出几声,算是对男人们的回应,于是男人们讲得更起劲了,女人们也忘记了疲劳,地里的麦捆转眼也多了起来。看看地里的麦把差不多了,闲谈的男人们便把烟袋烟锅头朝下在鞋底敲几下,抖干净里面的烟末,装进布袋,走下晒得发烫的石头,把麦把紧紧地捆在背枷上,然后几个人帮着把沉重的背枷一抬,那些男人们便背着麦捆子往村里走。一捆麦子不下两百斤,男人们肩上还得搭张毛帕,屁股后还得拖根杵子,毛帕随时擦汗,有时也垫一下背,如果在路边找不到歇息的石头,便支着杵子换口长气。村里狗多,当男人们背上麦子在农家院落间经过的时候,那些大大小小的狗们都要跑过来追着咬,拖着杵子,狗也才不敢上前。
一天突击,几亩麦子便全收到了家,再不担心暴风或者暴雨的突然袭击了,农民们这才能够睡个安稳觉。
但是,也有意想不到的时候。有的人家因为亲戚朋友没有工夫,只好拖几天再收割,然而,突然会在某个半夜听到呼呼的风声。主人家再也睡不着了,不能躺在床上眼看着一季的收成转眼化为乌有。于是,男人便一骨碌翻身下床,叫醒老婆儿女,或者兄弟姐妹,一起连夜去抢收麦子。这样的事我也遇上过好几回,迷迷糊糊中被叫起来,背上背兜摸黑上路,凉风一吹,打几个冷战,头脑一下就清醒了。一路来到麦地边,发现周围麦地里全是人,都在趁黑抢收。大人们摸黑抢割麦子,怕小孩子不小心割伤指头,便让他们捆麦把子。风一吹来,尖锐的麦芒在脸上扫来扫去,又痛又痒。四周是黑洞洞的山和鬼魅一样的草木,不远处还有大大小小的坟茔,风吹草动,虫鸣鸟惊,都要让孩子们背心冒汗。大人们便故意与隔地的大人们讲话,东一句西一句,还不住地叫骂这鬼天气,给孩子们壮胆,再也没有闲心抽袋烟了。风小了,天也亮了,地里的麦子差不多全席地而卧,男人们这才放心坐在地边歇一会,抽上烟,摆摆龙门阵,小孩子也顺便溜到地边寻找野果子吃。如果不抢在风雨之前把成熟的麦子收割回去,一场大风,麦子就会在地里乱成一团,麦粒也会散落一地,根本无法收拾。如果遇上连续几天雨水,那些麦粒就会在麦穗上长出嫩黄的芽,虽然又是一个个小命,但是会变成农民们最伤心的泪。
麦子收回了家,这只算麦收完成了第一步。要让麦子装进仓,还有许多事要做。麦子收回后,农民们看准一个个晴天,把成捆的麦子一一解散开来,让太阳晒上几天,直到抓过一把麦穗一搓一吹,亮晶晶的麦粒出现在手把心时,打麦子的时辰才算到了。早些年,村民们都用连枷打麦子。把麦子铺在没有缝隙的石板院坝里,然后举起连枷轮番拍打这些麦把子,打完一面,翻过来再打另一面,直到把所有麦粒都打下了,才用木叉将麦草挑到一边,把麦粒撮到别处暴晒。打麦子要选太阳最毒辣的正午,这时麦子才脆,打起来才轻松。有时麦把子捂得久了,长了霉,连枷一打下去,刺鼻的霉灰呛得人直憋气。这样的手工劳作沿袭了上千年,后来村里用上了机器,脱粒机把连枷淘汰出局,过去一次打麦要几天的工夫,现在转眼便缩短到半个多小时。
脱粒机进村后,改写了村子的历史,也改变了不少村民的命运。沉重的脱粒机有一个漏斗形的进口和一个宽大的出口,在进口和出口之间,是一个用厚厚铁皮包裹着的铁转滚,转滚上几根厚实的铁片由粗实的螺丝固定着,看起来十分简单,居然能代替人打麦子,不可思议。柴油机的飞轮与脱粒机的转轴用宽宽的皮带连接着,机手用手柄将柴油机嘿哧嘿哧摇响之后,柴油机便带动脱粒机的铁滚飞速旋转起来。在脱粒机的出口处可以看到那个铁滚上的铁片一个接一个飞速闪过,看得眼睛直冒金星。在巨大的声响中,村民们便开始紧张地流水作业。几个人把成堆的麦把往机器跟前运送,两个人用镰刀把放齐在进料口的桌子上的麦把割散,推给漏斗前的送料手。送料是个技术活,要掌握火候。送多了,机器拉不动,要熄火。送少了,机器空转,费时费油费钱,所以送料十分择人。机器一响,声响震耳,灰尘四起,人们都戴着口罩,无法说话,全靠打手势,大伙都心领神会,忙碌而有序地服务于这台机器。幸好时间不长,最多半个小时,上千斤麦子就打完了,村民们个个都灰头土脸,鼻孔嘴巴里全是黑灰。大家都顾不上洗漱,马上抬机器到下一家继续打麦。
比起早先啪啪啪懒洋洋的连枷声,机器的声音则过于急骤了,这种折磨比用连枷打麦更甚。然而,还有更让人意外的事。
送料手要选那些精明的青壮年,他们眼疾手快,反应灵活。可是,出事偏偏就在他们身上。我们村就有一个十分精干的人,正因为他活跃能干,村里请他帮忙打麦,他都当送料手。脱粒机一转,漏斗口就把麦把往里面吸,送料手就负责把麦把理匀,或前推后拖,让麦把连续不断地卷到铁滚上,然后把麦粒脱下。接连几年,村里都平安无事。然而,有一年,这个青年在送料的时候,天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居然把手伸进去多了几分,飞速的铁片把他的右手掌碰上了。他惨叫一声,拼命缩手,转眼间,光秃秃的右手鲜血直喷;已经没有了手掌。机手迅速关掉机器,周围的人马上死死捏紧他的右臂,把他抱到一边,另几个则飞快地跑去寻找村里的赤脚医生。后来,父亲说,那几根从脱粒机出口出来的手指早已没有血色,落在石板上的几截白晃晃的,落在麦粒里的灰扑扑的,根本看不出来是手。我每次经过那些生意火爆的卤菜店,看到那些盐水泡鸡爪就恶心,仿佛就是那些被机器打掉的手指。后来回村的时候,我见到这个右袖空洞的长辈,总要假装没有注意他的右手,他也看似无意地悄悄藏匿着那截飘荡的衣袖。几年后,我回村看到他脸上露出了笑容,我心里才好受了一些。
从此,村民们对脱粒机有了不可名状的恐惧。闲谈时,还经常讲那个独手青年如何学着用左手吃饭穿衣,像婴儿一样开始使用小勺,都说他是在做二世人。来年打麦的时候,没有人敢用手直接送麦子了,而是找来一个小扫把,把麦子往进料口推。
后来村里通电了,电动机替换下了柴油机,电动机的呜呜声比柴油机的轰鸣小多了,听着也不烦,电费虽然高,但人们的动作再也不必那么紧张了,只是还得十分小心,毕竟脱粒机曾经差点要了人命。
很快,村里出现了小型的脱粒机,两个人就可以操作,至此,打麦才基本轻松下来。再也不用担心机器吃人了,也不再担心柴油机的飞轮突然脱落下来,飞旋着打断人们的肋骨或者房梁。
机器的更换,让农村的农事随之变化,人们的劳作也日益轻松,同时不少意想不到的故事也随之上演。然而,机器在农村也有被淘汰的时候。
当第一个被迫离家的青年从南方带回大把的钞票和外省漂亮婆娘的时候,村里的青年男女都惊诧了,于是一个接一个的青年男女都变成了打工仔打工妹,从偏僻的山村拥到了一个个从来没有听说过名字的地方:东莞、中山、深圳、西安、农八师、大同……过去在村里是耕田犁地的角色,出去摇身一变当上了车工、漆工、制衣工、制模工……不少还混上了组长、文员、公关……三五年后,村里的女子与外省的男子好上了,远嫁到那些陌生的省份,村里的男子也带回了说着村民们听不懂的方言的女子。一个个酒席过后,男男女女又背包打伞地走了,十年八年不回家。经常有儿女托人把村里的父母接到远远的城市,然后再带上一个小娃娃回来在村里抚养。村子不是家,成了旅店,寄放着乡情、父母和儿女。然而,南方或者北方也没有家,他们住着廉价的出租房,漂泊异乡。
在远远的地方,城市在一天天膨胀。乡下人用汗水洗清了城市下水道的污浊、乡下人用皮肤擦亮了城市的高楼,乡下人扛起一片片高楼和一座座桥梁,虽然他们的汗水越来越混浊,面容越来越苍老,但他们仍坚定不移地待在阴暗潮湿的出租房里,毫无归意。那些麦色的脸孔,在城市里被人民币、港币、美元染画得五花八门。城里分不清春分冬至,大满小满,乡下人进城便忘记了农时。
大春小春、麦田麦地在城里都毫无意义。进城的青年男女穿上了皮鞋、牛仔裤,习惯了工号、饭卡,再也不愿意光着脚板下田插秧,再也不愿意冒着小雨打牛耕地,虽然不能成为城市的户主,但也愿意长期被当做城市的暂住人口,毕竟城里看到梦想的机会比农村多,城市比农村更容易满足自己。那些廉价的晚会、免费的公园、花样百出的促销总能让他们得到不少实惠。这一辈子不过还剩二三十年,再暂住个十年八年,这辈子也算是城市人了啊。进城的乡下男女把麦子留给了村里的遗老遗少,至于如何收割麦子,不再是远在他乡的男女们操心的事了。
如何收割麦子成了夏天村里的头等大事。老人们只有自食其力,没有力气把整捆的麦子背回,那就只割下需要的部分。于是,割麦变换了方式,人们背着背兜一路割下成熟的麦穗,留下长长的麦茬。割一亩地的麦穗倒也难不倒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背一背’麦穗对于一个十多岁的留守少年也不是问题。麦收时节,再也没有过去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开进麦地的壮观场景了,再也没有过去说说笑笑的热闹气氛了。老人们想念着远方的儿女默默地割下一根根麦穗,孩子们想念着电话那边的父母默默地背起一背背麦穗,曾经热闹的乡村变得悄无声息,变得孤单寂寞,变得荒芜颓败。
大片大片的麦地如同遇上一只只沉默的蚂蚁,他们或早或晚,上山下山,把一粒粒麦子运回了村子,收进了柜子,等待着远方打工的儿女回来品尝新面。可是,往往是新麦放成了蛀麦,儿女都不曾回来一次。最先尝到新麦的,无疑是那些日益兴旺发达的老鼠。
早年,那些麦秸被齐整整地背回家,铺在房顶上,搭成的冬暖夏凉的草棚,或者生火煮饭、烧砖烧瓦,或者切成细末和进黄泥糊墙。实在没有用处,便堆在路边,让日晒雨淋,然后沤粪撒地。如今,情况大不相同,割完麦穗,麦秸没有了用处。如同这些老人,把儿女养大送走后,都没有人要了,被抛在山野,自给自足。老人们看清了自己对麦子的直接需求,不再枝枝节节,而是单单割下麦穗,然后烧掉麦茬。
麦收过后,闲着无事的老人便慢悠悠来到麦地边,长长地吸几口烟草,然后点燃麦茬。一片麦茬在烈火中舞蹈歌唱,噼噼啪啪,最后化作烟尘升上天空。在越来越浓的黑暗中,麦茬的火焰异常耀眼,远远近近的山上山下都看得见,这是麦子最豪华的葬礼。
那些远走的儿女,如同一粒粒外出的麦子,他们什么时候再回村庄?他们以什么方式重回生养他们的地方?老人们的女儿嫁到了外省,多少年来,没有见上一回亲家的面,更不用说两家人在一起吃一回饭,照一张全家福。女儿显然成了那粒不知落在何处的麦子,长成了野麦,难以找寻。儿子们呢?都在远远近近的城镇买下了房,或者待在遥远的城市,成天与不懂农事的外地女子一起拼命挣钱,虽然不易遇上婆媳战争,但也很难再孝敬双亲。还有呢?就是那些能飞檐走壁的青年们,一个个的走进了班房,走上了刑场,那些尸骨在远远的地方燃烧,是不是也像这些懒得回收的在野外点燃的麦茬?
麦子的流年,浸染着人世沧桑。麦地的烟火,映照着千万个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