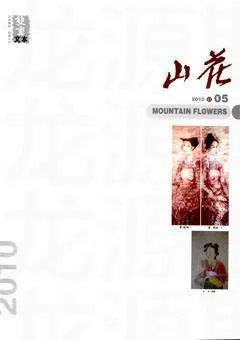宁静的田野
一前一后的两只麻雀,在油菜田的上空,弹上弹下地飞。
油菜成熟了。沉甸的绿色波涛淹没了田垅,铺满了田野,涌向蓝天低垂的远方。
顶多还晒一天,就要开镰了。接下来是打菜籽,榨菜油,整秧田,栽秧除草的又一个繁忙的轮回,这些关系一家老少吃喝的追赶季节的农事,一晌一刻也耽误不得。
农忙即将开始,农忙之前却是一片宁静。人们在做着大战前的准备,进行短暂的休整:人家院落里晃动着几个检查工具,平整院场的零散身影:寂静的田野,一片白晃晃的阳光里,响着油菜壳轻微的爆裂声。田野大战一触即发,可是这一天,突起的一声嘹亮的悲号,横空割倒了天地间的寂静。
刘老太太去世了。
去年的秋天,就说那老太太不行了。后面病倒的死了好几个,可她扛过了一个冬天,又活了一个春天。能够活到现在,没有人不说全是她几个姑娘的功劳。
老太太瘫倒在床,三个姑娘就这个照看十天半月,那个照看半月十天,人们路过老太太家的稻场,不是大姑娘把老太太背出来晒日头,就是小姑娘在给她梳头剪脚指甲,二姑娘也在给老太太换洗被子:而老太太的那个小孙子呢,也守在阶沿坎上做作业,要不就是用一根棍子挑着流在地上的一行冒着泡沫的洗衣水,独自玩得起劲儿。
三个姑娘的种种孝敬,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某个姑娘家的田里草快长满了堤,照料老太太也没有耽误一刻,某个姑娘半夜送老太太到镇医院去灌氧气,回来时摔伤了腿;某个姑娘胃口不好,照样给老太太洗屎衣尿裤,呕吐得几天吃不下饭——于是在人们皱眉咂嘴中,这几个姑娘倒成了大家怜悯的人。
先前还见老太太围着厚厚的被套,躺坐在院场晒太阳,后来就看不见她的身影了,只有几个姑娘进进出出地忙,小孙子趴在他婆婆常晒太阳的板凳上做作业。得知内情的人说,老太太躺在床上,已跟死人一样了。眼闭着,已听不见原先呼呼噜噜的出气声,如果不是胸部那一动一动的被子,谁都会认为那是一具只差入殓的尸体。有一次,来帮忙的一屋人已把棺材抬出来了,不料刚一转身,盖在她身上的那一床蓝印花布被单又在一上一下地动。她又回来了,硬是拽着一根稻草从某个深渊中爬上来了。于是她的姑娘们又要帮她翻身,洗澡,换洗脏衣裤,熬稀饭,喂水,再次遭受那些让人同情的磨难。
“这个老太太,不把人折腾够是不肯罢手的。”现场指挥的四贵,眼见白忙乎了一气,将茶杯一抖,半杯茶倒在院场上。他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这个老太太安然去世后,即将到来的是许多让人高兴的事情,喝酒,听丧鼓,都随着老太太的一口气喘过来,成了泡影了。她是成心不让人快活。九死一生躺在床上进气赶不到出气的老太太,在大家的眼里成了一个爱折磨人的老妖怪。
随着农忙的来临,几个姑娘换班的时间越来越短,十天,五天,三天。几天前,向来团结的三个姑娘第一次为排班的事闹了小小的不愉快。谁都不愿意在最忙的时候守在一个行将死亡的人身边。但是,她们毕竟都是人们称道的孝敬楷模,透过一层蒙着薄薄的塑料窗户,争吵声很快低了下去,接着是一阵听不清楚的嘀咕。过后,大家看见本地唯一的最高行政长官,村民小组长四贵,趿着鞋踱进了老太太的家门。显然,这个老太太为难的,不止是她的家人。她已牵扯到一村子的人。
就在这追赶农时的宝贵时间,在几个姑娘犯难的时候,知趣的老太太终于停止了呼吸。
那合唱似的撕心裂肺的声音告诉大家,爱开玩笑的老太太这回是千真万确地离去了,连一根可以拽在手中的稻草也没有了。听见了痛哭之声的人们并没有感到什么悲哀,悲哀是院墙外人家的事情。千万别误会淳朴善良的乡亲们没有同情心,该同情的是那几个已做出了种种牺牲的可怜的姑娘们。而这个老太太,她活着早已成了一种罪过,她的去世,是她本人和姑娘们的解脱。况且,几天来因为等待收割人们己感到了焦躁、感到了无聊,这宣告死亡的哭声,如同挂在树上的高音喇叭,在广播着县剧团要来演戏或者乡电影队要来放一场电影的喜讯,单调的生活突然别开生面,平淡的日子掀起了兴奋的波澜,人们索然冷漠的脸上生动起来,奔走相告这一桩已经广为人知的噩耗。
生活在民风淳厚的乡村里的人们仍循行着一条古训:红事非请不去,白事不请自到。前者关乎为人的尊严,后者却是做人的美德。何况实践这美德有许多不便向人道的好处:至少一日三顿有酒有肉。恰好又可作农忙大战前身体的补充,晚上说不定还有热闹的丧鼓,多日不见的女人端着盘子在桌席间穿梭,趁人不注意时可以摸上一把丰乳腴臀。酒足饭饱离去时,还可得毛巾香皂之类的打发。于是哭声就等于命令,不一会儿,那院场里就聚了无数的脸,胖的瘦的,圆的方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虽然衣冠不整像一群散兵,但个个脸上绷满义不容辞的责任,言谈举止全是仗义的气慨。
在同样衣冠不整,趿着拖鞋,却能指着人的鼻子大声说话的村民小组长四贵的指挥下,这些颇有侠胆义肠的人要不了一会儿就把一个灵堂布置得像模像样:堂屋正中停放着一口黑亮的棺材,棺材压在两条板凳上,像死亡之神乖乖地匍匐着四条低矮的腿任人摆布。棺材盖子用一根擀面杖支撑着,有经验的人知道是要等到出殡时才抽出擀面杖钉上爪钉。一进门的棺椁头前放着一张老太太的遗像,供着遗像的小桌上还点着一盏油灯,如同已死的生命做最后静静的燃烧。小桌下面是一个丧盆,里面烧的纸时时腾起片片黑色的灰烬,蝴蝶似的从门口飞出去,落到人的肩上、衣服上。丧盆的前面是一个空草包袋,那是供来吊丧叩头时的垫膝盖用的。老太太的三个姑娘一溜儿坐在棺材旁哭号。从她们伤心的哭诉中,人们知道今天是老太太八十寿辰,因此三个姑娘才聚到了一起。大姑娘准备吃了中饭回家去找人帮忙割油菜,二姑娘走时猪就没有喂饱,要回家去寻猪草的,不料她们还没有走,老太太却先走了。总之,老太太的去世的确出乎她们的意料。
丧礼有条不紊地进行,哭诉的丧家,忙碌的人们,每到一个吊唁的亲戚邻居,就会响起一阵杂乱震耳的爆竹声,一团呛人的乳白色硝烟就带着悲伤飘上瓦檐。当举着一个花圈,提着一把烧纸的远方亲戚跨进门来的时候,人们在接待中总感到丧礼有些不够圆满。还是那个趿着鞋的担当支客重任的四贵想到了,他一拍自己的额头:孝子!他望着众人责备道,看你们没有一个操心的!然后手一指,你,骑车子快去找!
在这个严格讲究丧葬礼仪的文明的乡村,没有孝子就等于演戏没有主角,这场多么隆重的丧礼也将成为天大的笑柄。
可是这个孝子太小了,小得让人们几乎将他遗忘。老太太没有儿子,只有三个姑娘。三个到了出嫁年龄的姑娘,留下了她认为靠得住的小姑娘。小姑娘坐堂招夫,老太太算招婿为子。上门来的女婿忠厚老实,对老太太也敬重孝顺,可是好景不长,在一次上山砍柴时,摔死山崖,好在给老太太留下了香火,一个孙子。这个小孙子还不到十岁,在外村的中心小学读书,只在节假日才回家,就是那个常爱趴在院场阶沿坎上做作业,做不了一会儿就跑去挑着地上的洗衣水泡沫玩耍的小子。人们只记得通知四方的亲戚,却忘记了那个很重要的角色。要知道,本地的习俗,孝子如果不是儿子,就只能由孙子来充当,再孝敬的姑娘也只能是一个配角。派去找的人急匆匆夹着摩托车骑到学校,学校已空无一人。喊了几声,才出来一个守校的老头,说学校中午就放了农忙假了。
主持丧礼的支客先生心急如焚,操着心的来客也时时出门探望,但那一条枯岗望到暮色苍茫也不见孝子的身影。四贵趿着鞋从大门圈到后门,一边走嘴里一边咕哝,脸上满是抱怨那孝子不懂事的神情:这个孩子,这个孩子——
迟到的孝子临近黄昏才进家门。人们期盼这个进门来的孝子也有一场撕心裂肺的哭号,这个丧事才算进入正常的轨道,但是他的表现却大让很失望。进门来的孝子,瘦黑的身上一件发着汗馊味的短衫,一条沾着泥巴的两个裤腿卷得一长一短,裤子衣袋像扭着两个树疙瘩,里面鼓囊囊的不知装塞着什么名堂;一个染着墨水的肮脏书包提在手上,一条斜到肩上的红领巾,像挂在颈口的一只角。他像站在老师面前做了错事似的低垂着头,一声不吭,因此人们也看不清他汗迹斑斑的脸上是不是大家期待的痛苦的模样。他一进门,就被人扯着在他被称为婆婆的遗像前叩了三个头,站起来后,就有人告诉他做孝子的职责:守在灵堂里哪儿都不能去,见有人进门就要向人下跪,别人对着灵枢行跪拜之礼时,也要陪着跪在棺材前面的草包垫上,等别人把一套礼仪行完,伸出手来拉时,才能站起来等等一系列繁琐的礼节。来的是女的,自然要在棺材旁哭几声才像话,是男的,就可退到一旁喝茶抽烟,而他这个孝子却要退到灵堂的角落,等着下一个吊唁人的腿跨进门来。老太太的几个姑娘见了女客就做千篇一律的啼哭,而这个小孝子整个过程都低着头像个木偶,不久人们便失去了对他关注的兴趣。这是一个还不懂事的孝子,倒不如去探听让人提神的消息:张开手指去量一量横躺在案板上的一头肥白的猪肉,打一打赌,几斤几两,看谁说得准;看厨房帮忙的人拖出放在桌子下的大塑料壶,把里面的酒装进小瓶里去,嗅着洒在地上的酒香,猜是在哪一个代销店打的,莫不是水货;主人准备了一些什么打发,争论着办丧事以来,哪次得到的毛巾质量好,用了多长时间还在用;还有几个干脆支起了桌子,玩起了牌,出牌的幅度和响动都很大,让人一看就知是心情舒畅的那份感觉。正玩得高兴,趿着拖鞋的四贵推开了门,喝斥道:还在这里玩!请的喇叭就要到了,到大门外去搭棚!
村民小组长官不大,却管一方人的生老病死,而这来帮忙的一天两天,能不能既送了人情又抵了村里义务工,全凭他一句话。于是大家忙丢了手中的牌,有的找雨布,有的牵电线,有的搬桌椅,虽然大家挨了几句训,脸上还是喜眯眯的笑容,不光是因为今晚的热闹可以调剂长时间生活的无聊,还有早已得知这老太太只停放一晚,明儿一早就要上山,并不耽误自家田里收割的大事。如果还迟一两天,在这儿帮忙恐怕心情就没有这么好了,心事就会在田里的油菜上了。明儿的葬期也好;老太太的几个姑娘异口同声要求明儿就下葬,灵柩并不会在屋里一天二天地停放。像掐准了时候似的,老太太真是一个体谅人的好人啊,难怪她有这么孝敬的姑娘——老太太的去世又重新换取了人们对她的好评,她又成了人们心目中最值得尊敬,最值得享用福气的人。几个在大门口栽桩牵线搭棚的人,悄悄吹起了口哨。
棚还没有搭好,一张标志着位置的写有“云台师坐”的白纸刚贴到墙上,那一套喇叭班子就来了。像是从暮色中走了出来,看不清他们的面相,只能辨别身体的高矮,以及手里提着的长短不一的唢呐、长号和几面沉甸甸的锣鼓。一阵迎接的鞭炮声后,他们手中的乐器就一起发作起来。长长短短的喇叭和唢呐先是朝下吹,再慢慢地昂起来,吹向天去,低沉呜咽,仿佛是向天告知又一个灵魂的上天。但是这种悲伤的气氛也只是一瞬,当他们接受了孝子的跪拜,坐在专设于大门口的“云台师坐”大棚里的时候,就和结婚生子时的差事没有什么两样了。没有人来时就在灯光下打牌,听见迎接吊唁人的鞭炮响起来,忙覆了牌,抓起吊在椅背上的喇叭锣鼓和乐似地一阵敲打。吹打的曲子都是大家熟悉的,什么“心太软”,什么“难忘今宵”,全与丧礼不搭边儿,自然也从中听不出丝毫的悲伤,如果不是竖在门旁的花圈,屋里人的几声啼哭,过路的人还以这家有了什么喜事。呛人的炮竹硝烟还没有散尽,喇叭响了一阵就停了下来,他们把手里的响器挂在椅背上,拿起覆在桌上的牌,问一声该谁出了,接着啪的一声一张牌丢出来,桌上的游戏又开始了:有孩子跑过去,冷不丁地敲一下那挂在椅背上的锣,吓得人们心里一紧,接着是一阵笑骂声。丧事热闹而体面,这才是一个孝敬之家应有的场面。
吃晚饭的时候,从大门口走进来的几个人,引起了大家的啧啧声。是三个老人,走路有些蹒跚,却一面走一边旁若无人相互取笑,枯瘦的脸上是一个开心的黑洞——那是毫无节制的香烟熏的;年轻一点儿的肩上挎着一面大鼓,另外两个手里拿着比筷子还粗的鼓棒。他们都比别人穿得厚,有一个还穿着一件破旧的羊皮白背心,一看就知道是准备熬夜的。原来老太太的三个姑娘,不仅请来了喇叭,还请来了本地最有名也最昂贵的丧鼓班子;这两套响器班子不知要增加多少开支。唉,到底还是人家姑娘孝敬!
灵堂外是喇叭,灵堂内是丧鼓,当两套响器一起吹打起来时,人们的脸上洋溢着对主人孝敬的敬意,对棺材里的老太太福气的妒意,而那热闹的乐器背后颂扬的也是孝敬这一传统习俗的美名。
丧事是空前的热闹。屋里屋外全换上了大灯泡,照得如同白昼。人们进进出出,各自按自己的角色行事,装烟倒茶,端盘执壶,繁忙而有秩序。突然听见一声一嗔一诧的女人夸张的叫骂,接着是一阵嘻嘻哈哈,那是被哪个男人实实在在摸了一把。可是有一人感到了寂寞,那就是少年的孝子。
夜色已深,再没有来吊唁的人,孝子的角色被冷落到一旁。棺材靠门的一头坐着他的母亲和两个姨妈,靠屋里的一头就缩着他一人。这个时候他的母亲和姨妈们早已停止哭泣。她们的悲伤写在脸上,脸上不再有泪水,她们也就不再悲伤,像往常一样头聚在一起,嘀嘀咕咕又是说不完的话题,那种小心的怕别人听见的神态,像在商讨着什么秘密。这个少年记得,就在为排班照拂的事吵架的第二天晚上,两个姨妈和母亲又在一起嘀咕了很久,显然是为什么事犯难。然后,还连夜去请来了组长,这个沾点儿亲带点儿故的丧事总指挥。当这个趿着鞋叼着烟的人被请进里屋去的时候,那一扇门便紧紧地关上了,留下他一人在外面堂屋的灯下做作业。接着里面传出女的哭声,男的为难声,又是姨妈或母亲的哭声,然后是一段时间的沉默,然后又是一阵低声嘀咕——过了很久,门拉开,放出一股呛人的香烟烟雾——母亲、姨妈们簇拥着那个重要的人物走了出来,脸上还挂着进行了什么重大决策的凝重。那个叫四贵的人趿着鞋跨进屋外的黑暗时,姨妈和母亲们还站门口叮嘱着说:叔叔啊,您可要为我们做主啊——
每进来一个可以哭泣的亲友,她们都要哭上一阵。大姨妈虽然嫁的是乡政府里的炊事班长,但在这一个地方她也算是级别最高的家属了,因此她的哭声也跟她高大的身材一样,洪亮而底气十足;二姨妈嫁的是一个村小学的教师,因此哭声中还有韵文,不是无知识的人毫无内容的干号,那份抑扬顿挫跟她讲究的穿着一样显出水平;他的母亲是一个瘦弱而劳苦的形象,毫无主见,两个姨妈哭,她也跟着抹泪。相比之下,坐在棺材旁的这四个孝男孝女,只有他自己的脸上无泪。悲伤在心里而不在脸上。虽然姨妈们凄惨的啼哭能让每一个人听了掉泪,但是他却觉得她们的哭声总有些做作的成分,如果说悲伤那也不假,但都不是为了躺在棺材里的人。大姨妈哭的是她的独生子因打架闹事被判劳动教养;二姨妈哭的是她的丈夫和一个开发廊的女学生好上了;而自己的母亲,哭的是自己的命运,年轻守寡。在婆婆病的头几天里,她们见她喘不过气时痛苦的样子,也的确眼圈发红,心情沉痛,但是时间一长,望着被单下的老人痉挛成一团,与其说是束手无策,倒不如说是袖手旁观:再后来,老人要喝水的时候,她们的动作也没有先前麻利迅捷了——回想这些往事的时候,少年比谁都悲痛,那是真正怀念这个躺在棺材里的人的痛苦,这种来自心底的悲痛是不会示人的,因此人们见不到他的泪水,他也听见了人们似乎是很开通的埋怨:到底还是个孩子,不懂事——
少年坐在靠墙的角落,浑身裹着悲伤和寂寞。灵堂里的丧鼓进入了高潮,人们都被那几个老人手里的鼓点和嘴里的唱词所吸引,更无人注意到缩在角落里的痛苦身影。人们与其说来守灵,不如说是来看热闹。少年孝子抬起头来,苍白的灯光下,是他那一张污浊苍白的脸。与少年对望着的,是靠在棺材上的那一个花圈,花圈正中那一个沉重的“奠”字;花圈的背后是用擀面杖支撑着盖子的黑亮棺材。他的那个称做婆婆的人,小时候一直背着他、哄着他的老人,这个相依相伴了他整个童年的慈爱的人,就躺在里面,将永远离他而去。而就在这天的早晨,这个少年还和他的婆婆说了几句话,虽然她说话很吃力,声音也很微弱,但是他还是听清了,她想吃果冻。因此他放学时就上了一趟街。不料只隔了半天时间,他就再也听不见她的声音了。他摸了摸自己鼓鼓的裤子衣袋,用自己的生活费给婆婆买的几个果冻,无声的泪水再次模糊了他的眼睛。棺材头下的丧盆里,燃着的几张火纸跳跃着红黄的火光,仿佛在帮他回忆和这个称做婆婆的人在一起时的一件件小事:牵着逃学的他去上学;背着病了的他去看病——每一件小事都足以让他号啕大哭,但是面对众人,他只能将汹涌的悲伤化作无声的泪水。从中午开始就没有吃一粒饭,进门就没有喝一口水,人们注意的是痛哭的姨妈和母亲,谁也不会注意这个木头般耷拉着头的小孩——痛苦仿佛只是大人们的事情。没有人来要他做这做那去扮演孝子的角色了,使他有时间不被打扰地来祭奠这个亲人了。一种从肉体到精神的哀痛这个时候才认真吞噬着他。他的母亲们仍在一旁嘀咕,棺材的对面仍是锵铿的锣鼓,以及那些看戏一样听入了迷的眼睛;而棺材的这一旁,是少年躺在椅背上耸动着的痛苦瘦弱的双肩。
当他从昏睡中醒来,发现灵堂里安静了许多;头顶上的灯泡仍是发着苍白的光芒,照得用一些锡纸做的花圈闪闪发亮。母亲和姨妈已不知去向,丧鼓的唱声在院门外突然响得高亢,那是在做收煞的尾章。大门外是一阵杂乱的脚步和组长洪亮的调度声,这声音使他明白:出殡即将开始。屋外仍是黑黑的一片,少年不知道人们为什么有天不亮时就要出殡的习惯,但是有一点儿已让他感觉到,不管口头上有什么堂皇的理由,人们的心底是想尽早结束这丧礼带来的麻烦和负担。没有了锣鼓声,没有了哭声,没有了人声的灵堂一时十分冷清,这种突然静下来的安静和即将到来的黎明的寒冷,让这个少年打了一个寒战,正在他抬起悲伤的眼重新凝视那冰冷的灵柩时,他听见了一个微弱的声音:
水——
少年一惊,这个声音多么熟悉!他仔细听了听,又听见了第二声:
水——
这声音正是从那棺材里发出的!
少年热泪狂涌,大吼一声:
婆婆!我的婆婆还是活着的!
少年扑上棺材,就去掀那棺材盖板。屋外是一片被惊呆了的脸:原来这不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他和他的母亲姨妈们一样,是一个真孝子!可是回过神来的,最先是他的两个姨妈和母亲,她们愣了一下,就一起扑了上去,将身子紧紧压在棺材盖板上,发出的哭号一下子淹没了孩子幼小的声音:
妈啊,你不能就这么走啊!你回来啊——
棺盖本来就沉重,压上了几个人,少年更是无可奈何了,但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在他的体内爆发,他抓住横在棺材中的那一根木棍,狠狠一压,沉重的棺盖撬动了,在哭声的间歇,棺材发出了惊心动魄的吱呀声。
见过世面的,还是那组长。是啊,自从他当组长以来,已不知主持过多少丧事,碰到过多少形形色色的生死场面。他立即大声命令还在发呆的人:
快快快!合棺!!
人们一拥而上。哭喊的少年和女人全被拉出人群外。少年被一双强有力的手臂抱住了,就像一只被拎在空中的青蛙,双腿还在空中乱蹬。少年还在大声呼喊:
我的婆婆还没有死!还没有死!——
在大人的痛苦中,一个小孩的痛苦可以忽略,何况他姨妈母亲的哭声已盖住了他的喊声。少年一边挣扎,一边睁大眼睛,放在地上的丧盆里的烧纸火光闪烁,使阴暗的天花板上,墙上,到处晃动着乱哄哄的人群怕陌生可怕的身影;他的姨妈和母亲的大哭大号只是制造着更大的混乱。接着少年听见一声更绝望的声音:
钉棺!
一阵铁和木头的碰撞声,钉在了少年的胸口。丧盆里烧纸的火光跳得越来越微弱,风一吹,倏地灭了。
出灵!
蚂蚁搬食一样,棺材被人簇拥着抬出了灵堂。
我的婆婆没有死!没有死啊!少年乱蹬着的脚撞到了抱着他的人的膝上,他一下挣脱了那人的膀臂,冲出堂屋。可是刚出门,又被一只强有力的手拉住了他的手臂。这时天刚黎明,而黎明时的光亮就像黄昏。他看不清那人的脸,他在挣扎中听见了那个艨胧的脸说了一句让他从此长大的话:
别闹了,人迟早都会死的。
那个脸又扭过去,对另外两个身影说:
看好他!不要让孩子伤了。
组长趿着鞋慢腾腾地走了,少年身上上来了四只手,如同钉在棺材上的抓钉牢牢地抓住了他。一旁的母亲和两个姨妈,看上去是哭得欲死欲活,她们的身边一边站着一人,那是在搀扶着并劝她们节哀。鞭炮震天,硝烟弥漫,喇叭锣鼓齐鸣,仿佛战鼓催征。
大家都快点儿搞啊,田里的油菜还等着啊!
一群人更是来了干劲。吵吵闹闹中,棺材被抬出院门,接着三把两下五花大绑,缠上粗绳,插上了棍棒,一声吆喝,被人簇拥的棺材在一片清冷昏暗的晨色里漂向前去——
走了,花圈,鼓乐,棺材。远远听见一阵鞭炮,树林上空升起一团白烟,那是棺材己上了山,即将入葬。少年的孝子一人站在院场中,呆呆出神。出来一个帮忙打杂的妇女,拿着扫帚来打扫院场,准备摆设早餐的宴席。扫帚所及,是爆竹叶,丢弃的烟盒,烟头,一次性塑料杯,人们一阵大嚼后扔下的骨头,是一场热闹过后的一片狼藉。
果冻!我婆婆的果冻!婆婆啊——
少年突然一声大喊,把低头扫地的妇人吓了一跳。只见这小孝子扑下身去,从扫帚旁抓起掉在地上的那几个己被踩乱的果冻,一边狂喊一边朝棺材远去的山坡狂奔而去。
惊魂未定的妇人待听清那狂奔而去的少年的喊声,羡慕地叹了一口气;真是满门的孝敬啊。她抬起头来,太阳已爬上了山顶,又是一个白晃晃的大晴天,远处的油菜田里晃动着收割的人影。
农忙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