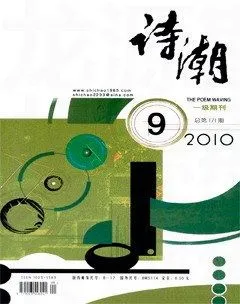诗歌本质与时代精神
尽管古今中外的诗家和学者对诗的本质和功能有千差万别的解说,当我们逐渐挣脱了对“诗言志”和“诗缘情”简单化、浮泛化、狭隘性的认知之后,都无法否认,诗是最富有个性和人性的文学样式,同样也无法否认,诗人的文化性格、价值取向和审美意识都具有时代印痕。特别是优秀诗人,他们是以先知般的直觉。领悟到时代的精神命脉。平庸的诗人和睿智的诗人有许多区别,其中之一:前者是浅显地、表象地、概念化地解释时代、讴歌时代;后者则是在诗的云霞中流动着时代之光,那是一种渗透,是一种交融,是一种自然天成,同时又是一种超越。越能体现诗歌本质的作品,就越能从不同侧面表现时代情绪,体现一个时代的快乐和痛苦,那是在霞光丽日或是阴霾满天的背景下灵魂的光亮。仅就俄罗斯诗歌而言,我们会从普希金、莱蒙托夫到叶赛宁的诗中,看到生活的不自由与灵魂的自由;20世纪的黎明用冬宫的炮声结束了千年的专制,然而一种政治乌托邦以另一种形式禁锢人的自由,人性是不可泯灭的,许多诗人和画家、雕塑家几乎同步以现代主义的夸张和变形,隐喻和象征,表现人民的愤懑和向往。艺术家伊利亚·卡巴科夫说“我疯狂地想要表现我们苏联社会的全部,不遗漏任何一页——我们一起苏醒的希望还是有的”。艺术和诗歌都无法描写每一页,却能表现时代情绪,我们从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叶夫图申科那些诗人的作品中,已经感到人性的复活和时代的觉醒。美国诗歌同样如此:我们从惠特曼的诗中,看到西部大开发的精神力度;我们从桑德堡的诗中,看到城市崛起的时代文明。由此可见真正的诗人,倘若真如哲人所说是“时代的骄子”,不管是颂歌还是挽歌,是进军号还是小夜曲,都从不同视角以不同形式表现历史踪影、文化印记和时代精神。
十年前我曾写过一篇短文《重铸桂林山水,再造盛唐之音》,旨在呼唤诗的生命之树注入时代精神内涵,使之在时间里长新。我国古代诗人们,并没有写作的使命感,却有心灵的自觉性,初唐的青春气息浸润着诗人的心扉,诗歌便从六朝宫廷靡靡之音走向广阔的生活,呈现出清新之风和鲜活之气。诚如闻一多所赞扬的卢照邻的“生龙活虎般腾踔的节奏”和骆宾王“那一气到底而又缠绵往复的旋律之中,有着欣欣向荣的情绪”。还有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的那种轻盈、流畅和安详:“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诗人的思绪荡向辽远,他探究“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己,江月年年只相似”。闻一多说,这是“一个更深沉更宁静的境界!”诗人看到的仿佛是一个更神秘更渊默的微笑,这是“一番神秘而又亲切的,如梦境的晤谈,如强烈的宇宙意识”。我说,只有那么清新明丽气象高远的时代,那种开放的文化氛圈和安详的生活景像,才能有这种青春气息和静谧情愫,才能让诗人去思考有限与无限,暂时与永恒的哲学宏奥。这是一个穿过历史烟尘新生的充满朝气自由开放的时代,自然会有“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的向往和迷茫,生发宇宙无穷人生有限的感触。这个时代赋予诗人灵魂的自由和文化的舒放。“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和“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相辅相成,前者是时代开拓的开阔胸襟和尼采那种伟大孤独;而后者是豪气满怀气象高远的劲健意绪。这是文化进程的铺垫,从此产生了气宇轩昂的盛唐之音,才有李白的《将进酒》那种超拔尘俗、邈视权贵、纵酒高歌的酣畅淋漓和放达浪漫。与之相同步飞腾的是音乐、书法和舞蹈,是王羲之、孙过庭、虞世南、诸遂良的轻盈飘逸,婀娜多姿;张旭、怀素的狂放飞动。而盛唐的音乐、舞蹈都吸纳了少数民族明快激越的旋律,与书法的奇绝变幻相映,共同构成盛唐的文化气象。这些都是音乐的诗、建筑的诗、形体的诗,都以强烈的个性特征和情感色彩,与书写的诗一起,内在而又熨帖地表现了时代精神。
我们正置身于伟大的时代,中华民族开始走向全面复兴,改革开放是这个时代的宏阔主题,也是其精神命脉,这个时代的本质特征是斗争哲学的结束、营构和谐社会的开始。这不仅使社会生活发生了急剧变革,而且催动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历史观念、审美意识乃至行为方式都发生了嬗变,无疑在诗中已有鲜明的体现。随着生产力的解放,逐步有了人的解放,中国人开始进入一种相对自由的境界,开始有一种自主意识,并且向往有个性有尊严地生活。马克思早就呼唤:
“我们要把宗教夺去的内容——人的内容,不是什么神的内容——归还给人,所谓归还就是唤起他的自觉。我们清除一切自命为超自然和超人的事物,从而清除虚伪,因为妄想成为超人和超自然的野心就是一切虚伪和谎话的根源。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永远向宗教和宗教观念宣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51页)。他所指的“宗教”是人为制造的禁锢人性的法规和理念,只有今天,我们才能拔开历史的烟尘,谛听到真理的声音,让人的鲜活的生命在诗中复活。我们从舒婷和李小雨的爱情诗中,从朱增泉军旅诗中,从吉狄马加的民族风情诗中,从雷抒雁的许多精湛短章中,从西川、翟永明等许多青年诗人的作品中,从大量抗击冰雪和抗震救灾的诗篇中,从李瑛等人的政治抒情诗中,既看到一个民族崭新的精神面貌,又从更深层的诗学本质上体现人类意识。只有这个宽容的时代,才让艺术风格、审美个性乃至创作方法多元共存。
改革开放30年来。诗人们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诗篇,但是诗歌显得平庸和细琐,缺乏表现时代精神的大气磅礴激人奋发的诗篇,缺乏传达人民心声感人腑肺引人共鸣的诗篇,缺乏思想深邃感情厚重震撼灵魂给人启悟的诗篇,缺乏表现真善美新颖独特情思优美让人的心灵得到抚慰的诗篇。
在若干缺憾中比较突出的是有大量作品浅显、浮露和概念化,缺乏新诗的审美发现,缺乏深邃的文化内涵和精神,而流于类型化的表现内涵。更为突出的是语言芜杂、平淡,缺乏诗的意韵和情韵。我们往往把语言视为情感的载体和灵魂的外壳,于是无数认识论的成果和类型化的认知就用语言承负托载了,于是无数思想的屋宇就用语言金镶玉嵌了。殊不知语言是文化的江河,靠它的流动和浇灌,诗人的心灵的原野才会花红草绿水碧山青;语言是生命之光,靠它的辐照,诗人才会风情万种。是人的有文化的生命激活了语言,给名词以诗化的命名,给动词以中国式的金刚怒目或中国式的柔情似水;给形容词以精约而典雅的形式,于是中国古典诗词的语言特色和现代意识相交融,才能形成了稳定的形神合一。
诗歌是流动的美学,它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诗人素质的提升。会更好地继承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吸纳外国诗歌艺术精华,一定会产生更多更好的体现时代精神的风格多样、绚丽多姿的艺术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