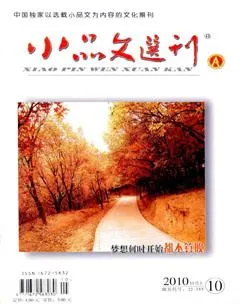一段历史的白内障
想说一点历史上的事,很远很远的事,舜禹时代的。据传,在舜帝暴死苍梧后不久,他的妃子,即尧帝的女儿娥皇、女英双双溺毙于湘江。这段富有神话色彩的历史公案被大量小说、专著、戏剧、诗歌和研究论文一再提及、描写、架构、推衍。同时,一些民间手工艺品或艺术创作也对它充满了热情,刻画、加工,再刻画、再加工,兴趣盎然,历久不衰,老少咸宜。
我要说的重心当然不是重述这段故事,而是关注舜帝死亡最大的受益者禹帝。尧帝时,显赫的贵族鲧,因陷于帝位之争被委治水,因不利“见诛”。若干年后,作为尧帝的女婿及继承人舜帝,在鲧之子禹明确表示推辞之下,乾纲独断,强令其前去治水,旨在迫害他,步父后尘,“不利见诛”。禹受命于危,为治水倾尽全力,三过家门不入——此事我理解是,禹并非不想回而是不能回,不敢回。回,势必将受到舜帝从道德层面发动的致命构陷和打击:不顾治水,惦念享福,可诛。如此,足见禹是在非常之际遇下,以最聪明和最猛烈的方式,将自己逼迫到了敏感、白热、极端、刻骨的境地。撤退的鸟群与远方的海市蜃楼,构成了不祥的隐喻;秋风中的内秀与孤独,则是历史的鼻炎与白内障。激烈的人儿得天独厚,激烈的人儿长袖善舞,一项在前铁器时代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这样于隐伏刺刀的荆棘中,或布满困兽的野林里,从禹亡命的手指上诞生了奇迹或奇迹的寓意。
奇迹的诞生意味着舜帝犯下了不可饶恕又无法挽回的错误,他不得不暗自吞下“借刀杀人”之策酝酿的恶果,立功勋卓著的禹为继承人,而非碌碌无为的亲子商均。以后,禹在重重“心计和残忍”中日渐强势,令舜日渐众叛亲离,局势趋于失控,他所信任的司法官员皋陶就在那时态度明确、坚定地站到了禹一边。此人手握国家暴力机器之要权,在禹夺权之路上饰演了至关紧要的角色。后来禹继位,第一件事就是封他为继承人,以示报恩。
我有个固执的观点:看,应抽离道德因素,否则容易未信先横,难以把握事件的要领——因其成败利钝皆攸关生死,斯人无论采取何种手段都是“生”之必然,无可置喙。所以,此问题的要害不在于禹的手段如何残忍,而在于其计划如何聪明,而此聪明的终点恰好成为了后世浪漫主义者的起点,因为在缺乏证据的旷阔时空里,鱼飞鸟泳皆有合情合理的可能。
严肃的儒家学者乐于这种浪漫,他们孜孜不倦地粉饰、书写上古三代,将血腥残酷的夺权一味化妆,变作高尚和平的禅让,无非是借死人之躯壳,演绎自家政治寓言或神话之经典,带有异常明晰的目的性和欺骗性。我读史,热在于把握人与事的微妙平衡。要知道,人浮于事或事离于人者,定有破绽可寻。
选自《今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