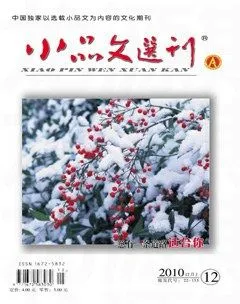云冈人
云冈矿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十多年前,我到过那里。那时我的一位小兄弟与她的媳妇住在单身宿舍里,她们两口子邀了文友若干,大家挤在不足10平米的小屋里畅饮,我们谈旧俗新习,我们谈手头杂乱而无法搁置的工作,我们谈谁谁的走向运势,我们谈内心纷乱的想法,谈到兴致处举杯共饮。最后,一位报社的朋友摊开了一张矿工报,矿工报的头版头条写着前进中的云冈人。我是那种不喜欢前进、亦不谈退步的人。但“云冈人”这三个字却在我的内心里是一幅幅熟悉的画面与场景,那怀旧的水就真的漫上了心际,濡湿了我的内心。
那是畅饮贪欢的一夜。有诗,有歌,简单的生活因此而葱郁。小憩苏醒已是凌晨,为了赶着上班,拖着欢倦过了的身体,急急地踏上返归的路途,云冈矿匆匆一瞥的景致就刻画上了心。“云冈人”涵盖着辛苦劳作的矿工,涵盖着锄地刨食的农民,涵盖着涌流而来的外来劳工……那感人的背影,那欢愉的笑声,做买卖的吆喝声,阳光下的老者,月光里的琴声,活生生的一幅清明上河图啊!
今天的云冈沟正在经历一场变革。北魏时期建造的云冈石窟现在已是世界文化遗产,作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这条曾经安详的沟壑,如今正迎来各方的宾朋。一个地域的变化,也具备了人性的迁徙。记忆中的云冈镇,云冈村,云冈人也在这样的迁徙中触动,感觉是一根知疼知痛的神经,或许,它就在岁月的肌理之中而有知。城市滚滚涌流的激情,重新荡起人们早已暗淡的热度与表情。
我曾经把建在山坡上与佛为邻的小屋称作“安乐窝”,那是我理想的憩所,一壶酒,一箪食,一瓢饮,禅释自我。诚然,追求与抵达永远充满了距离,没有理由让他们世世代代住在山坡,住在小屋。多年后,一场声势浩大的迁徙开始了。于普通的云冈人来讲,沧桑的感觉具有悲喜交织的过程,这过程中每一个人都经历着一场历练,在这种历练的过程中,纠葛就像断了环的大钟,碎了的巨响四溢的火花逐渐分散,进而淡定。真正的云冈人,他们有着大起大落的轮回,也有着一份真正的宠辱不惊,得失不计。
云冈人是普通的,同街面上任何人都相同,没有标签来甄别。石凿的大佛也遭遇着风化的过程,更何况普通人乎?历史上曾经抵达的辉煌与没落,真正是几千年的文明留下来的精神衣钵也要雾化?城市与城市在杂交中越来越相似,脾性、气味、着装、相貌,个人的理想、追求,一切都被重新组织,一切都被重新集中,残存的痕迹在哪里?在云冈人那里。
云冈人同大佛一样遭遇风化,也同大佛一样保留自我。
石凿的大佛朝拜者无数,他们求一份福禄,保一份平安,盼一日升迁,人不能解决的,到佛那里寻找答案,到佛那里归置自己。云冈人是淡定的,他们要一种与佛为邻的简单,与佛为友的自然。诚如我的一位朋友、云冈诗人张智有一首诗:我愿意创造一片叶子/那种会说话的绿叶/用它饱含童音的浓汁/召唤那只羔羊/那只/缓缓走来的/做轻声应答的羔羊。轻声应答的羔羊与怒吼的雄狮更加坚定了我内心的唯美,所谓困惑的却是为内心唯美的弱小而担忧。
生在矿山长在矿山的我曾为一些街道而备受煎熬,压抑与困惑,闭塞与落后,找不到心智微弱的亮光,也在佛前烧香,求一份宁静,求一份内心的唯美。好在有众多的人保留着内心的唯美。比如云冈人,他们不时尚,他们不追星,他们的遭遇,他们的困惑,他们的历史变迁都是随着大的变化而改变,留存的却是做人的一份底气,那十足的底气就像苍老遒劲的古松,这就是云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