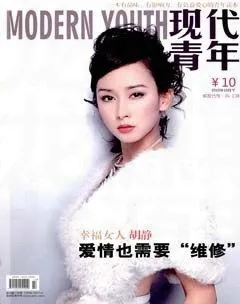张艺谋:我和“山植树”有个约会
在中国电影界,张艺谋无疑是最有成就也最有争议的导演。老知青、插过队、当过工人、摄影爱好者、电影“斗土”、国际大导演……短短几十年的人生变局,宛如电影一样,充满了蒙太奇色彩。
从《一个和八个》到《满城尽带黄金甲》,从摄影到演员再到导演,从电影到歌剧到北京奥运会开幕式,24年来张艺谋作品很多,获的奖也很多。《红高粱》壮怀激烈,让我们看到了男人的欲望和女人的性感,《菊豆》是压抑与撕心裂肺的男女情爱;《大红灯笼高高挂》则充满了某种象征隐喻,《有话好好说》有那么点儿小镇青年向城市转型的意思,尽管讲述的是北京故事,但里面的人际关系却充满了浓郁的乡村气息。
张艺谋拍摄的众多电影中,只有一部电影让批评家无话可说,这就是他在1995年拍摄的《活着》,很多人认为这是他最好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则又被视为他走向主旋律的开始,他由此从边缘走向权力话语的中心。
或许是经历新中国几个巨大的时代转型,张艺谋总是把自身命运跟国家成长联系在一起。“我们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我的信仰就是中国会越来越好。”他的确是时代的宠儿,无论是在计划体制还是在市场经济时代。《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在商业上的成功,让他彻底实现了从文艺片到商业片导演的转型。它们在内容上都充满了中国人喜闻乐见的武侠与宫廷阴谋,张艺谋美学+张伟平营销,又借力中国政府对电影产业与文化输出的渴望,让他在权力与资本上得到了高度统一。
张艺谋特有的形式美学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再一次放大,他给我们呈现了一场从未见过的华丽恢弘、水墨写意、浪漫梦幻的开幕式。儒生三千,太极阵式,海上舰队在光影之间形成了巨大气势。他深深知道:“奥运会开幕式的复杂性就像是十部大片一样,压力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即便如此小心谨慎,批评家还是把笔尖对准了张艺谋的集体主义美学。这多少有点不幸,无论他在艺术和商业上如何成功,似乎迎接他的总是批评,甚至都有刻意妖魔化的嫌疑。他早明白了这中间的话语规则,所以对待批评和指责,从不回应,也从不认同。
“你个儿大,不打你打谁啊,一定要有个个儿大的挨打嘛。今天不是我,是王艺谋,他们一样要打,要用新的力量、新的观念打你,就像我们历史上打谢晋一样,我觉得这是必然的。”吊诡的是:文化人用笔尖给他画了一幅像,然后又群起而攻之那幅像,而张艺谋本人却站在远处琢磨着自己的电影和生意。
那些“谋女郎”
“现在的90后,真长得不行。”
“我只想拍我感兴趣的东西,一种清新、自然和返璞归真的东西。”
——张艺谋
9月16日,张艺谋的新片《山楂树之恋》“首掀盖头”。电影《山楂树之恋》未上映先热。据说,为寻找女主角“静秋”,张艺谋的副导演们跑遍了全国各大艺术院校,看了五六千女孩,引来数万试镜者,结果都因不够“清纯”而未入法眼。最后,来自河北石家庄的一名高三学生周冬雨杀出重围,被张艺谋笑纳片下。
张艺谋在为《山楂树之恋》选女主角时开玩笑说:“现在的孩子越生越难看,漂亮姑娘都不和帅哥生孩子,全去找煤老板、有钱人、老男人。所以现在的90后,真长得不行。”没想到张艺谋一开玩笑,大家反而都不适应了,大家因此热议连连。
一直以来,清纯青涩、清爽秀灵,成为张艺谋选秀的基本策略。从最初巩俐干净又淡然的回眸一笑到章于怡眼神中溢出的青春与单纯,都是“谋剧”的主打色调。可见,寻找清纯早已经融为张艺谋电影故事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现在清纯女之所以越来越少,张艺谋分析与“老男人”有关,制片人张伟平觉得,与“生活开放态度随便”有关,还有人说与娱乐圈盛行的“潜规则”有关。
张艺谋表示,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照片,每个人都显得那么清纯。其实,不管在哪个时代,任何人都曾清纯过,只是在流行互联网、美容整形、打情骂俏的今天,这个阶段被提前并且周期大大缩短了。
早在十几年前,张艺谋的一部经典《秋菊打官司》将巩俐推上了国际舞台,而巩俐也令张艺谋的电影走进了世界。这里边女主角的名字就叫秋菊,且是一部以乡村题材为背景的中国旧社会农村的黄土电影。在当时巩俐算得上是中国数一数二的女影星,清纯指数虽在今天看来仿佛有点阿妈级,但在当时她可是广大的中国工人阶级男人的清纯偶像与梦中女郎。再接下来的张艺谋的电影中,如前几年的《满城尽带黄金甲》,那满地的金灿灿的菊花想必大家都记忆尤新吧,影片当中的重要情节是准备在中秋佳节共饮雄黄酒登高赏月观菊花,瞧瞧这秋日菊花又来了。再来看看《我的父亲母亲》与《一个都不能少》也是以乡村题材为背景的乡土电影。而从《秋菊打官司》到《一个都不能少》之间,张大导演也拍摄了不少商业片,但是老谋子在国际上拿大奖的通通都是反映上世纪50、6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那含有浓郁乡村色彩的影片。与此同时另外一个热议的问题便是继巩俐之后的章子怡、董洁而萌生的“谋女郎”的话题,她们三人样貌的“协和一致”曾经被人们认定是谋女郎的必要条件之一。就这样,在董洁之后仿佛每次张艺谋的女主角人选都与他的电影同样具有了商业价值。而在此之后《山楂树之恋》的女主角让“谋女郎”有了质朴的回归。
质朴而有力量的乡村风和大红大黄大绿的浓烈色彩
“城市题材和农村题材不能构成一个话题,现在好的题材不多,我只是找有感觉的。合适的拍。”
——张艺谋
他从来不拍电视剧,只拍电影,而他的电影不论是城市题材还是农村题材,不论是现代还是古代,总是令人刮目相看。在张艺谋看来,“城市题材和农村题材不能构成一个话题,现在好的题材不多,我只是找有感觉的、合适的拍。”从《红高粱》到《山楂树之恋》,尽管中间有一些极具商业元素的电影,但最终张艺谋的电影没有离开乡村风。
纵观张艺谋的电影:乡村、秋结、清纯女似乎是一直不变的选择。心理学中似乎可以将其分析为有某种特定的选择性心理情结。或者这些能够更容易让老谋子获得比商业电影更多的实惠:或者他依然固结在那个于他有着最根深蒂固。情愫的内心世界,但不管怎么样,《山楂树之恋》这部被称为史上最干净的爱情电影还是值得我们期待的,也许看了这部电影就更能让你领略到张导的第三世界将爱情固结的那一片净土。
张艺谋最为人所称道的应该是他对色彩的敏感,他的电影往往是以大规模地运用大胆的色彩而折服观众,《红高粱》中咄咄暹人的血红、《大红灯笼高高挂》中抑郁至极的暗红、《黄土地》中深沉凝重的土黄,到了《英雄》则凝成色彩纷呈的华彩乐章。尽管业内人士对此褒贬不一,然而张艺谋的电影能够征服国内外的无数电影专业人士和爱好者,这一点却是不争的事实。
大师或匠人 自在人心
“每位导演和演员最后命运肯定是这样的,这就像生命轨迹,不能避免,它是规律。我们不能违背这个规律,每个人都不可能永远足弄潮儿。年轻人总是追赶时尚和流行的,他们或许认为你是大师,但你千万别把这个大师当回事,或许这其中尊重大于兴趣。”
——张艺谋
冯小刚不久之前曾抛出争议言论中国电影没大师。张伟平在之前接受专访时则矛头直指冯小刚说:“有没有大师不是冯小刚一人说了算的。”享誉海内外的吴宇森一直被称为“电影暴力美学大师”,谈及“大师”的称号,吴宇森谦虚表示“我不习惯被称为‘大师’,也不希望别人称我为‘大师’,大师很孤独。”
那么中国电影到底有没有大师?吴宇森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他认为中国电影所谓“大师”还是有的:“其实大师有很多方面的,比如张艺谋、陈凯歌、贾樟柯,还有冯小刚,我们都非常尊重,以他们的成绩,我们称呼他们为大师也不为过。”
有媒体关于此问题问及贾樟柯时,贾樟柯回答说:“我个人认为,中国电影还是有真正的大师。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他们在我心中,就是大师。陈凯歌的《黄土地》、《霸王别姬》拍得非常精彩,曾让我落泪,张艺谋的《红高粱》、《活着》,让我热血沸腾,冯小刚的《集结号》、《唐山大地震》,这些优秀影片,影响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就足以证明,他们是中国电影的大师。”
那么何谓大师呢?张伟平说他理解大师的一个标准就是“在中外电影界享有盛誉”,你不能光中国人知道,一出国门就不知道你是谁了。你的作品要被全世界观众所认同,国内外都有影响力。
那张艺谋是大师吗?张伟平说他不能说,“因为我是他的制片人。但在欧美观众里打听他,有多少人知道张艺谋?几乎全知道!除了张艺谋他们还知道中国哪个导演?他的作品赢得了海内外观众认可,这是不争的事实!他是在用作品说话,而不是自己在那自吹自擂。”
对于大多数观众来说,知道张艺谋这个名字是在看了他导演的影片《红高粱》以后。这部片子,以中国观众过去未曾见过的浓烈色彩和豪放风格,在中国影坛上炸开了一个响雷。尽管在电影界内外,人们对这部片子褒贬不一、争论激烈,可是到头来,张艺谋对电影语言的出色运用以及他在这部片子中所塑造的与众不同的银幕形象,还是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交口称赞。1988年,《红高粱》不仅获得了中国的“百花”、“金鸡”两项大奖,还在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征服众多评委,获得了最佳影片“金熊奖”。这个“金熊奖”的获得,标志着中国影片开始真正走向世界,于是,张艺谋和《红高粱》理所当然地成了神州当年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中国有许多优秀电影导演,谁也不敢保证拍每一部电影,都是叫好又叫座的好片子。假如说,一个优秀电影导演,拍三十部电影,观众要求他三十部电影全部要拍成经典,这是不客观的,也做不到的。张艺谋算不算大师,我想大家所应考虑的不是“大师”头衔的问题,而是张艺谋为中国电影做了什么?正如中国著名演员和导演姜文所评说的: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红高粱》等一批优秀的中国影片在各种国际电影节上多次获奖,使中国电影在当今国际影坛上占据了一席之地。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无疑,他是一个用镜头向世界描写中国的人,从摄影师到演员再到导演,他都有很浓烈的中国风。陈凯歌说他像秦俑,因为是秦人第一次统一了天下,张艺谋有那种凝聚中国电影的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