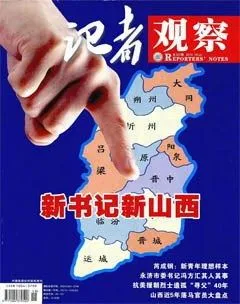理论争鸣
1 中西政党党内民主发展态势比较
谢 峰
西方政党党内呈现民主化与集权化共同发展态势,明显体现在党代表大会功能的演变上。大会曾是政党重要选举及重大决策机构,但其权力正出现分流,部分权力下移至普通党员,部分上移至党领导层及议会党团,大会的决策功能普遍弱化,选举或批准选举成为其主要任务。民主化与集权化并存表明西方政党在党内代议制民主长期发展之后进入一个新阶段,即向直接民主发展,此阶段的任务之一是恰当运用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两种形式,任务之二便是在民主已有较好基础之上平衡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民主与集中不可偏废,政党不仅需要民主来增强合法性与支持度,同样需要集中保证效率与权威,两者的相互制约是西方政党党内民主化与集权化并存的重要原因。
相比西方政党,民主化是中共党内压倒性发展趋势。多年来中共权力运行以集中为主,民主与集中处于失街状态,由此滋生很多问题。鉴于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集中过多而非民主不够,因此,进一步发展民主,平衡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是中共改革党内权力运行的一大趋势。从近年实践看。中共在基层发展直接民主,如村党支部书记和乡镇党委书记直选;在中高层发展代表制民主,如中央委员实行一定比例的差额选举,完善分工合作的集体领导制等,党内民主呈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发展路径。摘自《学习时报》
2
新左派新在哪里?
马立诚
上世纪90年代,新左派思潮在中国登场。新左派新在哪里?
人们还记得,老左派曾经高分贝抗议《物权法》,理由是这个法的内容“违背了苏维埃立法原则”(遗憾的是,今天俄罗斯立法都不再以“苏维埃”为据了)。
与老左派有所不同的是,新左派不再热络于继承斯大林主义的苏联遗产,也很少操弄“计划经济”“没收私产”“阶级斗争”“谁战胜谁”一类话语。他们在文章中谈论较多的是社会公正和参与政治。新左派批判资本,讨伐资本主义,反对跨国公司的“统治”,仇恨“市场拜物教”,批评全球化和wTO,嘲讽现代性以及与现代性相关的启蒙和理性精神。部分新左派人物认为中国已经变为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抵制资本的“邪恶统治”,新左派甚至称颂文化大革命。
还有一个表达上的差异。老左派的表述方式,多是过去大字报的遗音,义愤填膺,但逻辑不足,没说两三句就点名辱骂,不免失之于情绪化和简单化。表面上看杀伤力十足,读了却有过气之感。新左派代表人物的文章,旁征博引,比较西化。他们引述的内容,尽量追踪西方新的左翼思想。很多读者认为新左派有些文章食洋不化,晦涩难读。一句话,比起老左派的“旧时曲”,新左派更具当今西方左翼先锋理论色彩,更新颖、更洋化,用大学生的话来说,更时髦;用易中天的话来说,这一套,老左派是“玩不来”的。
新左派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群体,有海归新左、本土新左;有理论新左、文学新左,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他们的理论主张也不完全一致。总体来看,新左派代表人物的主张,基本上来源于西方左翼理论。也有一部分本土新左派人物,借鉴和承袭了老左派的思想,其主张与老左派大致相同。
然而,不少学者指出,新左派很少剖析国内政治体制方面的弊端,也很少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这是新左派思潮的重大局限。还有学者指出:
“新左派揭露批判腐败、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陷入了和老左派同样的困境:他们没有提出解决办法,没有什么建设性,在解决中国问题的价值方面乏善可陈。”
台湾《联合报》2010年5月发表文章,说中国需要“全新的”新左派。该文说,新左派应该反省一番,放弃鼓吹国家主义,除了批判资本主义和金钱万能之外,还应监督政府,追求“爱好和平、崇尚自由、推己及人的大爱”,这样才能对应时代。摘自《经济观察报》
3 监督让我们在道德上变得更好吗?恩里斯·韦斯特科特著吴万伟译
想象一下就在上帝警告亚当哪些水果可以吃哪些不能吃之后不久,派人在伊甸园安装了闭路电视摄像机,用来监视智慧树的一切。蛇爬到夏娃跟前,诱惑她偷吃禁果。夏娃伸出手想要采摘,但就在最后一刻,她注意到了摄像机,只好作罢。结果:没有罪恶,没有堕落,也没有被上帝从伊甸园中赶出来。所以我们不必要在长满荆棘和蒺藜的田野里终生劳作,不必汗流满面得以糊口,不用遭受生孩子的痛苦,我们都觉得没有必要穿衣服。为什么上帝不做这些,让每个人都免于这么多的痛苦呢?
也许,上帝想让亚当和夏娃因为正确的原因而做出正确的选择。他想让正确的行动不是出于对于监督的恐惧而是出于爱上帝和对正义的尊敬。因为害怕被逮住而不吃禁果不会为你赢得道德上的称赞。毕竟,你不过是出于自利的考虑而采取了行动。
这些思考旨在为下面的问题提供一个框架:无所不在的监督对我们的道德人格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里有一种思考方式:监督给人启迪和教化一一它塑造人的性格,把义务和自利结合得更紧密。监督越到位,人们就越不大可能违反规则,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就养成遵守规则的习惯,结果就是更少道德失范的例子和有助于社会和谐的行为规范。
但是有另一个视角一一康德伦理学指导下的视角:不断增强的监督力度可能带来某些功利主义的好处,但我们付出的代价是道德人格的下降。不错,我们做错事的情况少了,在这个意义上,监督或许让我们变得更好,但它也阻碍了我们作为道德个人的成长。从这个角度看,道德成长涉及到更加接近圣人理想,成为只渴望做正确事的人。18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描述这样的个人拥有了“神圣的意志”。
监督帮助我们走在正确轨道上,因此强化我们的习惯成为第二本性。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它阻碍人们的道德发展,通过扭曲或者遮蔽真正无涉利益的行为的圣人理想。那个理想是值得我们永远拥有的。
有人可能反对说圣人理想过于乌托邦了。确实是的,但乌托邦理想是宝贵的。不错,它不能帮助我们解决具体的、特殊的、短期的问题,如怎样让醉洒的司机不要开车或确保人们不逃税。但是,就像遥远的星辰,它们为我们提供用来确定航向的灯塔。理想帮助我们积累取得的每个进步,提醒我们要到哪里去,是否朝那个方向再继续前进等。
我们理想的社会是,如果税是必要的,人人自由和愉快地交税,就像他们交自己热情参与的俱乐部的会费,公民和政府相互信任。我们知道当今社会离这样的理想还很远,但我们应该警惕那些让我们离这个目标更远的行为。道德教育的目标之一就是培养良心,我们心中那个小小的声音,告诉我们应该做正确的事,因为它是正确的。但随着监督的无处不在,这样的机会越来越少,良心变成了我们内心悄悄告诉我们的声音:或许有人在什么地方看着我呢。
4 推动中国政改的四大力量
辛 鸣
阶层分化奠定了民主的基石。民主的出现、扩展、壮大需要有一定的社会基础,这一基础就是社会阶层的分化与阶层意识的凸显。中国社会这些年来,社会结构不断变化,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不断涌现。不同的阶层与群体都把自己的利益诉求提出来,相互协商、相互交易,你来我往、讨价还价,在尊重少数的基础上接受大多数的选择。民主就这样开始出现、滋长。
科技进步让权力不再能独断。进入互联网时代,开放的技术状态直接导致相应开放的社会状态,公开、透明日渐成为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特征,任何权力的行使都不得不接受社会大众的评判与检验。任何人、任何群体、任何组织,都可以通过网络来表达他的要求、传播他的理念、贡献他的意见,并且通过网络寻找志同道合的赞同者与支持者,对现实政治生活中的权力行为产生影响。
社会转型使得法治成为必须。市场经济改变了社会群体生活的轨迹,也改变了人们的行为模式。越来越庞大的社会系统、越来越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越来越微妙的利益格局,让如今的社会越来越充满不确定性。不确定的社会什么最确定?法治。陌生人的社会什么最权威?还是法治。开放的社会什么最靠得住?仍然是法治。法治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越发凸显。当然,法治在中国社会刚刚起步,法治社会仍有待成熟。但从乐观的方面看,大众已意识到法律的重要性,表明他们已认可了法律的权威,这正是法治取得的初步胜利。
新期待不断拓展权利的清单。今天的中国老百姓关心的是经济小康之后的政治小康、文化小康,要求社会主义民主大进步,要求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要过上“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要生活在“更加公正、更加和谐”的社会中。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大上把这称之为是“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其实,这新期待就是对权利的呼唤。社会民众每一个新期待的提出,都意味着中国社会的权利清单又加长了一页。新的需求必然引起新的变革,社会的需求更能把社会推向进步,更能把政治体制改革推向纵深。
我们有些同志往往对一些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豪言壮语与鲜明态度给予厚望,事实上,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来说,自觉的决心与态度固然重要,客观的“不得不”则更加现实和有意义。摘自《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