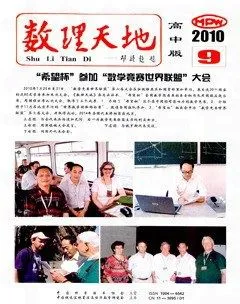学问的创造之培养独创性
由此可知,我感到不安的是,不知什么地方发表过同样内容的论文。一晃十几年过去了,就是今天,这种不安也没有完全消失,只要一提起学者的不安,我就情不自禁地回忆起这段经历。当年妻子给我的评论是:“我第一次看到你显得这样疲惫不堪。”也许我的确疲惫不堪过。
在即将退休的前一年,昭和五十六年(一九八一)三月,我来到美国佛罗里达半岛的帕姆科斯特,出席每年一度的专业讨论会。主持会议的仍然是我的老朋友雷夫丁教授。不同的是,出于某种考虑,这次把会场从萨尼贝尔岛迁往帕姆科斯特。我受托在这次讨论会上作特约演讲。我准备发表一批实验结果,这些结果使化学反应路线理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也许是就要退休的缘故吧,这一年杂务事特别多,直接从事研究工作的时间几乎全挤没了。但一想到退休后将失去亲自从事研究工作的机会,便又振作精神,开始为演讲中大部分内容作定式计算。其实计算工作委托给研究室的年轻研究人员也完全可以胜任,只是我把这件工作当作是最后的工作,决定亲自来完成它。
然而“不服老”却导致了一次意外“事件”。由于庞大的计算没能按时完成,直拖到出发前几天才整理好送交打印。我稍微松了一口气,躺在床上。天不亮又突然跳起来,禁不住叫到“完了!”
原来,计算结果虽然是正确的,我却突然发现计算过程中的公式推导有错误,这种经历还是头一次。结果有错误是经常发生的事情,然而一个正确的结果,其推导过程却是错误的这倒是从未经历过的。
在这之前,我已经事先把自己的特约演讲要点提供给专题讨论会的组织人,整个演讲基本上用的都是过去式,如果因为出了错误而把这段内容撤回来很不合适。
每当想起此情此景,仍使人不寒而栗。所谓“一筹莫展”大概指的就是我这种心情吧!一点也不敢耽搁,从发现错误的那一刻起,我马上重新计算。计算的过程中,头脑里还不断设想各种“可能出现的可怕场面”。光是在心里制服这些自寻的烦恼也需费一番苦功。经过夜以继日的计算,终于使数式前后相符,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这时,距出发日期只有一天了。
有人曾经写过,学者随身携带的东西就是不安,但受到如此集中、致命的打击,实属罕见。用“累”、“疲劳”等字眼都不足以形容,应该说是悲剧般的体验。
讨论会开幕后的第二天,我的演讲如期进行。这个多灾多难的演讲内容分两期刊登在《国际量子化学》杂志上,我化险为夷了。
讨论会一结束,我们又来到北加罗莱纳大学演讲,当晚住在该大学巴耳教授家里。教授邀请我们夫妇在一家名叫查贝尔·希尔的中国饭馆吃饭。这家饭馆的桌子上设有机关,只要放进一个硬币,就会自动跳出一个神签。我半开玩笑地抽出一支,啊!上面写着令人高兴的字眼:“要甘当劈柴,它将点燃起您更大的希望之火!”
回国后不久,便收到华盛顿美国国立科学院发来的电报,我被当选为该院的外国人院士。不知怎的,我又记起那次抽签的情景。巴耳夫妇想看看这支签,我却没给他们看,还开玩笑地说:“这是机密。”“啊,明白啦,是有关女人的吧!”巴耳夫妇也开玩笑地接住我的话。我顺口回答说:“对啦,对啦。”自从获学士院奖以来,十九年过去了,这一荣誉凝聚了巴耳教授以及许多朋友们的善意和友情,我真后悔当时为什么没把签给他们看一看呢?
直觉和独创性
我不是个电视迷,在吃晚饭的时候,边饮啤酒边用眼睛盯着电视画面,就算是看电视了。不过出于长年养成的习惯,就是在看情节复杂的故事片时,也要在手能够着的地方备下记录稿纸和铅笔,以便头脑里忽然闪过什么念头或者一下想起某个诱导公式的时候,就能随手记下来,以防消失。一旦计算起来,就完全听不见电视的声音了,情节达到高潮也不为之所动。(待续)
——摘自《学问的创造》 戚戈平 李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