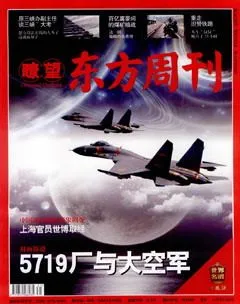乌尔里希.贝克:中国之于世界的使命为何
2010-12-29 00:00:00乌尔里希.贝克
瞭望东方周刊 2010年31期

过去几年内,我数次到访中国,并和许多同行、知识分子和政治家进行了讨论。访问期间,我发现,中国具有一种反复实验的精神,这种精神是我在西方世界没有发现的。
请让我来举三个这方面的例子。它们是:欧洲危机、中国日益加剧的个体化倾向和中国的生态化转向。
中国正在经历特殊的“去政治化”
欧洲危机始于雅典,并蔓延至里斯本和马德里,或许也包括伦敦。然而,认为正在蔓延的主权债务危机仍仅限于欧元区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这一危机是整个西方世界的财政危机。
而令我大为惊讶的是,希腊危机正在影响美国,但似乎并未影响中国。西方坚信的美国是“避风港”的看法因此显得很滑稽。
因此,我和其他许多人都想知道:在个人和国家共同经营的中国经济中,抵制这种主权债务危机的力量从何而来?
无论是欧洲,还是中国自己,都认为中国的社会生活是由集体认同主导的,因为中国的集体制结构是由儒家伦理和共产主义政策共同建构的,而个体行动和选择却没有占据多少空间。
然而,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中国正日益变得个体化一不仅人们对个体的认知正在改变,而且人们对个体自由、个体选择和个体性的期望值也正在增加。
正如中国学者阎云翔的研究所揭示的那样,个体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单位,与此同时,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等各领域的变化也正在进行。中国的发展道路正在以一种完全不同于我们欧洲过去和现在所经历的方式而展开。 在中国,个人的重要性与欧洲不同,它既不彰显于制度性的安全框架中,也不以公民、政治和社会基本权利为基础。在中国,宪法没有确定个体化的地位之前,对经济、劳动力市场、日常文化和消费的管制就已经开始放松了。
因此,当下的中国正在经历一个非常特殊的“去政治化”过程,也就是以市场为基础的个体化进程,而其结果尚不得而知。
在中国通往现代化和个体化的道路上,存在着一个标志性的矛盾:短期或长期的中国模式——“无(政治)参与的个体化”——是否可能?
还有第三个例子也引发了我的思考:在西方国家,推动国家(和全球)从高碳到低碳经济转型的创新体制引发了大量的辩论和冲突。然而,中国正在进行这种制度创新!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独立的温室气体排放者,同时作为一个飞速发展的经济超级大国和未来潜在的地缘政治超级大国,中国堪称全球低碳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发展“中国世界主义”是否可能
提到上述三个问题,我主要想说的是:中国将向世界提供的愿景、对世界负有的使命究竟是什么?
在我参加过的关于中国的众多讨论中,我尚未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要中国的国家发展规划成功了,中国就将不断地发展出一种关于世界的“想象”,并调动中国的文化力量,使其与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相匹配一即使中国明确否认自己是全球的主导力量。
然而,中国任何这样的发展规划都必须为更大的世界提供答案。而不是仅仅甘愿做眼中只有中国的中国一即使是一个伟大、繁荣的中国。
我的核心观点是,发展出一种来自中国、但能够被世界普遍接受的“中国世界主义”理论体系(chinese cosmopolianisrm),对于中国是一项真正的、格外困难的挑战。(我甚至不清楚,“世界主义”这个西方概念,能否在中国找到一种适当的译法。)
在这里,请允许我引用一些同行的观点。我的一位同行坦言,“‘人道’(humanity)并不是一个通用的中国概念”,尽管中国也有儒家人文传统。他说,他是刚刚认识到这一点,并且是通过国际合作获得的这种认识。
另一位社会科学家指出,她是从自己在国外的经历中学到了一种“人文精神”。她也动情地补充道,“我在英国期间获得的最大收获是,这段经历使我开始思考‘他者’,并关心‘他者’,无论他们来自何方”。
但与此同时,他们都强调明确承认中国国家发展地位和恢复对中国文化尊重的重要性。上述观点又是否开启了一种特殊的“中国世界主义”呢?
德国前总统霍斯特·科勒并不是一个以讽刺和幽默著称的人。但前几天,他讲了一个有关中国的笑话。这个笑话在德国人听来非常有趣。科勒说,有一个非常友善的中国商人对他说,“亲爱的总统先生,我要告诉你的是,我最喜欢购买的是德国工厂和企业!它们组织管理得如此之好!”
这就是我要讲的关键:中国相刘世界其他地区的愿景和使命,绝不应仅仅是富有和友好的中国老板在全世界到处大手笔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