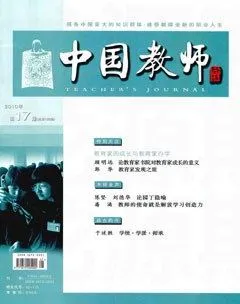知识的客观性与教学的间接性
近年来,随着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在我国教育理论界的兴起和传播,人们一般性地拒绝谈论知识的客观性,对“教学的间接性”也产生了诸多的怀疑和批判。有感于此,笔者也来发几句言论,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近年来,随着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在我国教育理论界的兴起和传播,人们一般性地拒绝谈论知识的客观性,对“教学的间接性”也产生了诸多的怀疑和批判。有感于此,笔者也来发几句言论,以求教于学界同仁。一、知识的客观性
人们对于客观性的理解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它首先关涉到对“实在”的理解。一般来说,近代认识论习惯于把“实在”理解为不是我们的随意设想、不为我们的想象所左右的东西。由此,人们认为,认知就是再现心以外的事物。或者说,“实在”是一个“经验先给予的自明的世界”,而认识的任务,就是去“追问这个世界的‘客观的真理’,追问对这个世界是必然的,对于一切理性物是有效的东西,追问这个世界自在的东西”[1]。这其实就是客观主义的知识理想,它企图建立的是一种“与人无关”和绝对超脱的客观知识。这种理想向往的是一种“绝对与个人无关的知识,这种知识不承认任何个人的作用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我们并不在其中的宇宙图景”[2]。这也就是近代认识论所理解的知识的客观性概念。
但是,在现代,尤其是现代后期,随着人们世界观、宇宙观的转变,这种知识理想已经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质疑。波兰尼在《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认识论》一书的前言中开宗明义地说道:“我的出发点是拒斥科学的超脱性的理想。这种虚妄的理想在精密科学中也许危害不大,因为在那里科学家们对它并不在意。可是它在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中产生的毁灭性影响,对于我们视野的蒙骗已经超出了科学的领域。为此我要建立一种不同的和更广义的知识理想。”[3]但是,与此同时,人们并没有完全拒斥知识的客观性这样一种概念。在波普尔看来,知识的客观性指的是能被主观间相互检验、非私人的意义。并且,他还用“逼真性”这一概念表明新的理论比旧的理论更加逼近真理。波兰尼认为客观性是指认识与某一隐藏的现实建立联系。他说:“从认识与某一隐藏的现实建立联系——这种联系被定义为预期着范围不定的、依然未知的(也许还是依然无法想象的种种真实的隐含意义的条件)——这种意义上说,这样的认识确实是客观的……”[4]。
承认知识的客观性有利于把知识与主观任意或那些“自以为是”的个人意见或臆想区分开来。比如,波兰尼提出“个人知识”这一概念,力图向我们证明的是,所有科学知识都要依赖于认知者个人的整合、判断、信念、热情、承诺等,也就是必须有一个“个人系数”。任何科学理论的建立都是以科学家的个人判断为基础的。但是,“个人知识”不等于是主观的。他之所以用“personal”而不是“individual”作为“个人知识”的限定词和形容词,也就是避免人们把“个人知识”理解为私人化和主观化的东西。或者说,虽然在认知过程中认知主36c88cf0501559a33875a0e1de0041cd体的求知热情、个人寄托等主观因素影响着其对认知对象作出的选择和判断,但这并不表明知识就因此是主观的。“如果承认知识是由认知者塑造的,是否就意味着知识可由认知者自以为是地决定?认知者充满激情地探求某项课题的正确解答,这令他没有机会武断决策。虽然他不得不揣测,但他也必定竭尽全力以求作出正确的揣测。对研究对象之真实存在性的感知能使我们免受主观偏见的左右,从而令塑造知识的过程成为负责任的人类活动”[5]。因而,“把个人性和客观性这两者的融合描述成个人知识,这似乎是有道理的”[6]。
这里,我们有必要将认识过程与作为认识结果的知识区别开来。认识过程牵涉到认识主体的精神气质以及行动、反应的意向和与之相关的思想过程,因而显得更主观化一些。而作为认识结果的知识,对它的确认,首先要经过主体间的检验,至于采用什么样的标准,则要视各个社会或时代的具体情况而定。当然最终还需要实践来检验。即“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思维的此岸性”[7]。
二、教学的间接性
知识具有客观性,它也就完全可以以“游离于认识主体之外的纯粹客观”的形式为社会分享和交流,以此构成一个客观的知识世界。这个客观知识世界也就是波普尔所谓的“世界3”,即“思想的内容世界,尤其是科学思想、诗的思想以及艺术作品的世界”[8],它是人类精神财富以及其载体构成的领域,是人类创造性功能集中显示、确证和提高的世界。这也是文化人类学家卡西尔所指出的由人类所编织的且人身处其中的“符号世界”。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是这个符号宇宙的各部分,“它们是织成符号之网的不同丝线,是人类经验的交织之网。人类在思想和经验之中取得的一切进步都使这符号之网更为精巧和牢固”[9]。现象学大师马克思•舍勒认为,在知识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一些基本公理。其中首要一条就是人类的全部知识是先于个体、预先给定的。也就是说,对于任何个体而言,只要他是社会的成员,那么,人类的全部知识对他而言,就不是经验性知识,而是“先天”知识,先于个体自我意识层次和自我评价意识而存在。换句话说,没有“我们”也就没有“我”,“我们”又充满了先于“我”而存在的内容。或者说,对于个人来说,种族经验(间接经验)始终具有先在性,对个人构成先验的存在。
同时,知识的客观性给予我们这样一种基本信念:即我们完全可以借助于前人创造的知识来获得在世间的有效生存,既可通过知识认识世界,也可运用知识改造世界。人类的发展本身证明,知识(间接经验)对于社会的生存、延续和发展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波普尔曾经用两个思想实验指出客观知识世界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性。实验一:如果我们所有的机器和工具,连同我们所有的主观知识,包括我们关于机器和工具以及怎样使用他们的主观知识都被毁坏了,然而,图书馆和我们从中学习的能力依然存在。显然在遭受重大损失之后,我们的世界会再次运转。实验二:如果机器和工具被毁坏了,并且我们的主观知识,包括我们关于机器和工具以及怎样使用它们的主观知识也被毁坏了,并且连同图书馆也被毁坏了,以至于我们从书籍中学习的能力也没有了。那么,我们的文明在几千年内不会重新出现。我国学者李鹏程先生指出,在千百年的人类历史发展中,物质文化可能被毁灭,语言也可能演变,但只要记载人们的精神文化的典籍留存下来了,人们就有一笔由知识、意志和审定精神所构成的文化世界的财富。人们在一些时候,尤其在战争、外族入侵和自然灾害的危机时,是依靠这样一笔财富来维系个体以至整个民族的生存的。
正是由于以知识为主体所构成的文化世界的积极意义,因此,对于儿童来说,他必须首先从这个既定的复杂的文化世界中吸取价值和意义,而不像原始人类那样靠自己经验知识的缓慢积累来创造一个有意义的世界,然后在这个世界中肯定自己。也就是说,一方面,社会的延续和发展本能地要求着儿童继承这些已创造的知识财富。社会成员的生和死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事实,因而有必要教给新生成员那些群体的兴趣目的、知识、技能和实践等。另一方面,知识所特有的客观性品质也说明了这样一种事实:即知识对于学生来说,具有促进个体发展的潜在价值。他只有通过对前人所创造的知识的研习,学生才能超越自身经验世界的狭隘性和局限性,获得认识的提升和生存力的增进;同时,他也才能从中获得赖以建构新知识的思维图式,成为新知识的创造者和现实的改进者。
基于以上理由,我们认为,主张以书本知识(间接经验)为主进行教学并不是一种倒退,而是一种坚持,一种清醒。
三、是什么在影响着教学
在实际的教学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场面:同样的知识或者说同样的教学内容,由不同的教师来上,有的教师上得意趣横生,学生主动参与的积极性高;有的教师却照本宣科,教室里一潭死水。在这之中当然有许多复杂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教师的知识观不同,导致教师的教学行为各有差异,产生不同的教学效果。正如索尔蒂斯所说,“我们如何思考知识,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我们如何思考教育”,“从根本上说,知识的概念与教育的概念是无法分离的,因而,我们对关于知识和认识方面可能存在的许多问题的回答,对我们教育者如何思考和行动将有重大影响”。[12]因此,可以这样说,把教学界定为教师引导学生掌握间接经验(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过程或者认为课程的核心是知识,并不必然就导致以知识控制学生、使学生失去学习的主体地位。关键在于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知识或先于学生存在的人类经验。如果我们把知识理解为一成不变的真理,那么自然而然就会拒绝从任何程度上来审视知识或质疑知识,因而学生在认识过程中的一切“个人系数”也将会被强制性地剔除或被压制起来。但是,如果我们把知识理解成一定典范内的相对真理,我们就会以该典范的评价标准来评价知识,并逐渐突破该典范以革新知识。这样,学生认知的“个人系数”才被突显出来,学生的个人意见或见解也会得到应有的尊重,因而不致使知识的客观性掩盖学生的主体性,反而使知识发挥它于促进学生发展方面的巨大的潜在价值。
我们真正需要研究的是有哪些方式或途径能够促进学生对间接经验(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掌握,并将其转化为个人的经验和智慧。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间接经验(这里是动词),一是直接经验(这里是动词)。在间接经验方面有哪些方式?在直接经验方面又有哪些方式或途径?在我们以往的教学中,确实一直是间接经验或间接认识占据首位,并且在实际上走向极端,将直接经验或直接认识彻底地排斥在教学之外,不被正视,不被考虑。在此次的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当中,直接认识的方式被引入,以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开设为重要象征。但是,这种直接经验的方式又如何使学生不耽于个人狭隘的经验,争取与他人或人类的经验或视界达到融合呢?它又如何使学生超脱于日常庸俗的生活世界并追求一种可能的生活(这种追求是人类前进的永恒动力)呢?教师在其中又如何发挥他的指导者或引导者的作用呢?这些问题恐怕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
参考文献:
[1]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与超验现象学[M].上海:上海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