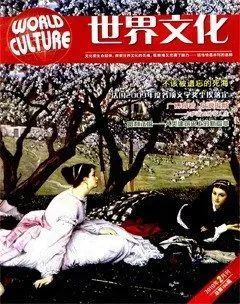赫尔辛基散记
一座城市与大海相邻,那是一种造化。何况赫尔辛基紧靠着波罗的海。我一直对波罗的海心存好感,倒也说不清什么原因,也可能觉得这名字听起来很别致很悦耳很可爱?波罗的海荡漾在无比遥远的北方,我从来都固执地认为它是一个沉静甚至充满冷峻之美的海。
果不其然,浮想千回不如亲眼一见。我迢迢万里来到赫尔辛基,首先也可说最难磨灭的印象,那就是赫尔辛基,太托波罗的海之福了。来自芬兰湾,准确意义上说,来自波罗的海的腥甜温润的海风,柔然无声、母性十足地轻拂着赫尔辛基。于是,这个北欧之都顿时灵动起来,显得格外妩媚与优雅。我记得2009年夏天,芬兰女总统访问俄罗斯,她热情而郑重地邀请那位年轻干练的梅德韦杰夫总统下次回访时,一定要畅游一下波罗的海。可见,芬兰人为紧挨着波罗的海很有几分洋洋得意与无法掩饰的自豪呢。
最方便的是在赫尔辛基的南码头看海。湛蓝的海湾里悠悠然来往着许多豪华客轮,去瑞典、爱沙尼亚、德国,每天都有航班。那海湾无疑喧闹而快活,充满了青春动感,只是在这里还不足以领略大海的淼远与苍茫。没关系,你乘坐渡轮,往东南方向,最多20分钟吧,登上芬兰极为著名的古堡要塞所在的蕞尔小岛,在那里观海就会觉得淋漓酣畅了。我有幸,独自坐在那碧玉般葱茏小岛最边缘的古炮台上,面对波罗的海,只见那沧浪之水波光万顷,盈盈乎,浩浩乎,滚滚乎,不觉感念天地宇宙之博大雄丽而无可比拟,顿时脑中竟一片空白,不知身处何时何地了!
赫尔辛基不是那种热衷于前卫时尚而失去历史沧桑感的城市,而是满目北欧古典主义的似乎貌不惊人的建筑,很淡定的那种月白色或米黄色,整体上仿佛是素装娴静的少妇。唯有两座一白一金的大教堂,各属基督教和东正教,气宇轩昂地耸峙云空,在北欧那特有的温煦如梦的阳光下熠熠闪光。是的,赫尔辛基有一种浓浓的脱俗而诗化的气息,让你感到心灵的清净、安祥与柔暖。
这里似乎一切都那么漫不经心地闲适。人口区区不到60万的赫尔辛基,街头很难有车水马龙的景象。除了上下班的时候,你所见到的人们几乎都是脚步从容和轻盈,脸上难觅一丝焦灼的阴云,一副绝对生活过得很滋润而悠然自得的模样。毕竟是举世闻名的社会保障系统最为成熟的国度,没有后顾之忧。看病上学包括读大学都不用自己掏腰包,这不必说。有的事听起来不可思议,就说军人吧,哪怕士兵,每周“上班”仅仅4天,其余时间都可以回家,其实服役期也就10个月,有的军种才6个月,这种兵当得也太舒服了,是不是也太稀拉了?加之薪金很高,难怪芬兰的青年人参军踊跃得很。还有,大街上我也偶遇乞丐,竟然衣冠楚楚,与常人几乎无异,他冷不丁地向你伸出手来,真让你吃上一惊,他们每人每月可从政府那里净领生活费800欧元!
赫尔辛基有难计其数大大小小的都很考究的咖啡馆,门前几乎都设有一排排露天茶座。在这里,男男女女手持杯盏,或自品独酌,或与好友边侃边饮,尽情享受着金灿灿的北国阳光,悠悠闲闲地观赏着变幻流动的街头风景。他们格外钟情阳光,越是门前阳光多的咖啡馆,品客越多,随着日影缓缓移动,人们也不断转换“阵地”,我竟发现,许多开始背阴的咖啡馆,门前竟很快变得座位空空,以至寥无一人!赫尔辛基人是追逐阳光的人。我实在难以想象,在冬天那漫漫“极夜”里,他们是如何度过的。
南码头农贸市场的露天咖啡座更有另一番情趣。一只只雪白的鸥鸟从空中翩翩飞下,竟大大方方地停落在桌子上,与客人几乎零距离相偕相伴,无拘无束地啄着食物的碎屑。夕阳冉冉西下,市场上的生意渐渐清淡起来,我见到不少闲下来的商贩,低着头给那些停在脚边的鸥鸟喂食。人与自然如此和谐融融相处,不由得让人心生感动。
我们住在市中心的莱迪逊饭店。这一带相当繁华,不远处有火车站、阿黛浓美术馆、邮政博物馆,靠得最近的则是赫尔辛基著名的赌场。从饭店里摆放的广告宣传材料得知,这个赌场拥有300台老虎机,30桌赌台,3家餐馆,3个酒吧,还有歌舞表演,够显赫的吧。听说赌场的生意很不错,可是,我们每晚回饭店,经过这家赌场的门口,很难见到有人进出,印象很深的,只是那乳白色的霓虹灯不事声张地静静地闪烁着。我想:赫尔辛基人一定是很低调的。恐拍只能这样解释。
正是如此。使馆的朋友告诉我们,芬兰的男人非常内向,甚至往往害羞。你如果在这里见到有的男人不是这样,他定是喝醉了酒,要不,就不是芬兰人,而是外国人。芬兰人好打猎,主要是猎鹿,喜欢到森林和湖畔独居。在芬兰,城市人口本来就不多,他们还要远离城市,他们力图使人际关系变得简单。也正因此,芬兰人很朴实诚恳,听使馆的朋友介绍,你如果在南码头露天农贸市场购物,嫌某个摊贩的东西贵,问这里有便宜的吗?他会很爽快地手指附近的另一摊铺:“那家比我便宜!”你过去一打听,果然如此。
赫尔辛基人很好客,待客由衷地真诚。实际上,所有的芬兰人无不如此,他们没有某些西欧人的那种自视不凡、人情淡薄而难以深交的情况。我们在赫尔辛基仅仅一周,亚历山大研究所作为邀请方,由德高望重、博学儒雅的基维宁所长偕同夫人三次出面宴请我们。而且,每次都特意安排在一个甚有特色,一些社会名流、文化精英经常光顾的餐馆,用很地道的芬兰美食佳酿盛情款待。
我们总是兴致盎然地听他娓娓生动地介绍芬兰的事情。他谈芬兰的历史,毗邻的瑞典、俄罗斯曾统治芬兰长达数百年,芬兰一直游走于瑞、俄之间,如今与瑞、俄仍保持非同一般的关系。特别不可思议的是,赫尔辛基的议会广场现在还高高矗立着俄国亚历山大二世的塑像。所长说,相比起来,这个皇帝口碑不错,当时能给芬兰很大的自治权,虽然俄国割去芬兰的许多土地,据说芬兰的版图原来看起来是一个高举双臂、身穿长裙的少女,可是她的右手臂和右裙角很大的一块被俄罗斯割去了。
所长还谈及芬兰的社会和经济。芬兰如今是世界上民众生活质量最高的国家。芬兰造纸业、电信设备制造业发达,“诺基亚”誉满全球。芬兰森林复盖率达75%,照说这为造纸业提供丰富无比的原料。可是芬兰人很聪明,并不开发自己的森林,却向俄罗斯进口木材,因为价格便宜。金融危机发生后,俄罗斯的木材抬价了,芬兰造纸业受到一定冲击。芬兰粮食、水果全部自给。芬兰向外国比如向沙特阿拉伯出口纯净水。
所长还纵论芬兰的文化、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以及相互文化交流。著名作家阿莱克西斯以及作品《七兄弟》是芬兰的骄傲。杰出的音乐家西贝流斯是芬兰的另一骄傲。所长毫不掩饰这些文化名人给他带来的自豪。在一个古典浪漫情调浓郁的咖啡馆里,我们诧异的是,一抬眼便看见垂挂着一排硕大的圆球形白灯笼,这与我们东方洋溢着喜悦与吉祥之气的大红灯笼何等不同!所长说:东西文化差异甚至表现在色彩的认知含义上……所长还安排我们去看孔子学院,它与研究所在同一座楼里。在孔子学院里学习的有留芬华侨的子女,更多的是纯粹的当地人。教学方法十分别致,比如办汉语沙龙,让中芬联姻的夫妇用汉语谈如何逐步克服文化差异乃至文化冲突,最后实现文化融合,很是生动有趣,效果特好。
芬兰的桑那浴向来远近驰名。家家都有桑那房,可说是大普及。这次出访,热情的主人邀我们来到一个名叫三塔哈米那的小岛上洗桑那。这小岛也位于波罗的海之中。在用圆木建成的桑那房里,主人不无自豪地手指窗外浓郁的绿树以及近在咫尺的蔚蓝色大海,说:多像一幅画呵!芬兰人有个习惯,赤身裸体地在高温的桑那房里沐浴一会儿,便跳进冷水中浸泡,再回桑那房。我们这次要跳入的当然是波罗的海。十分可惜的是,我的游泳技术很糟,未能斗胆下水,白白失去了与波罗的海亲密接触的机会,到现在我还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