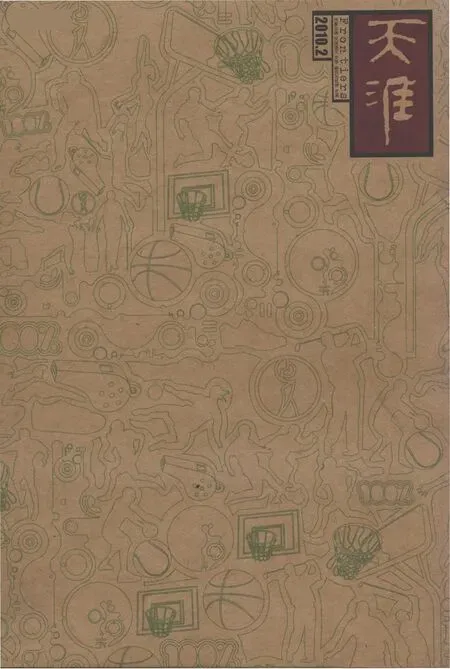与一具薄皮棺材有关的
郑小驴
与一具薄皮棺材有关的
郑小驴
如你所知,南方的冬天总是很阴冷,这也是你多年来一直不喜欢南方冬天的原因。1993年的冬天,除了寒冷,更多的还有恐惧。是的,1993年那个冬天只给我们留下了无穷的恐惧与战栗。如你后来的回忆,这个冬天给你带来的恐惧与一具白色的薄皮棺材不无关系。
1993年冬天的下午,当你小心翼翼独自一人从小学操场旁边的小石拱桥上走过时,你回了回头,看到其他的同学们穿着五颜六色的棉袄在操场上像只小皮球一样蹦蹦跳跳,他们谁也不肯理你,因为你在上课的时候被数学老师骂作是猪。数学老师揪着你的耳朵把你的目光从窗外拉回来,“蠢猪你还要不要听讲?”她就是这样骂你的。那一刻,你觉得自己就是一头猪。
1993的冬天异常寒冷,你戴着深红色的破棉帽,黄绿色的鼻涕长长地挂在你的嘴唇上,看起来就像一根红薯粉丝。你最后回头望了望远处的李小军一眼,朝他喊道:
“李小军,我们看拖拉机去!”
李小军并没有理睬你。他们正在玩一种“警察抓特务”的游戏。你的呼喊声像一滴水融入在大海中,他们刺耳的喧闹声让你感到一阵阵离奇的忌妒。他们并没有邀请你加入他们的队伍中去,甚至连“特务”的角色,你也没有当的份。他们稚嫩的声音在寒风中格外响亮:你这头猪走开些!
于是你就走了。操场外面的马路前方,正停着一辆“衡阳”牌手扶拖拉机。
你注意到这辆手扶拖拉机已经很久了。上数学课的时候,正是因为它吸引住了你的眼球,所以数学老师生气地将“蠢猪”的称号扣在了你的头上。你看到这辆拖拉机上午或者更早的时候就停在那里了,直到下午,它也没走的意思。它为什么一直停放在那里?它里面装满了什么?这一直是困扰在你脑海中的问题。所以,你决定一个人去探究一下。本来,你打算把好友罗燕霞或者罗丽也叫上同去的。她们假装没听见,蹦蹦跳跳地玩开了。
后来你回想起1993年冬天的那个下午时,记忆中只停留了一副灰暗而呆滞的画面:远眺隔着几丘田的操场,一刹那间,你看到操场上所有的之前还在蹦蹦跳跳的皮球们仿佛被刺了一针似的,全部蔫在了操场上。万物阒静。或许阒寂源于那辆拖拉机上的人。当你拖着鼻翼下那行长长的“粉丝”走到拖拉机前面时,你看到一个女人正静静地躺在拖拉机的拖斗里,一只掉了鞋子的脚突兀地伸向了你的眼前。她身下铺了厚厚的一层稻草。你惊慌地发现这个女人和你母亲一样,穿着一条灰白色的裤子。但是你惊魂不定地朝她看了一眼后,确定她并不是你的母亲。正因为不是你母亲,所以你才会害怕。当你迷乱的目光透过拖拉机的铁栏时,你看到了那个头发凌乱的女人疲倦地睁着双眼,她的额前微微地裂开了一道口子,你看到乳白色的脑汁像豆腐一样溢流在那把稻草上。稻草蓬乱地遮掩了这一切。你感到了一阵异常的寒冷,背后凉飕飕的。或许北风唤醒了你的恐惧,你战栗的声音像蘑菇云一样爆炸于南方冬天阴冷的上空。
“啊!……”
正如你后来的回忆,你的充满着战栗的呼喊便是那时传出去的。操场上的声音戛然而止,仿佛一阵夏季台风,将所有的嬉戏声刮得干干净净,你盯视着这个女人的脸,女人不知什么时候也盯上了你。你感到喉咙仿佛被什么掐住了再也发不出声音来。同时你看到雨点般的人群正涌过那座清代建造的小石拱桥,朝你奔来。所以你后来再回忆1993冬天下午时,脑海中只剩下了这灰白的单调色彩。
“怎么啦?”他们纷纷起哄道。
人群在阴暗的下午围着尸体。他们的恐惧让你为自己感到骄傲,因为你是第一个发现尸体的人。很多只装满疑惑的眼睛集聚在尸身上。是车祸!有人说。也可能是被人打死的,有人发出了这样的声音。而一个尖锐的声音透过重重的人群让每个人都惊讶不已:她好像是杨小燕的母亲!
事情的突兀超乎了你们的想象。你听到有人大声道,这不可能。
而那个声音是那么的坚定:我认识她,她就是杨小燕的母亲罗爱娇!
后来你回忆起这个场景时依旧难以抑制住内心的澎湃,你感到了一阵隐隐的害怕,你不知道自己为何会有这种疯狂的念头,你很想扑上去大声说:
“她是我的母亲!”
你时刻渴望着一刹那间被众多眼光包围时的那种幸福得颤抖的晕眩感。而事实上你的母亲活得好好的。
你略带恐慌与失望地察看着每个人的眼神,你发现他们都在盯视着这具尸体,个个看得聚精会神。于是你略带焦虑、响亮地叫了起来:
“我是头个发现这具尸体的人!”
让你感到失望的是,他们仅仅是转了下头,扫了你一眼,便马上又将眼光集注在尸体上去了。你看到数学老师顶着那个硕大无比的脑袋将身子微微往前靠,就在那时,你听到她喃喃自语地说道:
“三十都不到吧?”
杨小燕站在母亲的面前,她一声不吭地保持着缄默。她的表情无动于衷,你惊讶地看到她眸子里突然摄入了无数人群的头像。
你经常动不动就欺负杨小燕,有一次你甚至污蔑她偷了你的橡皮擦,而使张老师在课堂上狠狠地批评了她一顿。而橡皮擦实际上正藏在你的裤兜里呢。你欺负她的原因第一是她长得瘦小和丑陋,而最重要的原因则是她的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死了。
那天上午杨小燕被人从教室叫走了,她的碎花棉袄从你眼前飘扬而过,构成了那个冬天最刺眼的风景。你看到她的同桌李小军转过头来朝你说道:
“她家经常闹鬼!”
“你怎么知道的?”你问。
李小军龇牙咧嘴地笑道:“她爸还未死的时候,她家的床脚夜里经常会出现一束手电筒光!”
“她爸肯定是被鬼害死的!”他又幽幽地补了一句。
对于这个问题,你再也没有接下去聆听的勇气。作为一个女孩,天生胆小和你如影相随。所以你对李小军娇嗔道:
“讨厌!”
那年夏天,杨铁军肥胖的身体在清江被打捞上来时,你发现这个平日里胖得像尊菩萨的男人,躺在青草上,湿淋淋的再也无法动弹和呻吟,像一个巨大的标本。你想,如果有一把剪刀沿着他的肚皮剖开,弯弯曲曲的肥肠里面肯定灌满了暗绿色的河水。你有一种强烈想打开看看的欲望。
那个夏天开始,你不止一次在梦中看到了那个胖胖的男人,他手中举着一把锋利的剪刀朝你走来。他大声地说:
“杨小燕我的好闺女,快跟我走吧!”
你大声说:“我不是杨小燕,我是颜言。我不会跟你走的。”
可是你的反抗是徒劳的,那个胖子伸出的手像条巨蟒一样箍住了你的脖子,你看到他狰狞地挥舞着寒光闪闪的剪刀说,“你不认我了吗?别忘了,我死了也是你父亲!”
你无法动弹,巨蟒那么有力,他像提着一只鸭子一样将你提了起来,他充满焦虑和愤怒的喊叫在你的耳边呼啸,你拼命挣扎……一把冒着寒光的剪刀在你的脖子前一闪,你的脖子在咝咝地往里面吸着寒气,正如以前你看到宰鸭的场景一样,你的脖子被割断了……
“哈哈……”你看到胖子坐在地上喘息、狂笑不止。
这个可怕的梦境在黑夜中周而复始永无止尽。一次次你活过来,又马上死去。你最先是对李小军说的:
“杨小燕的爸爸他杀了我。”
李小军傻笑的样子如河马般难看,他马上对杨小燕说:“颜言她说昨夜梦见你爸爸杀了她。”
杨小燕瘦小的肩部耸了耸,她将语文课本翻到英雄王二小的那一章上,坐在那里像个小木雕一样一动也没有动过。
杨小燕在你面前显得如此地不堪一击。如果她是一只小小的蝼蚁,你只需举手之劳,轻轻一捏……
有一天,教室里只有你们两人,你坐在那里,眼前的这个人让你暴怒、扭曲、愤懑,于是你莫名地站了起来,指着杨小燕的鼻子说:
“我看你一眼,都觉得恶心。”
你将那个奇怪的梦告诉了母亲。当时母亲正在为一群猪仔不肯进食而绞尽脑汁,你的叙说在春暮的傍晚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她对你说,那一定是你睡觉时把心脏压着了才会做噩梦的。你将信将疑地相信了母亲的话,当然,她骗你了。
而此时已经没有谁再相信你说的话,因为第二天李小军向老师揭发了橡皮擦事件,你的老师在碰到你的母亲后,向她转述了此事。作为代价,你头回尝到了被揍的滋味,而更为难过的是,张老师从此再也不肯轻易相信你的话。她嚷着对你说道:颜言没想到你这个鬼丫头肚里装的全是坏水!
乡政府和派出所的人来的时候,已经到了放学的时候了。你看到几个大盖帽从草绿色的吉普车上跳了下来,他们很快就将人群挤开了一条缝隙,让开!让开!他们的声音果然起到了震撼的效用,每个人带着畏惧的眼光,一言不发地望着大盖帽们靠近尸体。
李小军突然冒了出来。他拽了拽你的碎花小棉袄说:
“颜言,尸体当真是你头个发现的么?”
“那当然了!”——你噘起嘴巴的声音充满了对李小军的不屑:“你不相信就算了!”
你满足地看到李小军用着一种充满崇拜与敬畏的眼光在看着你。那一刻,你发誓以后再也不屑和李小军这样的人讲话了。你变得崇高与伟大起来。
女尸事件似乎出乎了你和所有人的意料。你看到神色凝重的大盖帽们双眉间拧成了一个大大的“川”字。各种传言像黑压压的乌鸦一样在水车掠过,甚嚣尘上的莫过于罗爱娇是被奸杀的。
这种传言很快就压盖了其他的各种说法,赶集的那天,你提着一只竹篮跟着母亲的步伐走进水车的集市,你惊讶地发觉,几乎所有的妇女都在私底下议论着并不光彩的事情,她们甚至认为杨小燕的母亲可能是惹怒了某个男人的女人才有此下场。很多次你想插嘴,你想说,杨小燕的母亲是脑壳开花才死的,她是出了车祸。可是你噘起嘴巴说的话很多次都被你母亲粗暴地阻挡了回去:
“你懂什么呢,小孩,你不就看到一具尸体了吗!”
她们粗壮的嗓门在水车喧闹的集市上显得格外的富有穿透力。
作为死者的女儿,杨小燕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呢?你很想看看杨小燕,可是杨小燕和你预想中的一样,第二天她并没有前来上课,同样的,第三天也没有。然而大盖帽却来了。你首先被请到了操场上,你看到大盖帽们手中并没有拿枪,这让你有些微微的失望。
“昨天下午是你第一个看到尸体的吗?”
你怯生生地望着他们中的一个点了点头。
“你看到有谁在你之前来过吗?”他们又问,另外一个大盖帽赶紧补充了一句,“你看到拖拉机是谁开来的?”你有些恍惚地摇了摇头。
“你们怎么没带枪呢?”
大盖帽们彼此间对望了一眼,对你笑了笑说,我们只是来调查取证,不用佩枪。你又说,那不带枪,坏蛋不是跑掉了吗?
大盖帽们望了望你,一时语塞起来。这时站在你身边的班主任张老师推了你一下,说颜言你要好好配合警察叔叔们的调查知道吗?
你的脸很快便红了,用小手指很不自在地扭着碎花小棉袄的衣角儿。大盖帽们呵呵笑着对你说,不要害怕,你昨天下午看到了什么就和我们讲。你心想,大盖帽们比起你的班主任张老师要亲切和蔼多了。你总是觉得陌生的才是可亲的,而生活在你身边的人却是那么的讨厌。于是你说,我不知道拖拉机是什么时候停在那里的,我走神瞥一眼窗外,就发现它已经在那里了。大盖帽问,难道拖拉机没有声响吗?对于这个问题,你心里暗暗地责怪自己昨天怎么那么粗心,竟然没有听见它的声响,而你的班主任张老师她也表示,一点声响都没有听到。你看到大盖帽们略感失望的样子让你内心有些过意不去。你偷偷地发现,其中一个年轻的大盖帽穿着制服特显英俊,你不禁多看了他几眼,你内心怦怦直跳不已。
他们还问了一些什么?你的心思已经不在这上面了。最后他们要走了,你看到那个年轻的大盖帽在上车的时候将警帽摘了下来,一躬身钻入了吉普车内。你对班主任说:
“他们还会再来吗?”班主任显然对你刚才的表现不满意,瞪了你一眼说:“你这颠三倒四的回答,他们肯定还会来!”
你竟然心里有些暗暗的窃喜。
更为恐惧的传言在你耳边回响,那具女尸,她的头颅被破裂以后,脑浆却被人偷偷挖走了。足足有一杯子脑浆,像豆腐脑一样,被人用小勺子挖走了。这个传言让你战栗,在1993冬日的下午,你发现自己的腿像抽筋一样颤抖个不停。或许班主任欲盖弥彰的说法让你开始对这个流言将信将疑起来,张老师说,大盖帽正在追查女尸身上的一些线索。你伏在课桌上,一动也不动地盯着张老师,你发现她黑亮的瞳孔在某一瞬间像花火一样发出一种不可言状的惊悚与恐惧感来。你诧异地想,难道张老师也害怕这件事吗?
正如张老师所说的那样,大盖帽们很快又来到了学校。张老师叮嘱你先待在教室里别出来,你有些委屈地望着她扭着肥大的屁股走出了教室门口和大盖帽们谈话。而教室里很快就乱哄哄的,你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成为了班上的英雄,你的一言一动都引发着同学们激烈的争论,他们都把你当成了顶礼膜拜的偶像。班主任张老师马上返回来了,她说:
“颜言,你出来一下。”
“死者你认识吗?”大盖帽问。你很快点了点头。你发现之前的那个大盖帽这次没来。大盖帽们又说:“死者就是你们班同学的母亲,你看才这么大就失去了母亲该多难过啊。”你望了眼说话的大盖帽没有说话,你寻思他究竟想向你说什么。于是你小心翼翼地说:“她是车祸死的吗?”
大盖帽们望着你摇了摇头说:“现在还不好说,要等法医验完尸体后才有结论。”你不知道验尸究竟做什么。大盖帽们又说:“你上课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有人在拖拉机附近活动?”
你仔细地回想了一下,上课的那个冬日下着蒙蒙细雨,外面的田野显得有些灰暗,在你搜索中的回忆里,并没有出现其他人的影子,于是你说,除了那辆停在那里的拖拉机,什么也没有。大盖帽们最后又问道,你能确定在你看到拖拉机之前,它一直没人靠近过吗?
你肯定地点了点头,因为那节数学课你的注意力并不在黑板,而是集注在了那辆衡阳牌拖拉机上,于是你说,在我发现拖拉机停放在那里的时候起,它一直没人靠近过。而大盖帽们问起其他的同学,他们的回答却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你对这些回答充满了不屑,因为你敢确定,那堂课上,没谁有你那样对那辆拖拉机那样关注过。你甚至推想,那辆拖拉机可能更早就停在那里了。静止的或者已经存在的事物总是让人们疏忽,你为自己的这种想法暗暗激动不已。但是那个年轻的大盖帽没来,你忍住了不想对他们说。
事情很快就出现了转机。一个叫罗晓亮的麻溪男人在上午匆匆赶来,他对大盖帽们边递烟边说,这辆拖拉机是他的。
“拖拉机是昨晚停在这里的,不知坏哪了,怎么也摇不起来,所以只好把它暂时停这里了。”罗晓亮怕大盖帽们不信,于是从座垫下的工具箱里掏出铁棒,朝拖拉机头使劲地摇了起来,机头被他摇得像头发疯似的牛,但是依旧没有突突响。大盖帽们问他:“那事你都知道了吗?”
罗晓亮使劲地点了点头说:“知道了,所以我天未亮就从石门赶过来了,不知是哪个天杀的在我车上做这缺德的事。”
大盖帽们又说:“你来水车做什么?”罗晓亮说:“去替我姨妹拉一车木材去枫树。”
“你认识那个死者吗?”
罗晓亮摇了摇头说:“不认识,水车我不认识几个人。”大盖帽挥了挥手,说:“你跟我们回派出所走一趟吧。”
罗晓亮想了想说:“要得!”
你看到罗晓亮走的时候,将衣领高高地竖了起来,像是冷极了。你望着大盖帽们的破吉普在弯弯曲曲的乡村小路上渐渐消失于冬天灰暗色的视野里。不知道为什么,你略感到有些惆怅。
下午的时候,另外一种流言开始在水车流传起来。当你听到这是一桩谋杀案时,心里咯噔了一下。在你后来放学回家的路上,脑海中一直在想着杨小燕这两天在做什么。而奇怪的是,自从她母亲罗爱娇死后,那个噩梦再也没有出现过。你很想把这件事和母亲说,但是最后又忍住了。你同时还发现,几乎每一天你都有那样的体验,你脑海中飞速晃动的某个场景的片断刚好在你眼前的景物中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吻合,就好像很久之前某一瞬间发生过的事情在此刻又得到了重放。可是这些都是你之前无法用语言所表达的,而且你也不敢将这种体会说出来。在回家的那条小路上,你莫名地害怕起来,呈现在你面前的是冬日昏暗的景象。你想,或许杨小燕的母亲在另外一个世界会过得很好,或许她还会与他的胖男人再次相会。你又想,杨小燕此刻是不是在哭,她哭的样子难看吗?
接着你想象自己的母亲去世后的场景。
所有人都一致认为这是一起有预谋的谋杀案。当水车的人们纷纷向你询问死者的脑浆是不是被掏空时,你开始语无伦次起来。你惊恐地发现,那么多眼睛集体冒出的饥渴之光像群饿疯了的老鼠一样可怕,她们像是商量好了,要把你吃掉一般,一动也不动地盯视着你,生怕你跑了。
扛不过,你只好说:“我并没有看见,尸体已经被大盖帽们抬走了。等法医验完尸体后的结论吧。”你这样模仿着大人们的语气,打发掉他们。
母亲在那群长舌婆走后却对你异常地热情起来,她不仅给你打了荷包蛋,而且连喂猪这项让你十足讨厌的活计也表示不用干了。她朝你有些不好意思地问道:
“你把真实情况和我说说好吗?你当时看到的女尸是不是被人剥掉了裤子?唉,她们都这样说的。”
你喝了口汤皱皱眉说道:“我看到她穿着一条和你一样的灰白色长裤。”你发现母亲的脸色马上变得和天色一样难看。她说:“她怎么和我穿同样的裤子呢,你一定是看走眼了。”她又问:“你看到她的头颅开了吗?”
你的心像被刺了一下,站起来,一言不发地走出了门外。母亲的呼喊声在你身后拔地而起,她大声地问你要去哪里?
你怔了怔,没有接她的话,其实你也不知道要去哪里。你很想出去走走。
当你回家的时候,你发现家里多了一个女人。那是一个你从不认识的女人,她头上围着一块红蓝相间的围巾。你进屋的时候,她赶忙站了起来,朝你打着招呼,夸你长得很漂亮。你有些茫然地望着这个陌生的女人。你母亲说:“这是葛阿姨,罗晓亮叔叔的妻子。”你还是很茫然地立在那里。葛阿姨一个劲地夸你漂亮和端庄,你逐渐听得有些心花怒放。你觉得这些话如果每个人都这样说,该是件多么美妙的事情!最后葛阿姨换了一种语气和你说话,像是在叮嘱你:
“要是大盖帽们再问你罗晓亮叔叔的事情,你就说全部都不知道,懂吗?”
你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你后来想,为什么会那么轻易地就范呢?难道是被刚才那席话迷惑了?可是你又想,罗晓亮的事情她的确是一无所知的。
你看到葛阿姨临走的时候,母亲和她聊得那么愉快,就像两个久违的亲姐妹一样难舍难分。不经意,才发现桌子上摆着一袋子水果。
罗晓亮很快就被放了出来。因为法医的验尸结论出来了,死者罗爱娇是因为突发性心肌梗塞而死亡的。这个结论让水车很多长舌婆失望不已。但是死者的脑浆不翼而飞的事情依旧没有侦破出来,有人甚至这样绘声绘色地描述着:就像用勺子挖西瓜,整个头颅里的脑浆被掏得干干净净。
这种描述让所有的水车人毛骨悚然,就如你母亲所说的,既然死者是死于心脏病那干嘛脑浆还被人挖走呢?
回来的罗晓亮哭丧着脸说,他娘的,那个天杀的肯定不得好死,害得我差点背上了黑锅回不来了。而罗晓亮的婆娘在她老公回来以后,之前的那种哀怨的语调立马像雨水冲刷一般。你颇为诧异地听到这个鼻翼右侧长着一粒黄豆粗的黑痣的女人瓮声瓮气地在水车向每个朝她身边走过的妇人倾诉,“我家罗晓亮从不干这种缺德的事情!他连只鸡都不敢杀的!”
你看到前几天还在背地里就罗晓亮被抓的事议论半天的妇人无一不改变了脸色,她们朝黑痣女人纷纷表示,“我就说嘛,罗晓亮是老实人,老实人怎么会干这样的事呢!”
案件并没有像想象中的那样顺利侦破出来。连日来的冬雨没完没了起来,松针上白茫茫的一片,寒风肆意的天气里每个人都缩着脖子在肮脏的泥水路中小心行走。就在你看到那辆拖拉机的第三天早上,你看到了那具白色的薄皮棺材。
当时你正从家里往学校赶的路上,在那座荒凉的茶山小径,你怵然发现一具窄小的阴森可怕的白薄皮棺材出现在你眼前,当时你正低头爬上一个山坡,并没有将眼光伸向前方,所以直到你离它很近时,才猛然发现它的存在。四周一个人也没有,抬棺的人都已经回去吃饭了,入土要等到中午的吉利时辰才能进行,所以你毫无准备地遭遇到了这场可怕的经历。你呀了一声,这具白色的薄皮棺材像是长了眼睛一样监视着你,你透过薄薄的棺木,似乎看到了那个失去了脑浆的破头颅,那血淋淋的天灵盖就像一个打破了的葫芦,里面空空荡荡。呈现在你四周的是万物无声的恐惧,你感觉到自己的心在某一瞬间也像水中的葫芦一样漂了起来,你恍惚间又察觉到自己的毛发在那个冬天的早晨全部齐刷刷地竖立了起来。冷汗湿透了你的后背,你不敢回头,因为她们都说,回头的一瞬间,一条猩红色长舌会像蛇一样飚到你的眼前。你就呆立在那里,像张照片永远地定格在了1993年冬天的那个早晨。你嗅到四周全部充满了死亡与阴森透骨的气息。你在那一刻,嘴里开始不由自主地动了起来:
“你不是我害死的,你不要来缠我。”
你尽量模仿着大人们的语气给自己壮胆。可是你很快就发现自己失败了,你稚嫩的口音让你的信心瞬间瓦解。你泪眼婆娑地望着眼前的这具白色薄皮棺木,她们都说,只有死后不能升天的人才会睡白色的薄皮棺材。
你看到自己躺在白色的薄皮棺木里,你的母亲正在哭泣。你颓然地昏倒在这具让你无法逾越的白色薄皮棺材面前。
是唢呐和响铳的声音把你惊醒的。他们惊讶地发现你躺在薄皮棺材前,于是把你弄醒,他们一直认为这不是一个好兆头,棺材里的人已经化为厉鬼缠住了你的灵魂,你的命危在旦夕。他们都这样叹息道。你茫然地望着这些投射过来的目光,惊讶于自己并没有哭出来,而是一步一步朝学校走去。或许1993年冬天的那个早晨就像那个胖男人一样在你以后的梦境中重复光临着。它们像抚摸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抚着你,每当夜里你头痛欲裂,脑髓里像是有一根细长的针在来回挑拨之时,这个从未改变的幻象立刻便呈现在了你面前:这是场血淋淋的充满着暴力与残忍的宰割。它们面带着残酷的微笑,生冷的面孔上散发着一层毛茸茸的寒光。每次梦到这个场景,你总是会感冒好几天,病得死去活来。
杨小燕在母亲入土后,终于来上学了。这是你最关心的事情。你看到杨小燕将脑后的两条小辫子剪掉了,她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在你面前,显得格外的陌生。你甚至隐隐地感觉到了这股陌生的气息所带来的威严感。是的,是威严感。你发现李小军再也不敢随便拿杨小燕开涮了,他用充满着畏惧与生疏的语气小心翼翼地与杨小燕企图重新搭建一条友谊的桥梁。但是很快李小军像只漏了气的皮球瘪在坐凳上手足无措。杨小燕用胳膊朝李小军甩了甩:
“滚开!”
杨小燕在死了母亲之后,她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她开始用一些看似冷漠的举止来捍卫着这难得的权威。在漫长的一段时间里,她就像一个公主一样,说一不二,连班主任张老师也不敢说她。她掉了一支笔在桌下,马上对李小军命令道:“给我捡起来。”
李小军朝她打量了一眼,乖乖地就范了。她如法炮制,班上平时最嚣张的陈辉也拿她没办法,眼睁睁地看着她的指甲落在自己的脸颊上。
班主任张老师背着她对你们说:“你们最好别惹她,你们惹不起她。”
杨小燕变得越加肆无忌惮起来,她不屑于理睬任何人。你怯生生地背地里注视着她,有一天你吃惊地发现她竟然在本子上写着张老师的坏话。她发现了你,轻蔑地扫视了你一眼说:“你去揭发吧,真恶心你。”
你愣在那里。在张老师办公室,张老师说我知道了,胡乱把你打发了出去。这让你同样忐忑不安。
那些日子,随着冬天寒冷气流的日渐加重,你发现杨小燕开始有些不安起来。她几乎每天都在刻意地闹出一些事情来,仿佛在故意挑衅班主任张老师的耐心。有人发现她将讲台上的整盒粉笔偷偷地带回了家。没有人再敢理睬她,她就像一只被遗忘了的玩具躲在黑暗的角落里忍耐着孤寂的煎熬。有天你听人说,杨小燕常常跑到她母亲的坟场枯坐发呆。
那个年轻英俊的大盖帽在1993年冬天里再次与你相逢,当时他正和罗晓亮喝酒。他们喝得两眼发红,似乎成了一对孪生兄弟。
“她是谁呀?”他朝罗晓亮说道。
“一黄毛丫头。”罗晓亮哈哈大笑,接着喝了一口酒。他望了你一眼,生疏得可以将你从他记忆中删除。你确定他已经不认得你了,一种莫大的悲哀从你的心底腾起。你望着他喝得醉醺醺拎着一包东西回家,从罗晓亮的眼神里,你不安地察觉到了某种不可告人的秘密。
在1993年冬天一个最寒冷的天气里,水车的人们将愤怒的目光开始集注在了国癫子身上。这个因为早年做建筑活计从高处摔下来坏了脑子的男人在刺骨的天气中穿着厚厚的肮脏不堪的棉衣却光着一双脚从水车晃悠到石门,沿路撒播着这样让人毛骨悚然的疯话:是他亲手敲开了罗爱娇的头颅,他把头颅里的脑浆一点不剩地用一把稻草烤熟吃掉了。
“我的脑子坏了,吃了她的脑浆就会好啦!”他流着长长的鼻涕在寒风中像背诵一样,虔诚地向每个沿途路过的人撒播着这席话。
国癫子死于这年的一户人家的喜宴上,靠乞讨为生的他那天吃掉了整整三大海碗肥腻腻的东坡肉,被活活撑死了。而两年后又一个冬天里,罗晓亮在喝醉酒后,却说出了一种让人更加瞠目结舌的话,他语无伦次地说,他拿着那碗脑浆去给他姐姐治麻风病了。人的脑浆据说可以治疗好麻风病的。而那个麻风病女人最终因淋巴溃烂,早在一年前就死在了一间四处漏风的木板房中。她被一把稻草烧了个干干净净。
郑小驴,作家,现居长沙。主要著作有小说集《1921年的童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