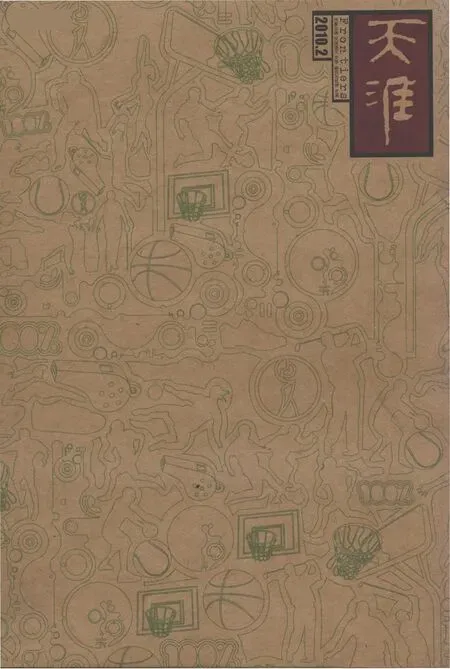离亲泪
杨瑞霞
离亲泪
杨瑞霞
2007年的今天,也是一个这么阴冷的日子。父亲在老家县医院内科病房去世。享年八十岁。
大雪与冬至两个节气之间的日子,阴气盛极,阳气衰微。今年的这几天我开车出去,在县城和乡村又都看到了正在办丧事的人家。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去世前的那次住院,是他一生里的第二次住院。第一次是两年前,因为脑梗塞,在县医院住了五天院。出院第二天,他早晨自己起床,洗了脸,刮了胡子,出了屋门去拉开了院门的插销。我在他身后跟随着他,用数码相机拍了一张他向门外张望的背影,然后,他回到屋里,见我拿着相机,他整了整衣领,面对着我,我又给他拍了一张半身像。父亲总是郑重地对待每次照相。后来就是这张照片做了父亲的遗像。这一点,当时我和父亲都没有想到。
在我印象里,第一次看见父亲输液,是在十四年前,那年他六十六岁。那也让我第一次意识到父亲竟然也会生病,关于这一点,小父亲一岁的我妈不这么认为,她说他这一辈子从没断了那些粘乎病,比如说,他有从我奶奶那儿遗传来的高血压,高压时常超过180;他中年时还腿疼过好几年,还有他常年爱犯“胃溃疡”。父亲身高一米八七,瘦高,医书上说,这是典型的胃溃疡体征。
去年的八月份,天气最热的时候父亲摔断了脚踝。后来,父亲去世后,我从一本书上看到,像他那样高龄的人若是摔掉了腿,一般情形下是过不去半年的。果然,父亲是在四个半月后走的。只是当时我不知道,那其实是一道神的预言,提醒着我与父亲即将到来的分离。
父亲摔伤后,家里的保姆给大哥打了电话,大哥和几个朋友从县城过来,把父亲搬上车,到镇医院拍了片,然后打上了石膏。等我赶回去,父亲指着打了石膏的腿给我看,一脸无辜、委屈而又茫然不解的神情。
我妈告诉我说,我父亲腿上的石膏要四十多天才能剥掉,她担心到时候他就再也下不了床,走不了路了。我妈脑中风已经十多年,偏瘫了十多年,每天在床头坐着。但这不妨碍她在家里的每件事上都有自己的主张,而且一定要把自己的主张坚持到底。她说,她已经打听好了,在离我们那个镇子六七十里的地方,有一家人有祖传的专治跌打损伤的绝技,骨折的人敷上他家的药二十四小时就能下地走路。她一定要我去买那个药,给我父亲用。
为了满足我妈的心愿,我开车去了那个诊所,买回了药,很沉的一坨,很浓的鲜姜和香油的味道,还有一些丝丝缕缕的东西。药买了,可是要砸了父亲腿上的石膏才能敷,谁能保证取下石膏父亲的腿不乱动,断骨不错位呢,大哥说:“胡闹!”我妈也不再说什么,最后我把花四百元钱买来的药给扔了。
那次断腿后,父亲的身体状态每况愈下,其实在此之前那几年,由于小脑蒌缩,他已有老年痴呆的症状,也不怎么会说话了,但他依然能记着那些他以为很重要的事情。每年的腊月二十三,他要一个人走到集市上,买一包祭灶的糖瓜和一块钱一挂的那种最小的小鞭炮,留着过年时给我儿子大卫,这个习惯他从大卫出生时开始,一直沿续到前年,大卫已经是个身高一米八二的大学生了。如果他还能活下去,我相信,他还会每年给外孙买糖瓜和小鞭炮,哪怕他的外孙已娶妻生子。
父亲还会很细心地把木头劈成木柈,把大哥买来的大块煤砸成小块,他把炉子里的火烧得很匀很透,在上午十点就熬上中午喝的大米粥。他把他的百灵鸟也喂得很欢实,在鸟笼里跳上跳下地叫。
在那个已经有些破败的,建于五十年代的老铁路家属院里,像我这样的孩子们一茬茬大了,像鸟一样飞走了。和父亲一辈的人们,有的去世了,有的跟孩子搬走了。而父亲和母亲一直留在那儿,过着他们过了一辈子的环保生活。年龄越大越像两棵无法移植的老树。在我看来,父亲是离了那儿的地气无法存活,而我妈是担心离开了那儿便再也过不了她自己想过的日子。于是他们几乎成了那里的“最后的守望者”。
四十天以后,父亲腿上的石膏被剥掉,骨折的地方长好了,只是脚踝有一些歪。正像我妈预言的那样,就是从那会儿起,他再也下不了床,走不了路了。不但这样,他的大脑也似乎完全进入了混沌状态。我回家时,我妈问父亲,你认识她吗?这是谁啊?父亲的眼睛像婴儿的眼睛一样专注而茫然的久久地看着我的脸,然后点点头,那是一种惯性的客套。父亲对每一个走进家门来看他的人都以这样的方式表示他的感谢,唯独对前来给他输液的镇医院的吴医生表现出极大的愤怒,每当吴医生一进门,父亲便瞪起眼睛,端起他的大手,做准备打人状,以此吓唬吴医生,让她快点离开,否则他就不客气了。
在此之前,父亲的生活还可以自理。这时已完全需要照顾,喂水喂药喂饭。保姆当着我们的面给他换成人纸尿裤,他也像个刚出生的婴儿一样随人摆布。这在以前是绝对不被他允许的,他一辈子是个特别在意自己的人,在女儿面前会避讳很多的事情。这时,他的老与病,他的痴呆,已经让他保护不了自己的隐私了。
那时的父亲大部分时间是处于一种无知无觉的状态里。在陪他的有限的时间里,我一直希望他能真正的明白过来,哪怕只有一会儿,以他父亲的身份给我一些表示,虽然他一辈子都不善于语言表达,而且早已经说不了话了,但我还是希望他用眼神或者手势给我一个明示或者嘱咐,给我一个只有我和他的父女之间的交流。
没有。
即使在他神智稍好一点的时候,他依然不认识他的儿女,似乎他也不关心你是谁,他只是在急切地寻找一件东西,用手比划着一个长方形的东西,啊啊的,用眼神问你,哪去了?它在哪儿?没人知道他要找什么,他便焦急地用手拍他的大腿。咳——
让人无限郁闷。
我多想知道,父亲,在他的一生中到底曾经丢失了什么重要的东西,以至于让他在垂暮之年,用仅存的一点意识,如此执着地苦苦地寻找。
夏天的一个晚上,七点多,我和保姆把父亲和我妈都收拾好,他们在那张大床上,一个在东头,一个在西头,睡着了。两人中间隔着一堆小褥子旧被单之类的零碎东西。保姆回自己家了,我一个人拿一个小板凳在院子里坐着。窗前的石榴树死了,它是大哥二十来岁时栽的,已经三十多年了,今年春天没有发芽。我记得,在那棵石榴树的下面曾经有过一个鱼缸,是个大瓦盆,里面有父亲养的七条大金鱼,墨龙睛,红顶虎头,似乎它们还在游,鱼缸的下面是我妈种的绣球花,而那时他们还年轻……
我很无望地坐在那儿,屋里是两个残败、孱弱的生命,这般无奈而无力的人生晚景,让我的心里充满哀伤和悲凉。一个念头浮现出来,父亲,与其这样活着,或许倒不如早一点解脱得好。而这个念头又是那么让我害怕,泪水一滴滴地流了下来。
其实我们都知道,生老病死是人生的一个必然过程,这样的事在这个世界上每天每时都在发生着,我们觉得自己已经可以坦然面对,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事到临头,我们依然很难相信自己的父母会离开,从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天起,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是有他们的,怎么会没有了呢?那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无论我们觉得自己做好了怎样充分的思想准备,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还是会觉得突然。
冬天来了。
立冬后的某一天,晚上我接到家里保姆的电话,她说,父亲从早晨开始昏睡,整整一天不吃不喝,怎么也叫不醒。
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未大亮,我从车库里把车倒出来,打开车的大灯,开始往家的方向开。城市的路灯还在亮着,有雾,但不是很大,出城不久,雾越来越浓,车窗外一片迷蒙,雾气像乳汁一样流动着包围着车子,什么也看不见。我小心地慢慢地开出几十里路。妹妹打来电话,说她已坐火车从北京赶回来,半夜到家,把带来的一颗安宫牛黄丸用温水化了,一点点给父亲喂了下去。喂完后,天也快亮了,父亲睁开眼睛了。她说,今天有大雾,姐你别开车过来了。我停下了车,车前和车后是一样的大雾。我已经回不去了。
幸亏那几年那条路跑得很熟了。
中午到了家,父亲的状态和平时差不多,眼睛睁开了,但只是斜着往窗户那边有光亮的方向看。镇医院的医生给输上了治脑梗的药。我们给保姆多加了一份工资,让她丈夫也过来帮忙。父亲虽然瘦,但身材太高大,骨架沉,每次翻身、擦洗、换纸尿裤,都得二三个人才挪得动。
第二天下午,我有事要回去,保姆给父亲身后堆上被子,扶他倚着坐一会儿,我和他告别,他没有任何反应,我举了下手里的包,说,爸,我走了,过两天再回来看你。父亲像被突然惊醒的婴孩,点了下头,还抬了下手,脸上还好像有一丝谦卑的不好意思的表情。
很快,时令过了冬至,父亲陷入了最后一次长达十一天的昏睡,再也没有醒过来。
我和二哥、妹妹都从外地赶回了家。我们聚集在那两间平房里。父亲睡在里屋的大床上,还像平常一样,他个子太高,而床的长度不够,于是在床边加一把椅子,椅子上放两个枕头。他已经这样睡了一辈子。
如果我们不去探究什么,如果我们愿意有意去逃避即将发生的不幸,父亲的昏迷,其实在我们看来,更像是一场酣睡。那持久、有力而匀称的鼾声。是我们从小就听惯了的,不但熟悉,还带给我们安全感。
在我们儿时的记忆里,在很多很多年里,在那些无数的白天和黑夜里,父亲经常是这样的酣睡,因为他在铁路上三班倒,搬道岔,一班十二个小时,不能有丝毫的懈怠,所以他上夜班前要睡足觉,下了夜班要补觉。作为铁路职工子弟,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父亲在睡觉,不能打扰。六七岁时我们就已经会拎着饭盒去给父亲送饭。长大后我曾问过父亲,嗜睡的他,是怎样在那间小扳道房里熬过那些漫漫长夜的?父亲说,困了,就用手拧自己大腿。三十年的扳道生涯,没出过一次差错,更不用说事故,这是父亲一生的自豪,而同时睡觉也成了他一生中最幸福的事。
父亲已经酣睡了四天,鼾声依然长而有力。到家后第一天,我让老家的朋友帮忙请来了县医院的脑系科主任,刘医生看过,说病人这是又一次大面积脑梗塞,接下来就会发生水肿,会出现脑疝和并发症,在家用些药维持着吧,不用送医院了,别折腾老人了。
此时,我们能做的只有等待,但那一刻又似乎永远都不可能到来。在家的第四天晚上,二哥给我们做了手擀面,用白菜和猪肉打卤,很快家里弥漫着往日熟悉的味道,仿佛一切又回到了从前,某一天,妈妈做好了饭,我们放学回来,父亲也睡醒了,全家人一起吃饭……
第五天,父亲依然在睡,鼾声的力度没有丝毫的减弱,这来自于他依然有力的心脏,而大脑却已经被堵得乱七八糟了。但他的鼾声和睡相,总给我们一种错觉,仿佛他随时会醒来,于是我们陷入不安,会不会是我们没有尽力,如果把父亲送去抢救,是否会有奇迹出现。假如有些事情我们该做而没有去做,日后会不会因为懊悔而无法放下?
而我最不能面对的还有我妈那几乎是带有乞求的眼神,虽然看到孩子们都很辛苦,她不再自作主张,但每一分每一秒,她似乎都在问:“送医院吧,把你爸送医院啊?”我不能告诉她,我是多么不愿意让父亲在外面去世,而不是死在他最留恋的家里;我又不能告诉她,一旦父亲出了这个房门,她将再也见不到他了。我说,妈,我爸一辈子最听你的话,你让他起来吧,别睡了……我妈说,他是一辈子听我的话,可这回不听了。我说,妈,医生说了,我爸就算抢救过来,也是植物人了。我妈说,抢救过来你们就给我拉回家来,我用饼干蘸着水喂他……
“送爸爸去医院吧!”我说。
120来了,邻居们过来帮忙。父亲被担架抬出家门。妹妹和二哥跟着上了救护车。我开车跟在后面,车上坐着妹妹的儿子,我的小外甥,他从小是跟着姥爷姥姥长大的。家里只剩下了我妈和保姆。
县医院这些年没有多大变化。从前边的门诊楼到后面的住院部,还是要通过那条狭长阴暗、地面高低不平的走廊。十几年前我妈脑出血住院时,我曾走过很多次,后来它还曾几次在我的恶梦中出现过。这一次又走进它,感觉它像某个电影中的情景,类似于两段剧情之间的铺垫,让你从生活的正面过渡到背面,从人生的一种常态走向另一种非常态。
经过一番忙乱,父亲的CT检查结果出来了,和之前刘医生的判断一样,父亲这次是大面积脑梗,而且是在脑主干部位。我去交了押金,主治医生给开了很多药,有治疗的也有营养的,整整一天都在不停地输液。晚上我和二哥留下来守护父亲。
县医院的住院部人满为患,只有八人间的大病房还有张床。1床是个八十五岁的心脏病患者,老头以平均每半个小时一次的频率不停地折腾着他六十多岁的儿子,一会儿“尿尿——”一会儿“不尿——”。6床是个刚患上脑栓塞的七十岁老太太,一只胳膊不能动,半夜里她想把溜下去的被子重新盖到身上,却发现自己无论如何也做不到,便大声咒骂她睡得死死的孙子,我过去帮她把被子盖好。
夜深了,白天像集市一样的住院部安静了许多。好人病人都要睡觉。日光灯整夜地亮着,空气很混浊。有人在梦里呻吟,还有大约四个人在高低起伏地打着鼾,其中父亲的声音最大最有力。
在此之前我的那些寻常日子里,我是不会去想有些人的有些夜晚是这样度过的。这会儿我才知道以前我那些平淡安详、心无挂碍的夜晚是多么值得感激。
下午有病人出院了,父亲的病床旁有了张空床,我和二哥分别侧身躺在床的一边,都无法入睡。夜里二点多,我去外面停车场找到我的车,从后备箱里拿出一瓶老白干,然后敲开小卖部的门,买了火腿肠和咸鸭蛋,和二哥用水杯喝了些白酒。二哥喝了酒,睡着了。我依然没有一点困意。一边照看父亲,一边看索甲仁波切著的那本《西藏生死书》,我想了解一些关于生命的生与死的真相。书上说,我们可以把人的整个存在分成四个实相:此生、临终和死亡、死后、再生。而“中阴”是指:“一个情境的完成”和“另一个情境的开始”两者之间的“过渡”与“间隔”,我想知道父亲此刻正行走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我该怎样去帮助他,书上还说,接近死亡,可以带来真正的觉醒和生命观的改变。那么我又该怎样去面对这生命中必然要发生的事情,并获得心灵上的解脱……在那个夜晚,我才知道关于生命的真相,我和很多人一样,有太多的不了解,并且缺少准备,所以当生命中的完美之相被打破,残缺即将来临时,才会有那么深的困惑和无奈。
父亲住院的第三天,昏睡的状态没有改变。医生的用药量每天都在递减。由于长时间仰卧,又一直在输液、吸氧、导尿,不太方便帮他翻身,父亲的后背出现了褥疮,垫上了胶圈,每隔几个小时胶圈上缠的纱布便被血水浸透。每次换纱布,对我都是一场折磨。
父亲住院时,大哥正在天津看病。接到电话,从天津赶了回来。那几天他每天在自己家喝酒,喝醉了便疯了似的闹腾。他认为这些年他对父母的付出比弟妹多,这让他心里很不平衡。他还对我二哥很不满,因为二哥的儿子在日本读书,经济压力大,曾说过不想按照旧习俗来操办父亲的后事。另外,他还认为这些年我妈偏向小妹妹,对他很不公平。
大哥当过二十多年的厂长,平常经常自誉是个厚道人。他的一反常态让很多人不理解,但我想,这或许是他渲泄内心脆弱与痛苦的一种方式,毕竟他身为长子,面临父亲的现状,他的压力比弟妹要大得多。为此,我和大哥之间有过一次谈话。我说,这些年我们一直以为妈妈是我们这个家的绝对中心,可现在我却明白了,原来爸爸才是我们这个家的根基,现在看来,虽然爸爸这口气还在,但他的灵魂已经走了,震不住这个家了,所以我们家才会出现这些是非纷扰。是不是别人家这时候也会生出这类家务事儿呢?大哥想了想,说,嗯——
第五天晚上。妹妹和大哥的朋友守着父亲。大哥在家炖了鸡,让我和二哥过去吃饭。那天晚上,我们喝了些酒,说了不少话。大哥二哥说起小时候的很多事,由于我比他们小十多岁,有些事情我并不知道。他们说我在《一只羊其实怎样》中写过的我家那只特立独行的羊,其实还有很多桀骜不驯的壮举,而我只不过写出了很少的一部分。大哥说,小时候他还喂过一只安哥拉兔,长到十四斤。二哥说,父亲在解放前为了不被抓去当伪军,只身从天津逃出来,步行几百里走夜道回老家,在捷地附近遇到了狼,父亲蹲在一堆碎砖上,手握砖头,无论那只狼从哪个方向扑上来他都能有效防御,那晚父亲一直与狼对峙到天亮。
我则想起,我上学用的第一个铅笔盒,是父亲给我用木头做的,很精致,盒盖可以抽拉。父亲还为大哥的女儿做过一个木马,马腿上装着四个小铁钴辘,可以拉着跑。而二哥讲的父亲的那段只身斗狼的经历,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让我想到,这些年一直以为父亲是一个平常、平凡到平庸的人,原来他也有着自己的生命传奇。想想也是,父亲曾经在那么贫穷的岁月里长大,竟然能长成一米八七的大个儿,这本身就是个奇迹。他一生经历过战乱、饥饿、忧患,用诚实的劳动养大了四个孩子,自己活到八十岁高龄,这无论如何不是件简单的事情。他灵巧的双手,他的知足、沉默、谨慎、安于天命,谁说不是一种生活的智慧呢?
那天晚上,我们一直说到后半夜。直到二哥在沙发上不住的打盹,五十六岁的大哥搂着五十三岁的二哥说,老二,去睡一会儿吧。
那时我已经几天没怎么睡觉了,天快明时,我在大哥家做了个梦,梦中,我像往常一样回去看望父母,却找不到家了,眼前只有一片残砖断瓦……醒来,我怔怔地想这个梦,一定是父亲要走了。父亲没了便意味着家没有了。
早晨,我们来到医院。妹妹说,父亲昨晚发高烧了,打了退烧针,一会儿输液时,还得再加些退烧的药。妹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从小一直对父母很依赖,这些年也是她和父母一起生活的时间最长。从住院的那天起,她就一直盼望着父亲能醒过来。这一晚,妹妹很仔细地把父亲的脸和手擦洗得格外干净。父亲脸上的皱纹很少,他虽然劳作一生,但皮肤天生细腻有光泽,这一点我们兄妹都得益于他的遗传。
我看着父亲。此刻父亲恍若一条被风浪推到岸上的大鱼,张着嘴,吃力地呼吸着,鼾声的力度已明显减弱了。他上颚的皮肤由于长时间被肺里呼出的热气熏蒸,已经开始腐烂、脱落。我想,父亲的最后时刻来了。
我握着父亲的手。我说,爸爸,你现在一定很难受很难受吧,爸爸,我们都盼着你能好起来,回家,喂鸟,劈柴,和我妈做伴过日子……我说,爸爸,你要是真的不行了,也别有太多的牵挂,放心地走吧。我们会照顾好妈妈,会好好地过日子。我说,爸爸,你一辈子为人清白,勤劳,忠诚,你在睡梦中离开这个世界,是终得善果,是你的福报。我说,爸爸,你走的时候,会有神灵指引你,去西天极乐世界,过安详喜乐的生活,你跟着他的光明向前走,不要回头……
当我说完了这些,我看到父亲的眼角涌出来了一滴眼泪,缓缓地,顺着脸颊淌了下来。
几分钟后,父亲停止了呼吸,安静地离去。
杨瑞霞,作家,现居石家庄。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枯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