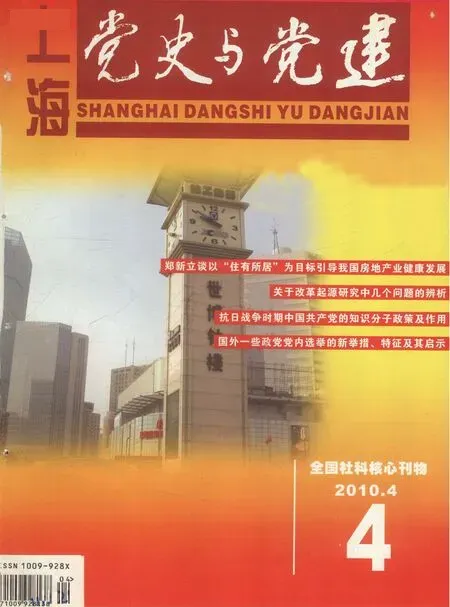关于改革起源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辨析
●张学兵
关于改革起源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辨析
●张学兵
在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起源的研究中,有些观点似是而非,有些观点不够全面,有些观点过于简单化。本文选取“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是不是改革的基本动因、改革从农村还是从城市开始、改革的对象是不是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国际机缘还包括什么等四个问题进行了辨析。
改革起源;问题;辨析
在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起源的研究中,一些观点已经耳熟能详,似乎不言而喻了。但稍作推敲可发现,这些观点中,有的似是而非,有的不够全面,有的过于简单化。本文选取四个相关问题略作辨析。
一、“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是不是改革的基本动因?
长期以来,有一个观点十分流行,即“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这是改革的主要推动力或基本动因。然而,无论从历史还是从逻辑的角度来看,该观点都得不到充分的支持,可质疑之处甚多。
第一个质疑来自史实层面。从1949年到1978年,除了五六十年代之交以及“文化大革命”最初几年,中国经济各项指标都处在不同程度的增长之中。资料显示,1950年到1978年期间,中国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9.5%,工业增长13.5%,农业增长4.3%。从国际比较来看,同一时期的工业发展速度,日本为12.04%,前苏联为9.5%,美国为4.5%。1951到1978年间农业的发展速度,前苏联为3.6%,美国为1.8%。[1]国外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莫里斯·迈斯纳在历数“毛泽东时代的遗产”时判断:毛泽东时代“与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及主要发达国家的早期发展相比,中国经济的增长率是较高的,与现代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周期相比,中国的发展速度也是较快的”[2]。当然,由于经济结构不合理,民生状况改善不大,但用“濒临崩溃的边缘”来形容上述状况,还是不尽客观。
第二个质疑来自逻辑方面。退一步说,即使“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们也难以遽然断定这与“市场取向”的改革之间存在着直接而明确的因果关联。如果说,处在“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局势导致了1970年代末的改革,那么,在逻辑上就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矛盾:经济体制改革为什么没有发生在1960年代初,而是在经济形势相对已经好转的70年代末呢?如所周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的三年“困难时期”,经济运行的混乱、民众生活的困顿相比70年代末,实有过之而无不及,那真正是“已经处于崩溃状态”[3]。更饶有兴味的是,经过国民经济调整,60年代初恰恰是中国计划经济比较典型和规范的时期。显然,用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来解释中国“市场取向”改革的基本动因,在逻辑上有些说不通。
可以说,用“经济濒临崩溃”来解释改革的基本动因,越来越难以为人所接受,恰如有人指出的,“这种说法为改革的合法性进行论证的成份远远多于客观的分析”[4]。那么,改革的基本动因是什么呢?人们可以从各种角度提出一个、两个甚至更多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要解释这些因素之间发生作用的机制是什么。本文仅仅着重指出,用“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来解释改革的基本动因,其说服力是不足的。
二、改革从农村开始还是从城市开始?
在人们的印象中,新时期的改革发端于农村,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城市改革逐步展开。但近年来出现另一种意见,认为城市改革的起步先于农村,早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就已经开始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只是最初成效不彰;而在此时,农村改革率先突破。
两种观点截然相反,但都有一定道理,也都存在偏颇。它们都试图简单地从绝对时间上比较农村改革与城市改革的发生次序,却忽略了这两种改革的差异性和某种程度的不可比性。从基本内涵和特征来看,农村改革与城市改革迥异其趣,前者是民众“自下而上”自发的改革,后者是政府“自上而下”主导的改革。
在20世纪70年代末,农民为了重获经营自主权和收益支配权,又一次自发进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而这种行为在当时仍属“非法”。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5]只是由于处在大转折的背景下,加上一些开明、务实领导人的支持,农民的自发努力才在一片争议声中逐步获得合法地位,被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所承认。正是基于农村改革的自发性,邓小平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6]
而20世纪70年代末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一开始就是政府自觉主导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家经委开始运作企业改革。[7]1978年10月,中共四川省委率先决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1979年5月,国家经委等六部门下发关于在京津沪三市的8个企业进行企业管理改革试点的通知。到1980年6月底,全国试点企业总计6600多个。[8]由于牵涉到复杂的利益关系调整以及需要整个宏观管理体制的“联动”,城市改革遇到的阻力和问题远远大于农村,因而一开始未有重大进展。
一个自下而上的改革,一个自上而下的改革,从严格的历史线索来看,比较二者先后是不可能的,因为虽可以列举城市改革早于农村的事例,但还可以说,包产到户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几度出现过;这种比较也是不必要的,因为正如上文所述这两种类型的改革在行为主体和行为方式上大相径庭,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可比性。然而,从抽象的逻辑线索来看,说农村改革在先,城市改革在后,也大体能够成立,因为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的侧重点确实在农村,此后逐步转入城市;另一方面确实是农村改革的突破对城市改革形成了压力和推动,也给决策者进行城市改革提供了经验和信心。
三、改革的对象是不是计划经济体制?
改革的对象是计划经济体制吗?答案似乎不言而喻。然而,细究起来也会发现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它涉及到对改革前中国经济体制特征和实质的基本把握。我们试从两个角度来看。
其一,1978年以前中国的“计划经济”与前苏联计划经济差异很大。改革以前,中国与前苏联的经济体制都被指称为计划经济,但在实际上此“计划经济”非彼“计划经济”。苏式计划经济比较强调计划的精确、周密和完善,以不断吻合最优化数理模型。比如,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前苏联就企图运用现代化计算机技术来加强和改善计划管理,特别是1971年苏共24大决定在已有的国家计算中心网和全国统一的自动化通讯网的基础上建立“自动化计划计算系统”。[9]中国的“计划经济”则缺乏这种特质,其行政命令色彩特别浓厚,“长官意志”十分明显,主要领导人的偏好不时会支配经济,因而经常处于随意和无序状态。
其二,1978年以前中国经济体制一直变动不居。有人认为,计划经济在中国存在时间非常短,而为了打破计划经济,从“大跃进”、1970年开始的“块块为主”到80年代以后的改革,已经用了数倍于“计划经济”的存在时间;“标本式的‘计划经济’年代只有1956-1957年和1962-1965年的两块,共计五年时间”。[10]这个观点很有意思,也不乏道理。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领导人就一次次地对现行经济体制进行调整,以1958年和1970年两次盲目下放经济管理权为典型,加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与实践的长期干扰,使中国经济一再陷入“大轰大嗡”的混乱之中。
可以说,中国“计划经济”在实际运行中,既不能做到“有计划”,也无法实现“按比例”。那么,改革的对象究竟是不是计划经济体制呢?可以笼统地说“是”,毕竟几十年来人们都称改革以前的经济体制为“计划经济”。然而,由于政治运动频仍,加上经常以运动的形式搞经济,中国的“计划经济”多少显得名不副实。准确地说,在改革以前,中国经济既排斥市场,更缺乏计划,或者套用邓小平关于中国社会主义“不够格”的说法,改革的对象是一种不够格的“计划经济”。
四、改革的国际机缘还包括什么?
谈起中国改革的国际背景,人们一般都会指出诸如西方国家的滞胀、国际产业的转移等因素,就像邓小平在1978年曾说的要“利用资本主义危机”。[11]然而,还有一个方面却不大为人所提及,那就是世界范围内自由市场复兴这一背景。
大抵与中国改革起步同时,西方国家在经济上也面临着一些与中国类似的问题。1930-1970年间,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盛行,许多私人工业实行了国有化,或由政府接收和经营。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失灵,西方国家普遍出现滞胀。于是,有些国家开始把政府企业售给私人部门,并不断放松对经济的管制。[12]由此,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市场力量复兴的浪潮,并影响到中国。这可从两个方面来观察。
其一,中国政府派了许多代表团到海外考察经济管理模式。比如,1978年6月1日、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并讨论赴日经济代表团和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的工作报告。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并讨论谷牧率团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汇报。在谷牧出访前夕,邓小平曾特别要求:详细地作一番调查研究,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13]1980年7月,社科院经济学家代表团访问法国后所写的报告中谈到了法国政府管理经济的经验,即“对公私企业的干预,主要是通过税收、信贷以至某些专卖价格(如汽油)等经济手段”。[14]无疑,这些考察对于中国决策者考虑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准许逐步引入市场机制,有着积极而正面的影响。
其二,国外许多经济学家来华,介绍相关市场的知识和经验。1979年到1980年初,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来华讲学。他的基本主张是,社会主义经济采取集权模式是不适应的,必须代之以分权模式。[15]1981年三四月间,捷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在北京和上海作了7次学术报告。他认为,由于“信息问题”、“利益问题”,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有市场机制,经济改革必须跳出指令性计划体制的框框。[16]1985年9月,多个国家的经济学家来华参加“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与中国同行就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税收和金融手段的运用等问题进行讨论。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20世纪80年代曾两度访华。1980年9月,他在社科院作了题为《中央计划与市场调节》的报告。[17]1988年9月他第二次访华,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还与他进行了会谈。此间,他在上海和北京的学术报告会上就如何抑制通货膨胀、提高企业效益、发展商品经济等问题谈了看法和建议。[18]
通过代表团出访和国外经济学家来访,人们不仅对西方市场经济的实效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还接受了现代经济学的启蒙,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选择。
[1][14]马洪.经济结构与经济管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21.321.
[2][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537.
[3]薛暮桥学术论著自选集[M].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456.
[4]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社会结构转型课题组.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J].战略与管理,1998(05).
[5][8]国家体改委办公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重要文献汇编[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0.81.243.
[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82.
[7]贺耀敏.扩权让利:国企改革的突破口——访袁宝华同志[J].百年潮,2003(8).
[9]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27.
[10]李志宁.“计划经济”在我国到底存在了几个年头[J].中国国情国力,2001(02).
[11]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写组.中国改革开放大事记(1978-2008)[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11.
[12][美]斯蒂格里茨.经济学(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139.
[1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中国改革开放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25.
[15]刘长龙,赵莉.市场经济思想史纲[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85.
[16]吴敬琏,荣敬本.奥塔·锡克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访华讲演内容简介[J].经济学动态,1981(06).[17]晓怡.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教授谈中央计划与市场调节[N].经济学动态,1980(12).
[18]张亮.“未来世界经济发展总趋势令人乐观”——访西方货币学派领袖米尔顿·弗里德曼[N].人民日报,1988-09-24.
D616
A
1009-928X(2010)04-0006-03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
■责任编辑:晏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