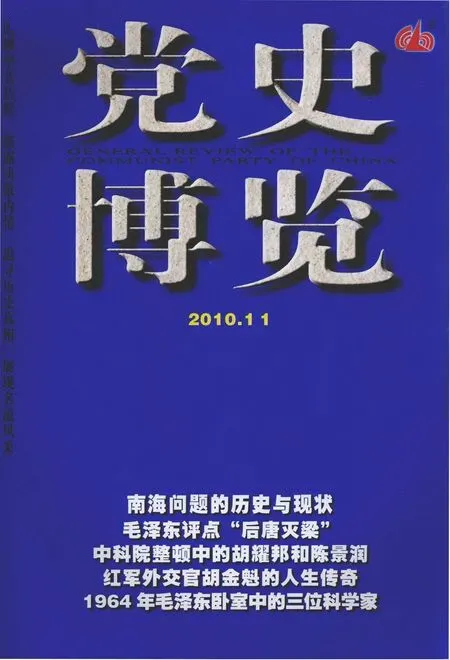于会泳浮沉录
艾英旭
从一个有音乐天赋的少年到音乐专家
于会泳,1926年6月生于山东乳山县海阳所镇西泓于家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于会泳从小喜爱音乐。家里虽然穷,但父母仍然拿出家里的积蓄,让他念书。读到中学时,因家中贫困,辍学回家。回到家乡后,被当地聘为小学教师。在此期间,他读了不少宣传共产党主张的进步刊物。1946年9月,他找到中共胶东地区党组织,讲明了自己的身份和参加革命的决心,随即被安排到胶东文化协会文艺工作团工作。
1949年10月,组织上送于会泳去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音乐专修班进修学习,时间为一年。在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于会泳很快就掌握了乐理、乐谱、演唱等音乐基础知识,并且很快学会了作曲。他选择民歌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他所演唱的民歌,生动传神,曲调优美,这引起了院长贺绿汀的注意。
1949年11月,于会泳还在上海学习期间,中共胶东文工团党支部经过讨论,发展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0年9月,于会泳结束了在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音乐专修班的学习。经院长贺绿汀举荐,于会泳留在音乐工作团搞创作工作。此时,该学院已更名为中央音乐学院上海分院(后改名为上海音乐学院)。
在上海音乐学院期间,于会泳创作了大量作品。入学不久,于会泳就比照着在文工团常用的创作方法,创作了小歌剧《夸女婿》,受到学院教师们的称赞。他编写出版的《山东大鼓》很有影响。他写的《陕北榆林小曲》、《单弦牌子曲分析》等音乐作品,反响也不错。他还与人合编了《胶东民间歌曲》专集。他撰写的《民间曲调研究》、《腔词关系研究》成为上海音乐学院本科和专修科的必修教材。他先后发表的《女社员之歌》、《幸福花开遍地香》、《不唱山歌心不爽》、《党的恩情长又长》等歌曲,在当时也受到好评。他于1963年出版的《民族民间音乐腔词关系研究》一书,有较高水平。依靠这部专著,于会泳得以跻身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专家行列。
被江青看中
1965年初,江青来到上海抓京剧革命,想要“促进”一下上海搞京剧现代戏。她把此前不久在北京搞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中最受好评的《红灯记》剧组调来,在上海演出多场,一时在上海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上海文艺界许多“笔杆子”纷纷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对《红灯记》进行评论。这些评论文章,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从政治上进行赞颂的,一类是从艺术角度赞颂的。于会泳也写了一篇文章,题目为 《从 〈红灯记〉谈开去——戏曲音乐必须为塑造英雄形象服务》,《文汇报》很快就发表了这篇文章。于会泳在这篇文章中认为,京剧假如要演革命现代戏的话,必须对原来的京剧音乐、唱腔作重大改革,老腔老调已不能适应现代戏的内容。他建议,每一出京剧现代戏都要为它设计出整套的唱腔,使成套的唱腔可以广泛流传。这篇文章与其他文章的不同之处,一是从音乐、唱腔方面谈的,二是提倡改革,而不光是赞颂。不久,他又在《文汇报》上发表了《评郭建光的唱腔音乐设计》一文。
江青对于会泳的文章非常赞赏,开始对于会泳这个人感兴趣。
有一天,江青问张春桥:“于会泳是个什么人?你去了解了解。”张春桥通过组织部门到于会泳所在的上海音乐学院,了解了于会泳的经历和表现,又调来于的档案认真看了一遍,然后到江青住处去汇报:于会泳是老区来的,出身贫苦,1946年参加革命,长期在胶东文工团工作,有音乐天赋,被组织上送到上海音乐学院培养,后留校工作,工作积极,是共产党员,在民歌创作方面有成绩,还写有专著。江青一听于会泳是个“根正苗红”的专家,马上提出要见于会泳。张春桥立即安排。第二天,于会泳被通知到锦江饭店小礼堂,说有一位领导同志要和他谈话。于会泳到地方后才知道,原来要见自己的是江青。谈话中,江青当面称赞他:“你的文章我看过,应该说我们早就认识了。你的文章写得很好!我们的想法还是一致的。”江青还当着于会泳的面对张春桥说,今后在搞革命现代戏的过程中要重用于会泳同志。江青的话,使于会泳受宠若惊。
成为江青搞样板戏的“台柱子”
这次与江青见面之后,于会泳的人生轨迹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久,张春桥将于会泳调到上海京剧院,让他担任重点剧目《海港》剧组的音乐设计组组长。于会泳在上海音乐学院的职务仍然不变,编制还在该院。
于会泳把《海港》中全部乐曲都认真分析了一遍,找出剧中乐曲中的问题,然后寻找改进的办法。为了改进乐曲,他对当时中国京剧所有流派的唱腔进行了透彻了解,分析各自的优点和不足,然后结合《海港》的剧情,对唱腔进行了重新改造和设计。他在设计《海港》女主角方海珍的唱腔时,更多地将京剧程派的唱腔加入进去,充分发挥了程派唱腔委婉深沉的特点。在戏中,当方海珍唱“忠于人民忠于党”这一段时,运用程派唱腔,将人物的内心活动和激情,表现得十分到位。当方海珍唱“有多少烈士的血渗透了这码头的土地”这一句时,唱腔既低沉又厚重,让人听了,有一种荡气回肠的感觉。上海京剧院把全剧的演唱录音后,于会泳立即将录音带送给江青听。江青原来就特别推崇程派唱腔,听了录音带后,非常高兴。
于会泳改造《海港》唱腔成功,使江青更加看重他,把他作为搞样板戏的“台柱子”。很快,于会泳被调到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组负责全剧唱腔设计工作。于会泳把全部心思又投入到这出戏的唱腔改造中来。他把中国传统京剧中最响亮、最高亢的唱腔进行分析选择,然后将其中精华部分融入《智取威虎山》一剧的唱腔中,还对全剧音乐进行了艺术加工,加进了西洋音乐的一些元素,使改造后的唱腔和音乐十分和谐。如在该剧“打虎上山”这段唱腔中,他把京剧锣鼓的点子与铜管乐器中圆号的浑厚交织在一起,并且和杨子荣的唱腔结合得天衣无缝,把杨子荣满怀激情打马上山,顶风雪入虎穴的壮志情怀,表现得十分充分。
“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考验”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把全部心思用在改编样板戏音乐上的于会泳对运动并不太了解。可是,运动的发展,让他不能不了解“文化大革命”。正在北京随《智取威虎山》剧组演出时,他接到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一个电话:上海音乐学院造反学生送到市委宣传部一纸勒令,于会泳必须立即回到音乐学院接受群众批斗、审查。
于会泳此前发表的文章和专著较多,造反派把这些作品找出来,挑毛病,断章取义,给他罗织了不少罪名。造反派抓住于会泳文章、专著中较多的“问题”,认定他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造反派指责于会泳有“资产阶级名利思想”、“走白专道路”,等等。造反派还说,于会泳长期不在音乐学院上班,是逃避“文化大革命”。得知于会泳是被上海市委宣传部调走的,便把这纸勒令送到市委宣传部,并且强烈要求市委宣传部不得保于会泳。
于会泳找到张春桥,问怎么办。张春桥回答说:“《智取威虎山》剧组的演出已经结束了,你回去吧。不要怕,我们信任你。你回上海以后,要和革命小将站在一起。”
于会泳听后,长出了一口气。他特别记住了张春桥这样一句话:我们信任你。因为此时的张春桥,已经是受到毛泽东信任的人。这一点,于会泳是知道的。
于会泳回上海后,立即到上海音乐学院,主动找到学院红卫兵各主要战斗队的头目,非常虚心地征求红卫兵的意见,并且主动作检讨。
这时,张春桥和姚文元也让手下人到上海音乐学院做红卫兵的工作,讲:于会泳是革命的,他被调来参与搞样板戏,是张春桥通过市委宣传部办的。他搞样板戏有功,受到江青同志的表扬,等等。此后不久,江青在一次开会时,特意派人用自己的轿车去接于会泳。还有一次,江青在于会泳陪同自己观看样板戏后,又特意拉于会泳和自己一起上台会见演员。江青此举,立即传到了上海音乐学院。红卫兵们得知后,不再揪斗于会泳,反而认为他是革命教师的代表。
紧跟江青
于会泳受到江青的青睐,工作更起劲了。即使是他当上国务院文化小组副组长后,仍然整天在排练现场,一丝不苟地过问每一个场景、每一个细节。他参加了《杜鹃山》、《平原作战》、《龙江颂》等样板戏的音乐创作。这些样板戏中的每个字,每个音符,都有他的心血。
于会泳年轻时就爱好写作,也有一定理论功底。他仔细研究江青讲话时强调的重心,然后写成文章。在“文化大革命”中流传一时并且曾经指导“文化大革命”中文艺创作的“三突出”理论,就是于会泳根据江青几次谈话的意思概括而成的。
1968年,《文汇报》上发表了于会泳写的文章《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这篇文章首次系统地提出了“三突出”理论。于会泳在文章中写道:“我们根据江青同志的指示精神,归纳为‘三个突出’,作为塑造人物的重要原则。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人物,在主要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人物即中心人物。”
这篇文章一发表,就受到了江青的称赞,说:于会泳的文章写得好,“三突出应该成为文艺创作的根本原则”。甚至还说,“是不是搞三突出,是革命文艺路线和反革命文艺路线的根本区别”。
为报答江青对自己的赏识,于会泳到处赞颂江青。他在指导演员演戏时,常说的话是:“对江青同志的话,一是要吃透,二是要紧跟,‘样板团’的人员,要永远铭记在江青同志领导下的幸福,做江青同志的兵的光荣……”在中共九大召开期间,《智取威虎山》作为首场样板戏,在京西宾馆礼堂上演。于会泳在演出的开场白中说了这样的话:“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为培育样板戏呕心沥血,她实际上是这出戏的第一编剧、第一导演、第一作曲、第一舞美设计!”江青似乎也受不了这番奉承,她站起来说:“会泳同志,你别这样说了,再这样我可要离场了。”
由于受到江青的重视,加上搞样板戏有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于会泳就担任了上海市文化系统革命筹备委员会主任和上海音乐学院革委会副主任。1969年4月,他作为上海的党代表,出席了中共九大,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中共九大之后,他担任国务院文化小组副组长。在1973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随之,在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会上,他被任命为文化部部长。
也曾受到江青的猜疑
江青是个喜怒无常的人,对于自己的亲信也常常是今天信任,明天又猜疑。她对于会泳也是如此。
施光南是于会泳的老师,“文化大革命”之前,对于会泳很是赏识,并着意培养。“文化大革命”中,施光南受到批斗。于会泳被迫参加批斗恩师施光南时,却迟迟不发言。张春桥对此很失望。
贺绿汀是于会泳的恩师,“文革”中受到批斗。于会泳想利用自己的影响,把贺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加以“解放”,却被张春桥斥责为有“糊涂”观点。张春桥还特意安排于会泳主持第二次批斗贺绿汀的“电视斗争会”,全市转播,张春桥则坐在办公室里观看批斗情况。于会泳主持这次批斗大会时,说话很软弱,而贺绿汀则在会场上顽强抗争,批斗会以失败告终。
1974年底,长春电影制片厂将拍摄的故事影片《创业》送国务院文化组审查。于会泳觉得这部影片很好,立即打报告向江青等人推荐这部影片在1975年春节公映。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先后批示同意,江青也圈阅同意。就在于会泳下令发行时,突然被江青叫到钓鱼台,她当面指责于会泳:“《创业》这么糟,你为什么批准发行?这部影片明目张胆为刘少奇鸣冤叫屈,替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老家伙评功摆好。”江青下令:长影厂要“修改”《创业》,于会泳要写检查。于会泳不敢不执行,立即以文化部的名义下令停止发行《创业》。除自己写检查外,还根据江青、姚文元的意见,写出文化部对《创业》的“十条意见”,上报中央。不料,当年7月毛泽东在《创业》编剧张天民的来信上批示道:“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毛泽东的批示下达后,“四人帮”一方面攻击张天民告刁状,另一方面把责任推给于会泳,要他和文化部承担责任。于会泳又不得不和文化部的党组成员共同写出检讨呈送毛泽东,并在文化部的司、局级领导干部会上作了公开检讨。
此后不久,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又与江青等人在电影《海霞》问题上发生矛盾。此时,于会泳恰恰被医生查出因长期营养不良患有代谢性肝炎病,医生意见:于会泳必须住院卧床休息。但江青等人认为,于会泳这是在逃避“斗争”。
1974年、1975年,“四人帮”搞“批林批孔”,矛头指向周恩来。于会泳明白这一点。他当上文化部部长后,与周恩来有过工作接触,对周恩来的品格和风范十分佩服;周恩来也称赞过于会泳。因此,他不愿意参与江青旨在攻击周恩来的斗争,对江青布置的“批林批孔”只是敷衍、应付。江青认为于会泳阳奉阴违。
幻想破灭后自杀身亡
尽管如此,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于会泳还是紧跟江青的。1976年初“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于会泳紧跟“四人帮”,全力以赴。因此,他仍受到“四人帮”的信任。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查获了“四人帮”所拟定的他们打算在上台后“组阁”的中央领导班子中,于会泳被列为副总理人选。
10月中旬,中央派出工作组进驻文化部。随之,于会泳被定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而隔离审查。在被隔离审查期间,于会泳对于自己紧跟“四人帮”十分悔恨,写了近17万字的检查和交代材料。当时,于会泳对自己今后的出路还比较乐观。他觉得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干过什么坏事,还做过不少如保护浩然、汪曾祺等作家的有益的事;自己跟随江青等人办的一些事情,只是奉命行事,不办也不行;自己有错误,没大罪,自己参与搞的样板戏,毛主席、周总理也是喜欢和肯定的;周总理还称赞过自己……他认为,隔离审查结束后,会给自己一个处分,处分大概不会太重,文化部部长是不能再当了,但总可以回上海音乐学院教书。即使回不了上海音乐学院,还可以回胶东老家的县文化馆或县剧团当一名普通干部,搞搞文艺工作。
于会泳确实过于乐观了。不久,中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直接点了他的名。于会泳感到如五雷轰顶。当天晚上他一夜未眠。第二天,他找专案组谈话,在表示认罪服罪的同时,请求要与中央驻文化部工作组组长谈一次话,期望这位组长能听听自己的意见。然而,他得到的答复是:组长工作忙,没有时间和他谈话。于会泳彻底绝望了。当看守人员向上级报告于会泳神志恍惚,有异常表现时,上级指示“提高警惕,注意安全”,但没有对于会泳采取其他措施。
1977年8月28日上午,于会泳在院子里散步时,发现厕所窗外有一只瓶子中盛放着足以使人穿肠烂肚的“来苏水”,便趁看守人员不注意时,将这只瓶子挪到自己经常洗脸的位置。下午,他午睡起来去厕所洗脸刷牙后,将“来苏水”倒入了自己刷牙的杯子中,用湿毛巾捂着带回了自己的房间。入夜,于会泳提笔给母亲、妻子和女儿写下遗书。遗书中有这样的话:“我跟着 ‘四人帮’犯了罪,对不起华主席,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我的结局是罪有应得,只有一死(后将‘一死’改为‘长期’)才能赎罪……我恨透了‘四人帮’,也恨透了自己;消除旧的于会泳……希望你们永远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革命到底。”晚8点左右,他决然地将自己刷牙杯中的“来苏水”喝了下去。当他被人发现时,已经处于昏迷状态。他被送到阜外医院抢救。医院采取了抢救措施,仍然没有挽回他的生命。
1997年,《音乐人文叙事》创刊号(年度学刊)上发表了于会泳的作品《民族民间音乐腔词关系研究》。作为音乐家,他仍然被人们认可。
——评张丽军《“样板戏”在乡土中国的接受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