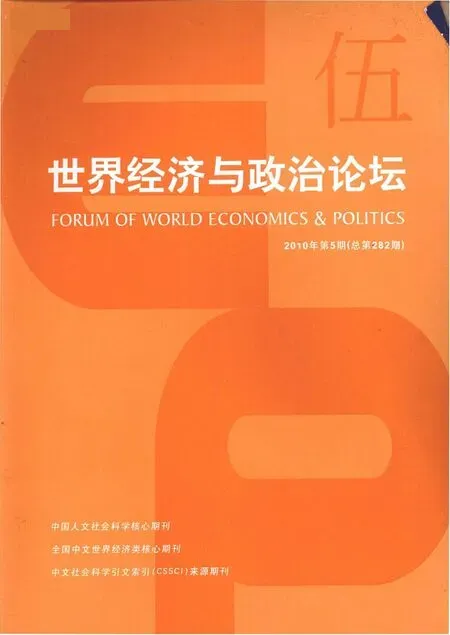现代性的兴起与主权的政治想象——关于身份政治的哲学思考
陶杨华
主权国家的存在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国内有序状态和国际无政府状态的著名两分,是主流国际政治理论的核心假定。对大多数国际政治研究者而言,放弃上述假定,对国际政治的理论性建构和思考就变得不可思议、虚无缥缈和无法想象了。本文则试图表明,放弃这一假定,不仅是可能的,必要的,而且是有益的。因为放弃这一假定,只不过使得对国际政治的实证主义式的探究成为不可能的,但这并不会危及对国际政治的哲理思考,相反,这恰恰为对国际政治的哲理性思考释放出了巨大的可能性空间。要认清这一点,关键是以一种历史性的眼光来考察主权原则,认识到主权原则是在现代性的语境下对政治秩序的一种解答,而这一解答不可能是终极和完美的。
主流国际政治理论的无政府状态假定
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把无政府状态作为它们的出发点,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对新现实主义来说,无政府状态是它的国际政治结构的核心变量;而新自由主义者也公开承认,他们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无政府状态下合作的可能性。
比较有争议的是温特式建构主义。初看起来,温特式建构主义似乎超越了无政府状态假定,因为它宣称“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然而细细品味之下,建构主义这一著名论断更准确的意思应当是,无政府状态的具体意义和特征是在国家互动中形成的。温特所真正质疑的是现实主义者所描绘的单一性的无政府逻辑,但他并没有质疑无政府状态本身。事实上,温特出于构建一个能与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结构理论所针锋相对的体系理论的需要,根本就无法质疑无政府状态本身。因为正如我们在本文一开始就表明的那样,要根本性地质疑无政府状态,也就意味着不能把主权国家的存在以及由此而来的内/外两分视为给定因素。但温特公开承认,由于构建一种体系理论的需要,他必须假定国家先于国际体系存在,温特这样写道:
“为了建立国际关系体系理论,在某种层面上,需要把国家视为给定因素。……我上面的观点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对国家本身提出任何质疑……我的观点是:体系理论不能够这样做,因为国家体系是以国家为先决条件的,所以,如果我们要研究这些体系的结构,就不能将体系中的部分再完完全全地分解开来。”①[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304
温特的意思很明显,为了建构一种体系理论,他将不关注下面这些问题: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本身又是如何出现的?国家对国际体系的两分本身何以是可能的?事实上,国家/国际体系的两分跟国内/国际的两分一样,都依赖于主权原则的出现。温特式建构主义也依赖于主权原则的给定性和非历史性。让·巴特尔森下面这段话清晰地向我们指出了这一点: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结构主义者和科学实在论者承诺通过废除幽灵式的结构和预先建构的施动者来结束社会科学中的物化,结果却是物化了主权本身,它们一点也没有可能解释主权是怎样进入到当代政治神秘地深层次结构中去的。结果是,主权是国内/国际存在的基础,它自己却没有基础,它是它自身可能性的条件。”①Bartelson J.A Genealogy of Sovereign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48
对于温特来说,追求一种体系化结构化的理论是其首要目标。在狭隘的科学主义语境下,体系化结构化的理论形态成了唯一可以被接受的理论形态。似乎如果不采取这样一种体系化的形式,对国际政治的理论性思考本身也变得不可能了。我们已经表明,这种对理论的体系化努力代价是巨大的,它使得作为在现代性的语境下对政治秩序作了解答的主权原则成了一种非历史性的存在,从而丧失了关于主权的政治想象,依然停留于马丁·怀特所谓的“主权国家造成的智识偏见”②Wight M.Why is There no International Theory?//Butterfield H,Wight M edited.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6:20中。
关于主权的政治想象
1.政治的概念
要知道何谓关于主权的政治想象,首先得知道何谓政治。政治意味着排斥、占有和界定。它界定一种合理的政治生活秩序并占有之,同时排斥所有其他的政治生活组织方式,视其为异己、他者,在冲突最为尖锐的时候,则视其为敌人。也就是说,在最高的意义上,政治意味着敌/友身份的确立和巩固。对这一点作了最权威阐释的当然是施密特的《政治的概念》,在该书中,施密特这样写道:
“政治性的敌人并不非得在道德上是邪恶的或审美上是丑陋的;他不一定是一个经济上的竞争者,跟他进行商业往来可能还会是有益的。虽然如此,但是,他是一个他者,一个陌生人;对他(作为敌人)的性质而言,下面这一点就足够了:以一种特别尖锐的方式,他的存在(跟我们)不同,外在于(我们),以至于在极端的情形下跟他的冲突是可能的。”①Schmitt C.The Conceptof the Politic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27(括号中的文字为笔者所加)
施密特的这一政治的概念影响深远,几乎所有后现代主义者都是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和使用“政治”这一词汇的。在让·巴特尔森下面这段福柯色彩很浓的话中,我们也能看到施密特式政治的概念的影子。巴特尔森这样写道:
“如果把知识理解成一个形成可靠论断的体系,那么,知识是通过区分而成为知识的,而这一区分是一个政治行为。首先,为了把自己建构成知识,一些给定的知识必须与那些外在于它的,不是知识的东西划清界限,这些东西被认为是观念、意识形态或迷信。第二,知识通过内在的区分来再生产自己,它区分什么是清晰的和模糊的,什么是有关联的和无关联的,什么是可靠的和不可靠的,什么是对的和错的。于是,知识意味着一组本体论决断;什么是存在的,什么是不存在的;什么被呈现为一个客体,什么缺失了。从这些决断中,导出了另外两个决断。第一个是伦理性的,它告诉我们我们是谁,谁是朋友,谁是敌人以及谁是陌生人。简言之,伦理性的决断是关于谁是跟我们一致的和谁是他者。另一个决断是元历史的,它告诉我们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怎么成为朋友,我们怎样走到这里,我们在哪里,我们往何处去。总之,知识,就它进行区分而言,是政治性的,并且与身份和历史无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②Bartelson J.A genealogy of Sovereignty:6
本文也采纳这一施密特式的政治的概念,并将用它来展示何谓关于主权的政治想象。
2.主权的政治想象
关于主权的政治想象可以有两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是指,像主流国际政治理论那样对主权原则做非历史性的处理,并把国内/国际两分作为其理论建构的出发点,本身就是一个政治性行为。就这样做鼓励和促成了对国际政治的实证主义式的探究,但却使得对国际政治的哲理思考变得艰难而言,这是一个政治性的行为;就这样做割裂了国际政治理论与政治理论,并使得对国际政治的思考与对良善生活的探究之间显得毫无联系而言,这是一个政治性的行为;就这样做使得主流国际政治理论成为一种现状维护理论,而丧失了批判和解放精神而言,这是一个政治性的行为。但让我们暂且搁置对这一层含义的探讨,我们更为关注的是第二层含义。
第二层含义是指,展开关于主权的政治想象,就是追问谁是主权原则的敌人,谁是它的朋友;主权原则肯定了什么,又否定了什么;主权原则是如何得以确立并获得合法性的,它的根基在哪。R.B.J.沃尔克下面这段话一定程度上向我们展示了关于主权的政治想象:
“对现代国家的承认涉及了一个与教会和帝国的层级性论断间的相当漫长的斗争。自主性的主权成功地掀翻了存在的巨链。平级的领土国家取代了那支配一切的关于层级性权威的论断。”①Walker R B J.Inside/outsid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Political The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131
也就是说,关于主权的政治想象就是要认识到,主权原则意味着政治秩序的重构,一种现代性语境下的重构。而在这一重构中,至为关键的一点是身份的重新界定。主权原则的确立意味着从此人首先不是基督徒、不是西方人、不是世界公民,人首先是某个国家的公民。
探讨一下下面这个问题是有必要的:那就是为何这一关于主权的政治想象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集体性缺失。为何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有意或无意地淡化主权原则政治性的那一面,而更倾向于把它作为一个价值中立的非政治性的概念来处理。
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是这样的:主流国际政治理论的实证主义倾向要求它们这么做。因为,如果它们赖以构建理论体系的基石居然是一个充满政治色彩的概念,那么,它们构建起来的以客观性和价值中立为标榜的实证主义大厦顷刻之间就有轰然倒塌的危险。但这个答案还不够深刻。因为,我们还可以继续追问,为什么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都痴迷和执著于实证主义?并且这个答案容易给人这样一种错误的心理暗示,即,似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这样做纯粹是出于一种学术探究上的兴趣或压力,但对具体的现实世界的政治进程则无甚利害关系。
一个更为深刻的解释是这样的:对主权原则的非政治性的处理,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根本而言都是为了防止人们对最高的善的追问,防止对一种最佳的政治秩序的追问。因为一旦我们认识到主权原则代表着一种特定的政治秩序,并且这种秩序是在与其他的政治秩序作生死搏斗中形成的,那么我们就难免会继续追问,由主权原则所代表的政治秩序是否是最佳的,是否还可能有更为美好更为合理的政治生活组织形式。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压制着这一追问,它们可能认为这种追问是危险的,会具有颠覆性和破坏性;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它们不了解这一追问的实质,它们不了解最高的善的标准内在于人的灵魂的高度精神体验中,也就是说,当灵魂向超验领域开敞之时。用沃格林的话来说就是,“由于它表征了在超验的边际上人的存在的真理,灵魂的真理性的秩序能够成为判断人和社会的秩序类型的好坏的标准。”①Voegelin E.The New Science of Politics//Voegelin E.Modernity Without Restraint.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2000:141事实上,根据沃格林的阐释,对最佳的政治秩序的追问,以及认识到判断政治秩序好坏的标准存在于当灵魂向超验领域开敞之时,可谓是整个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精髓。这一政治哲学的精髓毫无疑问在主流国际政治理论中是荡然无存了。但我们也不要过分责难主流国际政治理论。事实上进入现代以来,几乎所有政治学说都放弃了这一追问,在马基亚维利、霍布斯等人的著作中,我们同样也看不到这一追问。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主流国际政治理论就其本质而言,也是一种政治学说。并且,作为一种政治学说,用 R.B.J.沃尔克几乎天才性的透视来说就是,与其说国际政治理论解释了它所处的世界,不如把它看成它所处的世界的一个有待解释的方面更为有趣。②Walker RB J.Inside/outsid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Political Theory:6国际政治理论所处的世界是一个与古典世界有着根本不同的现代性的世界。这样,我们的讨论已经逼近了古典与现代的分野。我们已经明显地感受到,不了解何谓现代性以及其与古典世界的根本性的精神旨趣上的差异,我们就无法深入地理解主流国际政治理论,也无法真正体会到关于主权的政治想象的意义何在。但在我们转向对现代性的讨论之前,让我们用沃格林下面这段评价霍布斯的话来结束本文这一部分的讨论:
只有当历史的难题的根源,即,灵魂的真理,不再使人骚动不安时,通过发明一个持久长存的构造(指利维坦,笔者注)来解决历史的难题才是有意义的。通过摒弃人类学的和救赎论式的真理,霍布斯的确简化了政治的结构(意指放弃了对最佳政治秩序的追问,笔者注)。对于像霍布斯这样一个渴望和平的人来说,这种渴求是可以理解的;没有哲学(指古典政治哲学,笔者注)和基督教的信念,事情的确会变得简单起来。但他怎么能够废除它们而不同时废除内在于人性的超验性体验呢?这个问题,霍布斯也能够解决;他通过创造一个没有这样体验的人从而改进了作为上帝的造物的人。但在这一点上,我们进入到了灵智主义那梦幻般的世界的更高一级的领地中去了。霍布斯这一更进一步的事业必须被放在更为宽广的西方危机的语境下来解读。①Voegelin E.The New Science of Politics:218-219
现代性的兴起与主权的政治想象
随着存在的巨链被打破,主权国家成了历史的中心,历史从此要从主权国家得到拯救;与此相关,人不再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世界公民,而是逐渐以成为某个国家的公民为荣。关于主权的这两点政治想象,毫无疑问,昭示了人类精神层面的某种深刻的变革。没有这一相应的精神变革的发生,主权原则的合法性就是大成问题的;主权国家也不会像其在现代性晚期那样,被视为一种理所当然的存在。这一精神变革就是现代性本身,因为所谓现代性,就是“对前现代政治哲学的激进变更——这个变更的结果乍看起来是对前现代政治哲学的拒绝”。②施特劳斯.现代性的三次浪潮//贺照田主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2:88
也就是说,我们将把现代性解读为一种精神思潮,而主权原则始终与这一精神思潮息息相关。所谓现代性的兴起与主权的政治想象的关系,就是要去追问:经由何种精神变革,主权国家成了历史的中心,而正义问题以及正义问题由之发辄的人的灵魂的堕落与拯救不再成为历史的核心事件;经由何种精神变革,人不再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世界公民,人的精神从此可以停留于一个主权国家的范围内。答案当是在于搞清楚古今意识的根本性分野。
1.古典与现代的分野
让我们还是从霍布斯开始。在《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一书中,施特劳斯这样写道:
“要想恰如其分地认识和理解霍布斯的重要性,必须的条件是要把握一个根本的区别,就是霍布斯政治哲学的实体,即决定霍布斯思想的那个独特的道德态度与古典道德态度及基督教道德态度之间的根本区别。霍布斯政治哲学里蕴含的那个道德态度,是独立于近现代科学的基础的,至少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前科学的。与此同时,它又是为近代所特具的。我们倾向于说,这个道德态度,构成了近代思想的最深层。霍布斯的政治哲学,把它表现得最充分,最直率。”①[美]列奥·施特劳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申彤译.译林出版社,2001:5
施特劳斯的意思很明显,霍布斯的重要性在于作为他政治哲学核心的那个道德态度与古典和基督教的道德态度的决裂,由此霍布斯成为现代性的喉舌。换句话说,不了解古典和基督教的道德态度,也就无法真正了解霍布斯的重要性,也就无法理解何谓现代性,因为现代性正是相对于古典世界而言的,因为现代性正是由于其在精神和道德层面与古典世界决裂才成其为现代性的。
如果说古典和现代的分野根本而言在于两者在精神和道德层面的分野,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两者的分野实质上表现为古典世界中人的形象与现代世界中人的形象的根本差异,因为精神和道德层面的东西正是人的实存的核心。不仅主权原则的精神性内涵要从这一人的形象的差异出发才能理解,而且现代性的所有奥秘也存在于这一人的形象的差异中。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两种人的形象的差异的话,那么,应当是,作为精神的人与作为自然的人的差异。
2.古典的人的形象
无论古典哲学与基督教哲学之间有多少差异,在维护一种高贵的人的形象方面,在肯定人的灵魂的完整与有序,以及人的灵魂向一个超验的存在开放等方面而言,两者是根本一致的。一种高贵的人的形象存在于灵魂的觉醒、和谐与有序中,而这种灵魂的最高状态只有当灵魂向一个超验的存在开敞时才能达致。对基督教哲学而言,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用别尔嘉耶夫的话来说,“承认人的灵魂的绝对意义,这是基督教启示的最深厚的基础之一”①[俄]别尔嘉耶夫.历史的意义.张雅平译.学林出版社,2002:125,“基督教把个人与高级的神的本性、与其神的起源直接联系起来”,神的生命中心是“人的本性自身的最深刻的基础”②同上书:99,111。关于古典哲学,沃格林这样写道:
“事实上,柏拉图-亚利士多德式的分析恰恰就是肇始于对存在的这种真正洞见,而绝对不是肇始于对自身之可能性的思考。可以说,正是这种对于存在的洞见激发了这个分析的过程本身。在政治科学(此处政治科学实指古典政治哲学,笔者注)的奠立之中,一个关键性的事件就是达到这样一种哲学认识:此世之中可觉察的存在之各层面被一种超越的存在之源及其秩序所逾越。而这个洞见本身是以人的灵性灵魂走向超验的神圣这一场真实运动为根基的。正是在对存在之超世本源的爱的体验之中,在对智慧的热爱之中,在对善与美的欲爱之中,人成为了哲学家。正是从这些体验之中产生出了存在之秩序的意象。”③[美]沃格林.科学、政治与灵智主义//[美]沃格林.没有约束的现代性.张新樟,刘景联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3-24
“从这些体验之中产生出了存在之秩序的意象”,也就是说,当灵魂向超验领域开敞时,人认识到了“存在之秩序、存在之等级层次及其相互关系、存在王国之基本结构,尤其是人的本性以及人在存在之总体之中的地位”④同上书:23。经此体验,人认识到了某种超越于人的存在,人认识到了自身的高贵性有赖于那一超验的存在,人从而找准了自己在整个存在的序列中的位置,有所敬畏。同时,在这一高度的精神体验中,人真正成为一种自由的存在,人有足够的勇气和自信宣布自己为世界公民,人的精神已经无法满足停留于一个狭隘的地方性界限中。另外,随着灵魂的觉醒,随着对存在之秩序的确认,人开始追问正义,开始向流俗和偏见宣战。就这最后一点,沃格林给我们做了最好的阐释。在其《新政治科学》这一与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齐名的著作中,他这样写道:
“由于它表征了在超验的边际上人的存在的真理,灵魂的真理性的秩序能够成为判断人和社会的秩序类型的好坏的标准。但这一人类学的原则必须这样来理解:成为社会批判工具的那个人不是随便意义上的那个入世的个体,而是通过发现其与上帝的真正联系从而认清了自己本性的那个人。确切地讲,成为社会批判准绳的并不是人自己,而是那个通过精神性的区分从而代表了神性真理的人。”①Voegelin E.The New Science of Politics:141-142
综上所述,认识到存在着一个比当下的世界更为高级的存在的序列以及人的灵魂在向这一高级的存在序列的开敞中所获致的自由与高贵,可谓是古典的人的形象的精髓。古典世界致力于维护人的这一高贵性,致力于从高处来理解人,肯定超验的存在从而也肯定人性内在的超越的那一面。以至于著名哲学家雅斯贝斯忍不住说道,“在西方,个体自我的每一次伟大的提高都源于同古典世界的重新接触”②[德]卡尔·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王德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82。然而随着现代性的兴起,这一人的形象开始动摇和瓦解。
3.现代的人的形象
随着现代性的兴起,超验的领域被遗忘、遮盖和压制,存在的秩序被颠覆和破坏,开始动摇。人由此走上了自我肯定之路,人开始认为自己处于世界的中心,“人是万物的尺度”开始蜕变为“人是万物的主宰”。人开始急切地要求历史的意义在历史内部得到解决,由此,人的精力开始向外倾斜,人开始远离生活的精神中心。用俄罗斯著名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的话来说就是,“整个近代史就是欧洲人沿着逐渐远离精神中心的道路、沿着自由地体验人的创造力的道路前进的历史”①[俄]别尔嘉耶夫.历史的意义:104。最终的结果则是,在现代性末期,人感到危机重重,筋疲力尽,一种虚无之感开始蔓延。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沿着自由地体验人的创造力”前进的历史,在其历史的末尾,却使人筋疲力尽,创造力几近衰竭?别尔嘉耶夫下面这段异常深刻的解答,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据说,人文主义(别氏用人文主义这一词汇来指称整个近代史的精神实质,本文则用现代性这一词汇,两者是一致的,笔者注)揭示人的个性,让个性充分发展,把个性从中世纪生活有过的压制下解放出来,指引个性沿着自我肯定和创造的自由道路前进。但是,在人文主义中也有相反的本原。……人文主义把自然的人同精神的人分离开来,给自然的人以创造性发展的自由,远离生活的内部意义,脱离神的生命中心,脱离人的本性自身的最深刻的基础。人是神的形象和模样,人是神灵实体的反映,人文主义对此予以否定。人文主义以其占优势的形式肯定,人的本性不是神灵本性的形象和模样,而是世界本性的形象和模样,人是自然的实体,是世界的产儿、大自然的产儿,为自然的必然性所创造……人文主义借此降低人的等级。于是,人的自我肯定无须乎神,不复感觉和意识到自己同至上的、神的绝对本性即自己生命的最高源泉相联系,致使人遭到破坏。”②同上书:111
人遭到破坏,古典的人的形象被降级,自然的人取代了精神的人,人“开始受卑劣的过程、卑劣的原质支配,开始分解为人自身的自然界的因素”③同上书:123,这一政治性的事件,正是我们称之为现代性的东西。现代人的命运都处于这一事件的影响之下,主权原则也必须被放在这一政治性事件的背景下来解读。
首先,随着这一政治性事件的完成,主权原则的出现所必需的精神土壤也变得成熟。随着人日益远离生活的精神中心,随着人的精力的日益耗散,人开始变得虚弱、不自信,人的精神世界日益收缩、枯萎,人无力再像古典时期或近代早期那样勇敢的宣称自己为世界公民,人的精神开始满足停留于一个狭隘的地方性界限中;同时,随着存在的秩序被打乱,随着人开始走上无限的自我肯定之路,那么,那个无限的自我肯定的主权原则的出现所必需扫除的精神障碍毫无疑问已经不存在了,也就是说,至高无上的主权与现代意义上的那个无限的自我肯定的主体,其精神实质是一致的,都是对存在的秩序的颠覆,沃格林下面这段论述《利维坦》的话,可谓切中要害:
“契约的签订者们并没有创立一个能代表他们每一个人的政府;在签订契约这一行为中,人停止成为那个自我管理的人,从而把他们的权力欲求融合成为一个新人,即,国家,而这个新人的掌控者,它的代表,就是主权。”①Voegelin E.The New Science of Politics:236
其次,这一降级了的人的形象,这一受卑劣的原质支配的人,开始被普遍化和客观化,开始被等同于人的本性。“一种对现代人进行经验性心理探究的现代心理学发展了起来,所谓现代人是指那个在精神和智识层面迷失了方向从而主要受他的激情驱使的人”②Ibid:239。而这一扭曲了的人的本性又被用来论证主权的必要性。霍布斯的“利维坦”正是建立于这样一种低级的人的形象上的。正是因为单个的人是如此的傲慢,所以要用利维坦这一庞然大物,这一傲慢之王来压制和克服人性的傲慢。正是因为人已经无法内在地超越自己以获致灵魂的和谐与有序,所以必须用政治强权所施加的恐惧来迫使人服从秩序。我们可以用沃格林下面这段评价《利维坦》的话来结束本文这一部分的讨论:
“如果人性被假定除了激情的存在之外别无他物,如果人性被假定缺乏灵魂性的秩序之源,那么,对毁灭的恐惧的确可以成为迫使人服从于秩序的一个支配一切的激情。如果傲慢不会向正义女神低头,或者傲慢无法通过恩典来获得救赎,那么,它就必须被利维坦这一傲慢之王来打碎。如果灵魂无法参与到逻各斯之中,那么,那个让人的灵魂感到恐怖的主权就会成为国家的核心。”③Ibid:237
结 论
本文结论如下:
(1)本文实质上探讨的是主权原则的精神基础。我们已经表明,现代性的那个自我肯定的主体是主权原则的精神基础。而要清晰地看到这一精神基础,则需要我们了解古典的人的形象,那个由雅典和耶路撒冷所共同缔造的人的形象。因为现代性的那个自我肯定的主体,那个受激情所支配的主体,是从对古典的人的形象的拒斥和否定中形成的。也就是说,现代性的那个主体的造就,是一个政治性的事件。而只有对那个古典的人的形象有清晰地认识,我们才能充分地认识到这一事件,即,现代性的政治含义。也就是说,不了解古典政治哲学,也就无法了解现代性本身。就现代性深刻地影响了人的处境和命运来说,我们得出本文的第一个结论:不了解古典政治哲学,就无法了解当下的人的处境和命运,当然也就无法真正深刻地了解国际政治。
(2)就实证主义式的国际政治探究把主权原则物化,并无论有意或是无意,都压制了对一种最佳的政治秩序的追问,都否定了政治秩序的根源在于人的灵魂的和谐有序这一点而言,我们说,实证主义式的国际政治探究背弃了古典政治哲学的精神。从而,实证主义式的国际政治探究就停留于现代性的眼界内,它缺乏一种深邃的历史感(这一历史感只有清晰地把握了古今意识的分野才能获得),成为一种现状维护理论。可以这么说,无论体系化、结构化和科学化的国际政治探究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其代价实在过于巨大:主流国际政治理论丧失了思考人的处境和命运的能力,主流国际政治理论无法触及时代的精神危机,更谈不上为这一精神危机提供出路。由此我们得出本文的第二个结论:如果我们研究国际政治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人的处境和命运,并为时代的精神危机指明出路,那么就有必要拒斥实证主义式的国际政治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