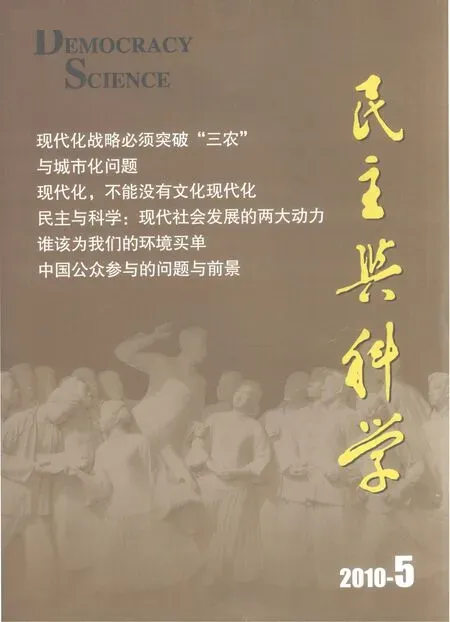到太空中定居去吧
——忆我国发射第一颗地球同步卫星的报道
■陈祖甲
到太空中定居去吧
——忆我国发射第一颗地球同步卫星的报道
■陈祖甲
如果说,1970年4月的第一颗卫星上天是我国航天事业的一个起点的话,那么1984年4月发射地球同步卫星成功则是我国航天事业新的飞跃。我有幸参加了这次报道。
无需多言,发射地球同步卫星是航天事业的一件大事。对这样的大事进行报道,自然需要做充分的准备。对于人造卫星技术我是外行。所以,在1983年9月我随国防科工委组织的记者团到达西昌发射基地去采访。实际上,这是一次参观和学习,所得颇丰。
西昌地处成都平原的外围,在两座大山之间有一大块平地。这里曾经是红军长征时期,刘伯承同志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握手联盟的地方,当地的工作人员陪同我们参观了遗址的现场。我们住在西昌城里发射中心的招待所。这次,西昌发射基地的领导和技术人员分别向我们介绍了“331工程”的有关情况。原来早在1974年,周恩来总理收到群众来信的建议,批示同意制造地球同步卫星。这个计划是在1975年3月31日由中央军委批准的,故而以“331工程”为代号。当时我国已经发射成功了14枚科学实验、返回式卫星,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与以往不同是,将要制作和发射的是地球同步卫星,它将被固定在赤道上空、与地球自转同步行进。它的功能是把收到的信息反馈回地球,我国的地球同步卫星反馈的信息将覆盖整个亚洲、太平洋及欧洲的部分地区。现在我们看到的卫视、听到的广播以及各地之间的无线通讯等都是通过地球同步卫星实现的。我们发射新卫星在世界上是第五个国家,运载火箭采用了新的型号以及零下几百度的液体燃料,有的国家还没有采用液体燃料。我们同一些科技人员进行了座谈,并参观了卫星发射指控中心、发射测试站和观测站,学到不少相关的科技知识,而且了解到科技人员的执著、拼搏和严谨的科学精神。然后,我们搭乘专机回北京。
在飞机回北京的路上有一段小插曲。我们乘的是一架三叉戟型飞机。我坐在机窗边上。飞机升空后,我好奇地向窗外望。巧合的是,我的位置正靠近机翼。大约飞了十分钟吧,我突然发现机翼上的油箱盖是打开的,盖子由一根链条连着,在机翼边晃动,油箱口还有晃出汽油的痕迹。这叫我很紧张,怕出事。我赶紧按电铃,呼叫乘务员,告诉她实情。她立刻请来机械师。机械师走来看了一下,马上去驾驶舱同机长商量。他回来说,飞机已经离开成都,那里有云层,无法返回。好在飞得时间长了,油面会下降,不再外溢,不会有大问题。请注意观察,如果有什么异样请马上通知我们。遵照机械师的嘱咐,我一直看着窗外,大约飞了两个小时,飞机在北京西苑机场安全降落。我的忐忑不安的心才真正地落下。
过了四个月,1984年1月,我与一位同事又去西昌。这次是到发射场观看卫星的发射。我们从北京飞到成都,然后转机到西昌。从成都到西昌属民航支线,乘的是安--24型小飞机,乘客才四十人左右。虽然只有半小时的路程,可是一路上遇着气流,飞机上下颠簸,我承受不住,呕吐了一口袋。
这回我们住在发射基地的招待所。那里没有接待过不穿军装的记者。因而住处好像是由办公室改的,设施简陋,盥洗室和厕所都是在走廊里公用的,吃饭需到工作人员的食堂。有一天吃烫面饺,我吃了后,又吐又泻。有人说,你得了“西昌病”。原来西昌地处高原,尽管海拔不算高,但蒸出的饺子像是半生不熟的,不易消化。我本来患有慢性胃炎,加之飞机颠簸引发的呕吐奠基,很容易得“西昌病”。基地给我一些药物,还专门为我开病号饭。每次是一碗面条,上面卧三个鸡蛋,加一撮豆苗,这让我联想到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战士在老百姓家吃的病号饭。我总算忍过一二天,便痊愈了。
在那里我们采访了火箭的总设计师任新民和副总设计师陈寿椿等专家,就等待天气的情况,合适时就发射了。整个工程的工作人员热情特别高涨,他们的口号是“质量第一,安全第一”、“决不让‘331工程’的‘列车’在我们这里晚点”。
大约在26日下午,我们得到通知说傍晚要发射。为了确保基地周围居民的安全,他们都被疏散了。我们也准备到发射现场附近去观看。谁知突然又得到通知,停止发射。为什么?原来发现了一个故障,是什么障碍?属于机密,我们无法打探。但可见工作人员的缜密和严谨的精神境界。第二天上午,通知我们去参加指挥部会议。我们以为,大概可以从会议上得到有效的信息吧。
谁知出乎我们的意料,会议一开始,国防科工委的一位领导就批评搞“资产阶级新闻自由”。这显然是针对我们的,让人莫名惊诧。这是怎么一回事?扣这顶帽子有什么依据?我们四个文字记者,住在一起,没有相机,也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都是穿军装的军事记者。他们没有同我们住在一起,平时活动也很少见。我们不必发新闻稿,都用新华社的通稿。如果真有人泄了密,那“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的帽子也不够用啊。听到这里,我已无心再听会了。后来讲了些什么,我也无心记录。那天下午,我们几个不穿军装的记者愤愤不平,找到国防科工委的宣传部长李运昌同志提出质疑。老李也不太清楚,无法解释,只是说向上反映。后来这件事就这么不了了之,但我总觉得如鲠在喉,到今天才吐出来。
1月28日,也是下午,我们接到通知,傍晚将发射。一套准备的程序正常地进行着。吃了晚饭,大约在七点钟之前,我们来到火箭发射塔附近500米左右的一个山洞里。这里有铁轨,可能是运输火箭与卫星的路。前面是宽广的发射场,火箭揣着卫星雄壮地矗立着,等待着迈上举世瞩目的行程。几位摄影记者都聚集在这里。因为离发射塔比较近,看得清,又安全。
过一会儿,火箭开始冒气,进入倒计时状态。接着,怀抱火箭的铁臂缓缓地打开,好像是母亲展开了双臂,温馨、豪迈地说:“孩子,飞吧,到太空中去定居吧!”高音喇叭里传来爽朗高亢的倒计时声:30秒、10秒、9、8、7、6……“点火!”随着一声令下,火箭下面喷出红蓝色的火焰。强大的火束,顺着一条特制的水泥渠道,把百米开外的小山包上的小树点着了。预先等待在那里的战士们冲上山岗,全力扑救。这时,我们的脖子似乎变成了活动的支架,顶着脑袋,目光顺着火箭的尾火缓缓地向上抬。火箭就像彗星拖着长长的尾巴,徐徐地上升,又顺势缓缓地拐弯飞向远方,最后只见一个亮点。“火箭发射成功了!”我们为从来没有见过的壮观场面所振奋,欢呼着拍手庆贺。
之后,我们回到住处期待消息:卫星是否进入轨道了?这只有在指挥部才能知道。过一会儿,两位火箭的总设计师回来了。看他们一个个脸色阴沉沉的,我们感觉有些不妙。出什么事了?打听之下,才知道第三级火箭运行不正常,同步卫星没有进入预定的轨道,发射失利。常言道:胜败乃兵家常事。第一次发射地球同步卫星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在所难免,那时在世界上发射卫星的成功率才86%,美国发射地球同步卫星有过两次失败。我们的失利可以理解。
事后,指挥部找我们谈话。那位科工委的领导表示:他们第一次组织到现场采访,没有经验。工作复杂,人员多,对大家工作便利不多,生活上照顾不周,希望同志们谅解。同时,我们得到信息,虽说当时的口号是力争“万无一失”,但国防科工委主任张爱萍同志始终关注着制造和发射卫星的每一个步骤,并早就让工作人员作了准备。于是,下决心发射第二枚,争取成功。
4月8日,第二枚火箭准备发射。这次我们没有去西昌,而在国防科工委的指挥大厅里观看。下午19点准备发射,20分钟后点火。火箭一级分离、二级分离、三级分离……经过一系列正常的运行,卫星进入轨道,发射成功!张爱萍同志当即来电,说这是第一胜利,是研制和试验部门的共同胜利,对卫星发射成功表示祝贺。
尽管进入了轨道,但在赤道上空定居还需时日。大约过了八天吧,卫星定点在距地面三万六千公里、东经125°的赤道上空,这是报经国际电讯联合会同意的。我国第一颗地球同步卫星发射完全成功了!这表明我国的航天技术在掌握卫星姿态控制、轨道控制等一系列高新技术上达到了新的水平,是我国航天技术新的起点和飞跃。
我们怎么报道?那时的思想还没有现在解放,紧箍咒还大一点,对报道的要求同现在大不一样。国防科工委政委周一萍同志对我们说,准备发新闻公报,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贺电。既要报道,又要保密,要处理好这个关系。
原则定了,我们怎么行动?按惯例,发公报与贺电都由新华社操作,写通讯也不是我的强项。于是,我走写述评的路,把这次卫星发射成功在我国航天事业中的飞跃意义和新的特点作个评述。我写的述评题为《新的飞跃 新的起点》,经过必要的审阅程序,在4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述评引起海内外媒体的关注。中国新闻社转发了这篇述评,当时境外的不少报刊刊登了这篇报道。
(作者单位:人民日报)
book=52,ebook=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