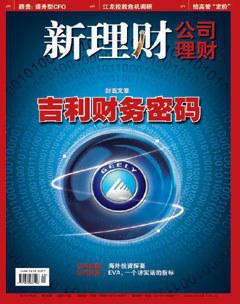投资谈判中的法律风险
王士萍 郑春华
在投资谈判过程中,风险主要存在于五大方面,下面的案例就是这些风险的具体体现。
政策合规性风险
CASE 1
贝多公司(以下简称“贝多”)是一家以经营增值电信业务为主的美国公司,随着其自身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近年来中国互联网行业的迅猛发展,贝多萌生出了到中国市场“淘金”的想法。经过朋友介绍,选中了北京金闻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闻”)这家同样以经营增值电信业务为主要业务的公司。由于经营不善,金闻公司出现了资金不足的情况,急需外部投资来度过难关。经过双方多次谈判,贝多同意以10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金闻80%的股权,双方就此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但是,在办理相关转让手续时,贝多却被中国电信管理局告知,根据《外商投资电信企业法》的规定,经营增值电信业务的外商投资电信企业其在企业中的出资比例不得超过50%。因此,贝多仅能购买金闻公司50%以下的股权,而不能达到控制金闻公司的目的。最终,贝多无奈地放弃了对金闻的股权收购。
▲ 点评:
投资不仅要受到经常性法律法规的调整,如《民法通则》、《合同法》和《公司法》等,还要受到投资所属行业的法律法规的调整和投资所在地地方政策的制约。因此,在投资谈判中,企业应予以特别关注,并确保在谈判前就相关法律法规做出相应的调查。特别是部分特殊行业,对外商投资限制过多,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对外商投资的审批却非常严格。
CASE 2
中国尚荣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荣”)是一家实力雄厚的钢铁公司。为扩大经营业务,尚荣拟投资中国百昌煤碳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百昌”)。尚荣(股权受让方)与百昌(目标公司)的股东张三(股权出让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收购张三持有的70%百昌股权,并支付了有关股权转让金。但双方在办理股东、章程等变更登记手续时,却被告知,根据该省地方政策的规定,企业收购煤业公司股权的,必须具备本省批准的煤炭兼并整合主体资格,由于尚荣公司不具有煤炭兼并整合的主体资格,因而股权买卖未被批准,尚荣拟投资煤炭行业的计划也就未能实现。半年后,张三因欠债而被债权人起诉,法院冻结了张三名下的、已出让给尚荣的70%百昌股权,这部分股权面临着被强制执行以抵顶张三债务的风险。
▲ 点评:
在善意债权人(第三人)的利益与合同相对方利益发生冲突时,法律将优先保护善意债权人的利益,尚荣的股权很可能被拍卖执行以偿还张三的债务。自然,作为一种惯常的法律救济渠道,在股权被执行后甲方可以通过追讨张三而弥补自己的损失,但该损失是否能够最终全部得以弥补,则取决于张三的财产状况、诉讼和执行的进展情况等多种因素。即便这样,股权被执行所导致的目标公司易主他人,仍是通过一个诉讼远远不可能弥补的损失。
其实,并购方案是否可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现阶段对该类商业行为的态度。商业行为就是利益划分,并购方除了应注意国家大政方针对此活动的利益导向外,更应当关注投资所在地政府的主张,大到省市,小到区县,均不可小觑。
交易主体风险
企业投资时,应注意审查股权“出让方”是真正的股东,还是“赝品”。即便不是纯粹的“赝品”,还须审查其是否为“挂着羊头的狗肉”。
CASE 3
山东凤凰集团(以下简称“凤凰集团”)拟投资煤炭行业。经过与山西胜利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胜利煤炭”)的股东王伟进行洽商,凤凰集团(股权受让方)向胜利煤炭(目标公司)投资12亿元,购买胜利煤炭100%的股权。在投资过程中,为谨慎起见,凤凰集团要求王伟向其出示相关营业执照和文件。于是王伟向凤凰集团出示了胜利煤炭的采矿许可证、生产许可证、煤矿安全生产许可证、矿长安全生产许可证、矿长资格证和营业执照等煤矿开采所需的“六证”,以及胜利煤炭的公章、合同章、法定代表人印章等印鉴。
收到上述文件后,凤凰集团认为王伟和胜利煤矿的身份已调查清楚,遂与王伟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收购了胜利煤炭100%的股权,双方办理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凤凰集团成为胜利煤炭的股东。此后,甲方开始对胜利煤炭进行技术改造,期望能够大展宏图。一年后,凤凰集团却被胜利煤炭的真正股东李明告上了法庭,诉请人民法院判令凤凰集团归还煤矿并赔偿损失,人民法院冻结了凤凰集团在胜利煤炭中的股权和煤矿。
原来,所谓的“股权出让方”王伟系该煤矿的租赁经营人,这就像房客偷偷卖掉了房东的房子一样,王伟卖掉煤矿后就销声匿迹了。现在,李明要求凤凰集团归还煤矿,因此,凤凰集团面临着“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危险。
▲ 点评:
在本案中,根据物权之追及效力的有关规定,目标公司的真正产权人是有权利向股权受让方主张返还煤矿的。所谓“物权的追及效力”是指物权标的物无论辗转流落于何人之手,物权人均得追及其所在而直接支配该物的法律效力;如果目标公司的产权人有证据证明甲方在购买目标公司股权时未尽谨慎审查义务、不构成善意受让人的话,该目标公司则会被判返还产权人。
交易的主体审查,作为投资方而言,就是查明出让方是否为真正的权利主体或者得到了权利主体的有效授权。交易方仅仅是提供了目标公司证照等是远远不够的,上述资料充其量是交易的形式要件而已,具体到实质要件,投资方还应当要求出让方提供至少下列文件,并对提供的下列文件到核发该文件的有关机构进行核实:
1.工商登记的公司历史沿革资料,其中有股东姓名或名称,身份证号码或法人机构代码,股东出资是否到位等资料;依据自然人股东的身份证号码,到公安部门进行查询,核对交易主体是否与工商登记的股东确系同一人。
2.与目标公司的其他股东(如有)取得联系,核实交易有关情况。
3.交易主体若是从“前手”那里买来的股权,则应提供地方政府的有关批准文件(依法如需),和交易主体与“前手”签订的有关合同,及该合同确已履行的证据。
4.即便上述文件均已具备,还有可能存在隐名股东的情况,即:交易主体仅是全部或部分所出让股权的挂名股东,对所挂名持有的股权并无所有权和处分权,而真正的权利人为真正的投资人即隐名股东(又称“实际控制人”)。为避免购并结束后隐名股东追索已转让的股权,购并方应当要求出让方、目标公司和其他股东共同出具承诺函,承诺所出让的股权不存在隐名投资人。
交易客体风险
交易客体一般为投资方投资时收购的公司。一般情况下,投资方应从公司本身是否干净、无瑕疵上做细致的审查,深挖本质,才能有效地防范风险。
CASE 4
北京金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鑫”)是一家经营电子商务的企业,为扩大经营业务,其向北京圣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达”)投资了50万元,从股东张三(股权出让方)处购买了圣达60%的股权,随后,双方进行了股权和转让价金的实际交割。一年后,王五起诉圣达,要求偿还其欠款人民币200万元。得知该消息后,金鑫“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在投资时,其已调查清楚,圣达并未欠王五任何债务,为何王五要起诉圣达呢?
原来几年前,李四作为北京光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亮”)的老板,其剥离出光亮的优质资产与张三合资成立了新公司圣达,而将所有的负债都留在了原公司中;后来,李四又将其在圣达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了张三并移居海外。如今光亮的债权人王五起诉圣达,要求其在所接受的优质资产的范围内承担还款责任。了解情况后,金鑫后悔莫及,自己在投资时小心谨慎,认真审查了公司的资产、负债情况,以及股权是否“干净”、是否设定了抵押、质押,但是现在还是面临着偿还王五相关债务的风险。
▲ 点评:
上述案例中,李四用于出资设立圣达公司的资产,是有负担的资产,即其上背负着留在光亮的负债,因此该用于出资的资产是有瑕疵的。用瑕疵资产出资形成的圣达股权,自然也是瑕疵股权,根据“债务跟着资产走”的原则,目标公司即圣达应当承担光亮的债务。这说明,审查交易客体中的风险,要审查股权上是否设定了抵押、质押等担保权,是否存在查封等限制转让的情形,以及出让方是否出资到位和是否有抽逃出资的行为等,仅仅是上述审查还是不够的。除了经常性的审查项目外,还要对公司资本本身进行审查。
交易对价风险
交易对价,往往是依据交易标的的净资产值,在法律法规的范围内,经协商确定的;而决定净资产值的基础因子为资产和负债。因此,在投资过程中,审查被投资方资产和负债中的风险是风险防范的主要内容。
CASE 5
北京万里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万里”)欲收购山东天水抽水蓄能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水”)100%的股权,遂与天水(目标公司)的全体股东—张三、李四(股权出让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约定:股权转让金即为天水的全部净资产值。于是,双方委托了评估机构对目标公司净资产进行了评估,其中天水资产1.8亿元,负债1亿元;因此净资产约为8000万元。双方按照8000万元的交易价格,履行了股权和对价的实际交割,并办理了目标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一年后,有关部门通知甲方,要求目标公司缴付水资源费约200万元。原来,天水在出让时尚欠有关部门水资源费200万元,万里在收购天水时,未将该笔水资源费在净资产值中扣除。因而,白白损失了200万元。
▲ 点评:
在投资过程中,审查被投资公司的资产是否完整,是否有欠缴的国家行政收费,是否有未支付的人员工资、社保等费用,并购方应当到国家有关主管部门进行详细核实,避免风险的发生。
税收风险
CASE 6
北京祥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祥凡”)欲投资一家图书公司北京风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风易”)。经与风易的股东张三协商后,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祥凡向张三支付人民币250万元,祥凡取得风易公司100%的股权。在此之前,乙方在获得目标公司股权时支付了人民币100万元。
双方到工商局办理目标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时,因未能提供税务机关开具的股权转让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完税凭证或免税、不征税证明,而被拒绝。于是祥凡要求张三缴税,张三称股权转让金已全部用于支付购房款,已无其他钱款上税,双方为此扯起皮来,迟迟办理不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 点评:
《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个人转让股权的所得属于财产转让所得项目,以转让财产的收入额减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并依20%税率按次缴纳个人所得税。值得注意的是,《个人所得税法》及《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暂行办法》规定,在股权转让中如发生应税所得,以支付应税所得的单位或个人为个人所得税的扣缴义务人,以所得人为纳税义务人的;扣缴义务人不得以不知道为由不履行扣缴义务。
上述案例中,祥凡即为代扣代缴义务人。现张三与祥凡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所持目标公司股权作价人民币250万元转让给祥凡。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属产权转移书据,还应按协议价格(所载金额)的万分之五缴纳印花税;张三的该股权转让应缴交印花税=2,500,000×0.5‰=1,250(元)。因此甲方应代扣代缴的乙方应缴纳个人所得税=(2,500,000-1,000,000-1,250)×20%=299,750(元)
当购买自然人股权时,可以采取下列运作方式来防范该风险:(1)双方在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时,就将扣缴税款事宜约定清楚;(2)股权出让方确不愿缴税、股权受让方又确希望购买该股权的,可以要求股权出让方先将股权转让给其实际控制的法人单位,再由该法人单位将股权转让给股权受让方。这样,既免除了股权受让方的代扣代缴义务,又使该交易顺利、合法地完成,同时将扣缴义务推给了乙方处理,一举多得。
(作者供职于北京市明诚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