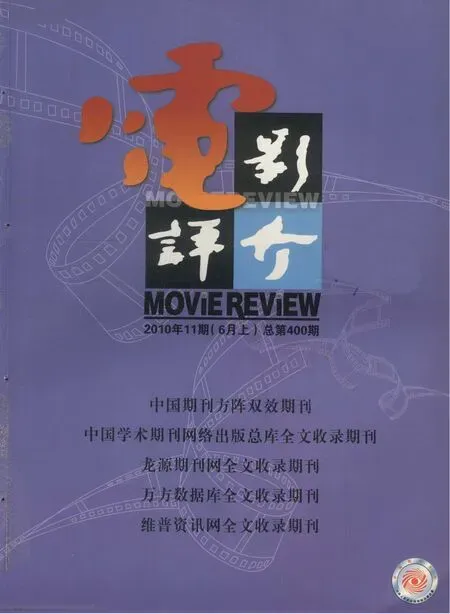论新版《画皮》中“人妖恋”书写的新向度
鬼魅之说在中国历来非常兴盛,尤在蒲松龄《聊斋志异》中达到顶峰。其中最有影视缘的要属《画皮》,这一千多字被几度改编、重拍,每次公映皆引起轰动。由陈嘉上导演,周迅、陈坤、赵薇主演的《画皮》是当下最新的阐释版本。前车之鉴使之在拍摄剪辑过程中格外小心,最终没有遭遇到1966年鲍方版由恐怖而遭禁映的命运;也并非如1979年邵氏公司李翰祥版着力于色情的香艳风月片。它运用特定的电影叙事手段来脱离由题材带来的恐怖与艳情,表达了导演自己的思想,且取悦大众保证票房。
一、回避还是噱头:色情与恐怖
小说《画皮》的内容决定了影片所必要的场景:画皮的恐怖和勾引的艳情。蒲松龄简约的文字可以给读者无限遐想空间,以达到理解主旨目的。对导演而言,色情和恐怖是表现人性至深的一种手段,也是寻求票房的一个保证。而以往的两部片子在恐怖与色情上遭遇到了某种尴尬。此时度与量的把握成为导演心中最忐忑之处。
影片宣传时涉及恐怖的场景有两个:吃人心和画人皮。这既是为了唤起观众的阅读期待,更是为了票房。然而,吃人心的场景始终没有正面出现,狐妖吃人心由王生妻恐怖的脸侧面呈现,狐妖也只是有擦拭的动作。恐怖之因源于观众的惯性想象,且程度在自己经验过或阅读过的可接受范围之内。最有噱头的“画皮”一幕,虽说有几分害怕之意,但在当下国外魔幻恐怖大片对比之下,如《木乃伊》系列,则变成小巫见大巫,最多只能是一个小小的惊吓,根本谈不上恐怖。
涉及男女感情纠葛似乎便有激情戏,或为表明主旨,或为宣传卖点。新版《画皮》在王生、狐妖/妻子的感情上也涉及此。王生和妻子的床上戏只是拥抱和接吻的保守阶段,狐妖裸背也成为大陆影片在“露与不露”、“脱与不脱”中摇摆的无奈或暧昧,是在吸引眼球和影片送审之间的思量和平衡。
二、真实还是虚构:故事与年代
新版《画皮》主题被定位为思考人的情爱观,尤其面对婚外情应该怎么办的问题。这个当代话题被放置到汉代(有着汉服舞美的策略),造成了故事发生与讲述年代的错位,会使观众放松对细节合理性的警惕,使故事获得了多向性阐释的可能。
电影宣传画上有“爱无界”字样,按此理解,应该肯定狐妖与王生的“真爱可跨越人妖之界”。但影片结尾却是狐妖用死来离开,使之回到原有的生活秩序。于是,这种矛盾叙述可引发相当有意味的思考、追问。
1.依然是“狐狸精”
“狐狸精”的真谛在于媚:面容姣好、柔情万种,是古今情人(单指为爱情跨越底线,物质利益交换目的除外)的必备素质,还有为占有爱人的不择手段,或曰执着,或曰歇斯底里。
“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似乎符合大众心理期待的结局。“小唯”这一角色在影片中受到谴责的话,原因究竟何在?妖吃人,还是第三者?这恐怕是很难说清楚的一种复杂。最终她的死使家庭恢复到稳定状态,但在观众对“浪子回头”得到的胜利的欢呼背后,在展示夫妻重新恩爱的宁静平和背后,我们可以感受到九霄美狐凄凉的眼神。
2.依然还是“地母”
与古代家庭妇女不同,王生妻子(佩蓉)有独立事业,经营着胭脂水粉店。这种当下性设定易使人产生“男子爱后妇”的鄙夷和谴责,妻子追求情谊深笃,男子仅看容貌。但电影先展示王生英雄救美的情节,后出现妻子佩蓉,这一剪辑编排方式无意中减少对前者的贬低,似乎佩蓉成了不协调因素的制造者,成为“第三个”出现的主角。
佩蓉(王生妻子)的痴心最感动观众之处在于主动退出、喝药、变妖,愿牺牲自己来挽救丈夫及全城百姓,前者指向个人情感,后者指向民众大义,以柔弱而又坚强的方式,弹拨人们那根脆弱的神经。这种奉献、牺牲的贤妻乃至地母形象给予道德义愤存在的充分合理性,进而赚取眼泪和拉动收视率。
3.依然“进退两难”的王生
在传统文化中,书生注定要因敏感而出轨,又要因担当社会角色而受到伦理规范的质疑。而武生,长年征战在外,邂逅便被理解为浪漫。于是,王生由《聊斋》中心术不正、轻佻好色之书生,转变为英武将军,且英雄救美。
王生喜欢狐妖不同于以往的负心汉,既非为功名,也非为美色。最重要一点是王生并没有真正彻底背叛婚姻,性冲动被道德塞住。虽然有无数次的梦中相遇,这依然在男子的正常反应范围之内。在剧情中,他与狐仙并没有发生性关系,甚至干净到没有接受狐仙的表白,虽有犹豫,但坚持了家庭责任,成为好丈夫的楷模。
这种楷模的塑造将女人之争推到了前台:狐妖身份的发现由前几版的男主角变成了现在的妻子,将王生与狐妖的冲突改放在了两个女人争取一个男人的信任上。过多的感情戏都将女人放在了聚光灯下,甚至是每一个细微的表情和内心的轻微波动,都要接受大众的监督和审判,但男女之间的情感终究不是独角戏,男人究竟躲在何处?
王生的自杀显然渲染了浓烈悲壮的一幕,但深思之后,毕竟是晚了一步,是对别人付出的一种回应,而非主动。没有妖的世界是平静的,但似乎是波澜不惊的;有妖的世界是激情的、但又是冒险的。这种感性和理性的平衡点又在那里?这或许是导演无法给予解释的,,是现实中存在的恍悟而又困惑之处:这是一场女人之间的战争。
三、结语: 获利的艺术
感情出轨后回归家庭,这种模式迎合了大众口味的同时,又帮助和促成了这种口味的确立和巩固,造就了一代习惯于欣赏大团圆结局而有窥视欲望的观众。伦理秩序道德责任的呼吁,固然是一种庄重,但过程一旦被例行化,粘贴着同样的标签,说教意味浓重,似乎就有了嘲讽的意味。因此,我们的导演应该将娱乐和思考的并置。
如何做到获利的艺术?导演陈嘉上似乎展示了更高明的做法:痛苦的展示(depicting),而非讲述(telling)。全方位的体验之后,观众会置身于那种特定的氛围,感受心灵的震撼,激发对现实相关问题的思考。“人是一种有性别的生物”,感情出轨的问题,是现实与道德给人们提出的难题,究竟如何给出满意的答案呢?即使社会思想解放,这种两难处境依然很难解决。影片只是告诉观众:在经历了道德与情感的两难矛盾,经历了社会的激烈争论之后,应该跳出传统的道德评判模式,转入冷静的和客观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