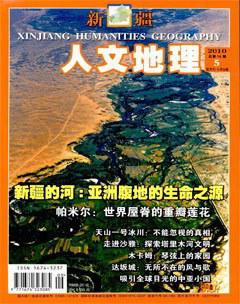丝绸之路上的三大名果
沈 苇



葡萄、无花果、石榴、并称为“丝路三大名果”。它们是西方通过丝绸之路向东方输出的三种最著名的水果。无疑,也是三种绿色文化。
葡萄:火洲翡翠
吐峪沟是吐鲁香火焰山中的一个峡谷。
阵阵热浪中,展开了吐峪沟的葡萄园,展开了葡萄树的浓荫和果实的芬芳。站在山坡上,葡萄园就像卡在峡谷里的一块翡翠,又像涌动在村庄四周的绿色波澜。峡谷中的葡萄园是一种珍藏,如同日月的“后宫”,流淌着绿色的真、绿色的善,也流淌着肉欲的欢愉和感伤。它散发的气息近似女性身体的芬芳:从夏日少女的麝香到秋天成熟女性的馥郁,仿佛时间遗失的珍宝隐藏在那里,提醒它去孕育、发酵、酿造,从细小青果的羞怯,到突然间蜜汁四溅的放肆,整个葡萄园为之一亮,变得超凡脱俗、神圣高洁。
如同葡萄到葡萄酒的演变,从夏天到秋天,是葡萄园从肉身向精神的一次缓慢过渡。当葡萄变成了琼浆。变成了纯粹的精神饮品,葡萄园的世俗意义也在发生变化。有时你会觉得,深秋萧索的葡萄园,冬天葡萄树埋墩后的景象,似乎与精神化的吐峪沟的背景更加匹配。安放在峡谷中的这块翡翠,只是圣地暂时的配饰,生土与山峦的荒凉,却是事实上的无边无际。
在世俗的荒凉中,葡萄干和葡萄酒是葡萄的两种出路和未来。前者是岁月的“干尸”,后者是圣徒的“血”。
上个世纪初,米德莱·凯伯(Mildred cable,1878~1952年)等三位法国修女在去向中国西部沙漠的旅行中,都来过吐峪沟。她们在《戈壁沙漠》一书中写道:“吐峪沟的葡萄园如同火焰山中的翡翠,一种幽幽的香气令人想起天上的事物。浅金色,或清朗的淡绿,吐峪沟葡萄干是黄金、琥珀和海绿色的玉粒。”
差不多同一时期,德国探险家冯·勒柯克在吐峪沟进行考古挖掘,称这里的无核白葡萄干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葡萄干”。
他还说:“这种葡萄干在当时的北京也是一种非常奢侈的食品,价格很贵,因为从吐鲁番到北京要走115天。”(《新疆的地下文化宝藏》)
洋海古墓位于吐峪沟洋海夏村西北,为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后氏族社会大型墓葬。考古工作者在这座古墓里发现了两千年前的葡萄藤。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吐鲁番地区文物局的考古报告说,葡萄藤与其他木棍盖在281号墓的墓口上,藤截面为扁圆形,长115厘米,宽2至3厘米。洋海的考古发现有力地证明: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吐鲁番盆地已经种植葡萄了。
无独有偶。在新疆博物馆,我瞻仰过1600年前的几粒葡萄干,它们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地下古墓。
阿斯塔那古墓群是高昌回鹘王朝的公共墓地,经过十多次的考古挖掘,已出土各种珍贵文物上万件。在这些文物中,发现了不少租种葡萄地、浇灌管理、买卖葡萄园的契约、书信、账册等文书,还有随葬的葡萄(葡萄干)、葡萄枝、种子等。高昌居民将一串串鲜葡萄供奉在死去亲人的墓室里,为的是让他们在幽冥世界里继续吃到生前喜爱的这种美味的水果。这在当时,是一种十分流行的风俗。
阿斯塔那墓葬壁画描绘的情景,也为吐鲁番大约在南北朝时期已是重要的葡萄种植业中心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在一幅壁画上,一对贵族模样的夫妇端坐在葡萄架下宴饮享乐,餐桌上是美味佳肴,侍女们忙着斟酒、上菜。出现最多的是女供养人手捧果盘的壁画,果盘里除了梨、甜瓜,还有葡萄。摩尼教徒的工笔画也常常以葡萄等水果为主题。与此同时,葡萄纹样、图案开始装饰佛教洞窟和普通民居。
关于葡萄传人西域和中亚的时间和情况,历史学家也有自己的看法。
有人认为,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东征,把希腊化文明带人中亚,同时把葡萄种植、葡萄酒酿造和酒神崇拜带到了这个地区。汉时“蒲萄”二字的发音,直接源于希腊文“bonytis”。
两个世纪后,张骞“凿空”西域来到大宛(今费尔干纳),发现这里俨然已是中亚葡萄种植中心。“宛左右以蒲萄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积数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萄肥饶地。”(《史记·大宛列传》)张骞从大宛带回了葡萄种子(还有苜蓿种子),但未获得葡萄酒酿造技术。
据此可以推测,新疆种植葡萄要晚于亚历山大东征,但不会晚于张骞出使西域。
公元后,葡萄种植在新疆已十分普及。384年,北凉将军吕光征龟兹(今库车),他报告说,这里有许多葡萄园,葡萄酒总是被大桶大桶地享用,人们在酒窖里日夜酩酊大醉,连守城的士兵也不例外。“胡人奢侈,厚于养身。”以吐火罗人为主的龟兹居民在信仰佛教的同时也不忘纵情享乐。
在伊斯兰教传人之前,西域民族嗜酒如命,收录在《突厥语大词典》中的民歌证实了这种豪饮:“让我们吆喝着各饮三十杯。让我们欢乐蹦跳,让我们如狮子一样吼叫,忧愁散去,让我们尽情欢笑。”他们喝的是西域最古老的葡萄酒——慕萨莱思,也即唐诗“葡萄美酒夜光杯”中的美酒。
西晋张华所著《博物志》上说:“西域有葡萄酒,积年不败。彼俗传云,可至十年。欲饮之,醉弥日乃解。”
隋末唐初,中原汉地已种植葡萄,但尚未掌握葡萄酒酿造技术,王公贵族和文人雅士对时常耳闻却不能品尝的“西域琼浆”心向神往。公元640年,唐太宗发兵破高昌,得到了马乳葡萄的种子,将它们种在皇家禁苑中,专门开辟了两座葡萄园,同时从回鹘人那里学到了酿酒技术,共酿出了8种“芳香酷烈,味兼醍醐”的葡萄酒。
唐王朝要求高昌以年贡的方式进贡不同品种的葡萄产品,除葡萄干外,自然还有葡萄酒。这一进贡制度一直延续到清代。康熙皇帝甚至说,让自己的臣民种植葡萄等果类,比给他们建造一百座瓷窑还要好。
从唐代开始,“吐鲁番”这个名字就与“葡萄”紧紧联系在一起了,这是地理与果实的唇齿相依、水乳交融。直到今天,当我们说出“吐鲁番”时,脑海里的第一反应便是“葡萄”。
无花果:长在树上的糖包子
无花果是人类最早栽培的果树之一,已有5000余年的历史。它的原产地,一说是小亚细亚土耳其的Carica。一说是阿拉伯半岛南部,后来传人叙利亚、高加索、土耳其等地,于公元前14世纪前后引入地中海沿岸诸国。
在古希腊,无花果是祭祀果品,是渗透了地中海阳光的“圣果”。它出现在希腊瓶画上,供奉在星象师的占卜台上,点缀在酒神的花篮里。它和葡萄、常春藤一样,是酒神的配饰和标志。
古罗马的农业已相当发达,帝国的果园内大量种植葡萄、苹果、橄榄,除此以外,无花果是罗马人的最爱。除了鲜食,他们还将无花果制成果脯、果酒、果酱、果汁等。
在中东,无花果是十分普及的粮食作物之一。希伯来人喜欢将它晒干,压成饼状,是常年吃的一种食物,就是再穷的人也吃得起。因此无花果在巴勒斯坦有“穷人的食粮”之称。希伯来人最早发现了无花果的药用价值,将它贴在脓疮上用以治病。“以赛亚说:当取一块无花果饼
来,贴在疮上,王必痊愈。”(《旧约·以赛亚书》)公元8世纪前后,无花果通过丝绸之路由波斯传人中国,首先是奔波在帛道上的商贾和僧侣们将它带到了西域,开始在昆仑山北麓的塔里木绿洲种植。现在我们在新疆南部看到的无花果,仍是古老而单一的波斯品种,即波斯语所说的“a-yik”(阿驿)。但它们品性优良,历经千年而少有改变。
唐人称无花果为“底称实”,他们对这种来自西方的“圣果”已有一定的了解。段成式在《酉阳杂俎》写道:“底称实,波斯国呼为阿驿,拂林(阿拉伯半岛)呼为底珍。树长四五丈,枝叶繁茂。叶有五出,似蓖麻,无花而实。实赤色,类(蓖麻)子。味似干柿,而一月一熟。”
在印度,无花果树(优昙钵)是菩提树(毕钵罗)的一种,是神圣的树。它能在自身的灰烬中复活,并通过枝条的移植,不断繁衍。它和黄金、水晶、宝石一样,是智慧和启蒙的象征。
公元前528年,乔答摩·悉达多王子正是在一株无花果树下证得菩提、获得真知的。因此,佛经中称无花果树为“觉树”。
无花果在佛教和基督教中均占有重要地位,在伊斯兰教中也一样。穆斯林既将它比作“长在树上的糖包子”,又把它敬为“天堂圣果”。
几个世纪以来,土耳其是世界上无花果产量位居第一位的国家。法国画家、建筑师勒·柯布西耶在《东方游记》中记录了上个世纪初君士坦丁堡的动人一幕:土耳其人喜欢在墓地里喝咖啡,而在墓地与咖啡馆之间,种了许多无花果树。“死者躺在无花果树的根底之间,而高大的无花果树的枝梢则像死者的灵魂,朝着天空伸展。当地的风俗,是让死者躺在活人中间,好让他们保持安宁。”
无花果出现在波斯细密画中,成为绘画风格的有机部分。伊斯兰教是反对偶像崇拜的,久而久之,图案和装饰艺术开始发达起来,渗透到精神生活和日常生活的各种细节中。就拿维吾尔族来说,无花果的“无限图案”直接体现在民居上,如门楣、窗框、廊柱、藻井、面砖、壁炉等。日常生活中,地毯、艾德莱斯绸、服饰、花帽、印花布、首饰、小刀、土陶等上面,更是少不了无花果精美的图案。无花果图案,是生活艺术化和艺术生活化的一个范例。
从阿图什、喀什到和田,沿昆仑山北麓,是新疆无花果的主产区。一些高龄的无花果树,因它们的历史感而在人们心目中有着很高的地位。和田县拉依喀乡有一株400多岁的无花果树王,占地1.5亩,绕着走一圈需花五六分钟,每年能结15000多个果子。在阿图什,我听说还有七八百年的无花果树,但拥有它的主人小心翼翼,秘不示人,连当地人都不清楚“树王”究竟长在谁家的果园里。但从他们向我描述时的诚恳语调和认真眼神中可以推测,“树王”的存在不只是一个传闻。
石榴:红英动日华
皮亚曼是个小地方,但它出产的石榴大名鼎鼎。
新疆的石榴,数南疆从喀什到和田一带的最好。而南疆的石榴,数皮山县的皮亚曼乡、叶城县的伯西热克乡和疏附县的伯什克然木乡三个地方的品质最佳,种植历史也最长。
皮亚曼位于和田和皮山之间,离两地均为90公里,是一个沙漠中的小绿洲。发源于昆仑山的几条小河汇聚到这里,使沙漠有了绿色、生机和人烟。由于特殊的土壤、气候和光热条件,皮亚曼一带是名副其实的“水果天堂”,葡萄、杏子、无花果、苹果等在和田地区很出名,更不要说石榴了。
正当六月,榴花似火,阳光漫过皮亚曼的村庄、果园、林间小路。人们称石榴花为“榴火”,十分形象生动。每年五六月间,皮亚曼的石榴树繁花怒放,红艳艳如同升腾的火焰。一株石榴树就是一个高举的“火把”,一片石榴树则是一片熊熊的“火海”。
皮亚曼的村庄就在石榴花的“火海”中。黄泥小屋,红柳篱笆墙,渠边高大的白桑树,迈着小碎步的毛驴拉着车上的柴火……
皮亚曼种植石榴已有数百年历史。
皮亚曼大规模种植石榴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现在,全乡的农民家家户户种石榴,少的三四亩,多者四五十亩,全乡共有两万亩耕地和两万亩石榴园。石榴种植业已成为乡里的支柱产业。
“石榴酒,葡萄浆,兰桂芳,茱萸香。”这是唐人眼中流光溢彩的丝绸之路,因为它添加了植物的芬芳和异彩。
石榴的原产地是古代波斯。后来,航海的腓尼基人将它传播到地中海地区。向东,则传播到布哈拉、塔什干、撒马尔罕等中亚地区。波斯人称石榴树是“太阳的圣树”,认为它是多子丰饶的象征。在日常生活中,他们用石榴做酱油,先把它浸在水里,用布过滤,使酱油有颜色和辣味。有时他们把石榴汁烧煮,请客时用来染饭,使饭的颜色漂亮,吃起来更加可口。
和葡萄、苜蓿一样,石榴是汉使张骞引进到中国的。从这一点上来说,张骞无疑是中国最早的“植物猎人”,当然,他承担的使命比这要多得多。李时珍说:“榴者,瘤也,丹实垂垂如赘榴也。”《博物志》云:“汉张骞出使西域,得涂林安石国榴种以归。故名安石榴。”
安石榴,确切地说是“安国和石国的榴”或“安石国的榴”。后来就简称为石榴了。安国和石国均为中亚小国,在历史上附属于康国。分别指的是现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布哈拉和塔什干两座城。
3世纪之前,中国古籍中对石榴尚无任何记载。石榴传到中国内地是在3世纪后半叶。4世纪诗人潘岳的《安石榴赋》是出自中国人之手的第一首“石榴赞美诗”。他写道:“若榴者。天下之奇树,五州之名果也。是以属文之士或叙而赋之。遥而望之,焕若隋珠耀重渊;详而察之,灼若列宿出云间。千房同膜,千子如一,御饥疗渴,解醒止醉。”
到唐宋,写石榴的诗章多起来了,李白、元稹、李商隐、杨万里等都写过与石榴有关的诗。唐代有一首无名氏的《燕京五月歌》:“石榴花发街欲焚,蟠枝屈朵皆崩云。千户万户买不尽,剩将儿女染红裙。”这是“石榴裙”和“拜倒在石榴裙下”的由来。
中国人把石榴叫做若榴、丹若、沃丹、金罂、天浆,都是十分好听的名字。我最喜欢“天浆”这一叫法,但这一称呼看来更适合石榴汁,芬芳甘甜的石榴汁正如“天浆”一样妙不可言,简直不是地上的汁液,而是天上的琼浆。
但汉地的土壤似乎不太适合石榴树的生长,它们大多变成了盆栽观赏植物,树身矮小,可怜兮兮,结的果子只有鸡蛋那么大。
当唯美成了病态的情趣,石榴的命运变了。只有在新疆,特别是在南疆阳光之地喀什、和田,石榴树长得生机勃勃,石榴花开得如火如荼,果实如婴儿的头颅,一只只天庭饱满,浑圆完美,最大的能达到一公斤多。
石榴在维吾尔语中叫“阿娜尔”。许多姑娘取名为“阿娜尔汗”(石榴姑娘)或“阿娜尔古丽”(石榴花),读起来有一种音乐和色彩的美感。当花朵和果实为人名所借用,就足以说明这种植物的深入人心,以及在这个民族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