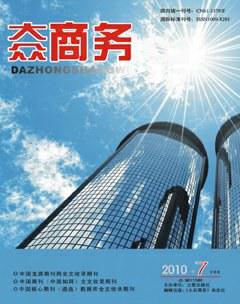剩余控制权的划分及其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陈瑞浦
【摘 要】在不完全契约(Grossman-Hart-Moore模型)的理论框架下, 企业的控制权来自于剩余控制权,而剩余控制权来源于物资资产的财产所有权。伴随企业组织形态多样化复杂化的发展趋势, GHM模型中古典意义的剩余控制权也呈现出更多的表现形式。根据剩余控制权的不同来源,本文将其细分为直接控制权和间接控制权两种形式。间接控制权及控制权 收益的普遍存在,使得公司治理理论关注的焦点从剩余控制权的有效配置转移到了剩余控制权的有效行使上,相应的公司治理实践也发生了变化。
【关键词】剩余控制权;不完全契约;GHM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83(2010)07-0105-02
1 前言
以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Oliver E. Williamson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用产权解释企业的性质及其边界,创立了资产专用性(纵向一体化)理论。该理论是由Williamson(1975,1985)和Klein(1978)等作了开拓性研究,又在Tirole(1986)、Grossman和Hart(1986)、Hart和Moore(1990)等人那里取得了进一步发展,其中最著名的是资产的专用性质确定企业规模的假说。由于他们强调按照契约建立起来的组织中权利的重要性,这一理论便以“产权”的名义出现。
Williamson用专用性资产来解释企业的边界或规模。他认为,当投入的资产具有专用性时,为了节约交易成本,应该选择企业这种组织形式或企业间实行纵向一体化,如果不存在资产的专用性,通过市场合约来联结生产的各个连续阶段,是可以大大节约交易成本的。沿着Coase(1988)的分析框架,这一问题可有两种解决方案:纵向一体化和长期合约缔结。他们的结论是,当资产的专用性产生越多的可占用性准租时,缔约成本的增加将超过纵向一体化的成本(治理内部科层组织的成本),那么,纵向一体化就发生了。在Klein等人的研究中,并不是专用性投资必须采用企业的形式,但是专用性投资的程度越高,采用企业的形式所费交易成本会越低。
GHM模型指出,企业是由它所拥有或控制的资产构成的。不完全契约的存在,使一部分资产的权利在合约中不能明确界定或界定成本相当高,形成所谓的剩余控制权,这种权利成为所有权的核心内容。GHM模型将注意力集中在分析比较各种所有权(剩余控制权)安排的效率差别上,按照GHM理论,资产所有权决定剩余权,在资产可分离的前提下,拥有更多的资产保证了拥有更多的剩余权。GHM模型在企业理论、融资理论、资本结构理论和企业治理理论等方面得到广泛地运用。
2剩余控制权的拓展
2.1 Aghion - Tirole( 1997)对剩余控制权概念的拓展及其不足
正因为意识到企业组织形态已经普遍偏离其古典形态,Aghion-Tirole(1997)对GHM的剩余控制权概念进行了拓展。他们将剩余控制权细分为正式权力(formal authority)和真实权力(real authority)两种形式,构造了一个组织内部正式权力与真实权力如何有效配置的理论。正式权力是指来源于财产所有权和正式授权的权力,真实权力则来源于代理人所享有的信息、技能等相对优势。正式权力并不必然带来真实权力。关于正式權力与真实权力的例子有:股东拥有正式权力,董事会拥有真实权力;董事会相对于经理层拥有正式权力,经理层拥有真实权力。
Aghion-Tirole从信息的角度理解权力及权力的配置,将剩余控制权细分为正式权力和真实权力。这种划分使我们得以进一步考虑组织内部的委托代理关系,考虑组织内部权力的不同配置和性质对组织绩效的影响,因而是对GHM模型的有力拓展。但他们对剩余控制权概念的拓展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在其模型中,正式权力和真实权力是一组相对的概念,任何一个层次的委托人相对其代理人来说,他所拥有的权力都是正式的,代理人拥有的权力都是真实的。权力不同形式的相对性使得正式权力和真实权力的来源显得混淆不清,因而也无法具体分析正式权力和真实权力的不同特性及其对权力行使的影响。事实上,正式权力、真实权力概念的不足恰恰在于其权力来源的不清晰。因此,本文引入“直接控制权”和“间接控制权”的概念,以更清晰地表明权力的不同来源,并基于剩余控制权的不同来源和表现形式讨论其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2.2 直接控制权与间接控制权
本文认为,从权力不同来源的角度看,存在以下几种形式的剩余控制权:一是直接来源于资产所有权的“直接控制权”。二是来源于企业内部的委托代理关系,或者说授权的“代理控制权”。三是通过诸如金字塔式持股结构、交叉持股等手段形成的“衍生控制权”。“代理控制权”和“衍生控制权”又可统称为“间接控制权”。“直接控制权”与“间接控制权”的性质根本不同:前者直接来源于财产所有权,是一种有足够的物质抵押品的控制权。后者则没有足够的物质抵押品,间接控制权不来源于物质资产的财产所有权。
关于直接控制权的现金流权的份额与控制权的份额是对等的,因此我们说这是一种有足够抵押品的控制权。该抵押品激励着控制权人事前正确行事。直接控制权更多地存在于古典型企业以及股权封闭的非公众企业中。在古典企业中,企业的资产由企业所有者个人拥有,他所拥有的直接控制权是完全的剩余控制权。在股权封闭的非公众企业中,直接控制权对应于一股一票原则,拥有最多投票权的股东最终拥有企业的剩余控制权。但是现代企业更多地以股权分散的公众企业形式存在。因此,企业的剩余控制权更多地以间接控制权的形式存在。在股权分散的公众企业中,大股东拥有的控制权是直接控制权,分散的小股东名义上拥有的控制权也是一种直接控制权。如果不考虑权力是否具有“剩余”的性质,我们可以更一般地将一股对应于一票产生的控制权叫做直接控制权。相应地,间接控制权是指偏离一股一票原则而产生的控制权,如一股多票,或者通过金字塔持股、交叉持股等复杂手段而产生的事实上的一股多票。如果没有相应的治理机制来约束这部分权力的行使,这种“赤裸”的权力被滥用是不难理解的。如果我们认同不完全合同中剩余控制权概念的“0-1”性质,那么间接控制权中没有相应抵押品的份额就更大,权力被滥用的危险也更大。将剩余控制权细分为直接控制权和间接控制权拓展了其应用范围,并使其能更好地解释因企业组织形态发展变化而产生的一系列现实问题。
此外,Aghion-Tirole强调信息、技能等客观优势对于真实权力的作用,认为代理人因具有信息和技能等方面的优势而具有了真实的权力,然后委托人考虑应该将权力授予代理人。但应该注意的是,信息优势产生权力的一个前提是代理人必须处在一定的职位上,例如经理必须处在经理的位置上才可能具有某些信息优势。也就是说,如果代理人没有委托人的授权而具有的身份,即使有信息优势也无权力可言,或者衍生控制权人如果没有获得控制权的手段或渠道,即使有一定的信息优势也无法获得这种权力。因此,强调剩余控制权的来源及其不同形式,对我们理解公司治理理论和实践关注焦点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3公司治理理论与实践的相应转变
Hart(1995)给出了公司治理问题存在的两个条件:一是代理问题,二是交易费用之大使得代理问题无法通过合约解决,或者说合同不完全。从权力来源的角度看,直接控制权不存在权力的代理问题,因而不会存在与权力行使相关的公司治理问题。
公司治理理论关注的仅仅是权力的有效配置问题。间接控制权通常通过一重甚至多重代理行为产生,公司治理不仅要关注权力的有效配置,更要关注权力的有效行使问题。
随着企业组织形态复杂化程度的加深,间接控制权的来源也更加复杂,公司治理理论需要关注的就不仅仅是如何最优地配置剩余权力,还需要考虑如何保证配置后的权力能够有效行使。公司治理研究的核心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是因为间接控制权上往往附着较高的控制权私人收益,这种私人收益对控制权人的行为激励产生扭曲作用,严重影响配置后权力的有效行使。在世界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公司治理的核心是解决控制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而控制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之所以会发生利益冲突,其根本原因在于控制性股东拥有的剩余控制权往往是一种没有足够抵押品的间接控制权,控制权人有强烈的攫取私人收益的动机,因而损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
企业组织形态的发展变化使得间接控制权(包括代理控制权和衍生控制权)的间接程度越来越大。相应地,公司治理实践更需要对间接控制权人进行约束而不是进一步的激励。间接控制权的间接程度越大,约束机制就显得越重要,激励机制的重要性则相对下降。历次经济危机包括当前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機再次说明了这一点,即约束不足是当前公司治理的主要问题。对此,公司治理实践可以从两方面展开:一是减少间接控制权的间接程度,即通过增加间接控制权抵押品价值的方式来抑制滥用权力的机会主义行为。现实中,诸如股权期权激励计划、许多国家对交叉持股行为的限制等,都是旨在减少间接控制权“间接程度”的重要公司治理手段。
げ慰嘉南:
[1] Aghion P.and J.Tirole.Formal and Real Authority in Organization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7, 105(1).
[2] Hart,O.Firms,Contracts, and Financial Structure.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3] La Porta,R.Lopez-de-Silanes,F.and Shleifer, A. Corporate ownership around the world[J].Journal of Finance,1999,54(3).
[4] Williamson,O.Markets and Hierarchies: 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 New York: Free Press,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