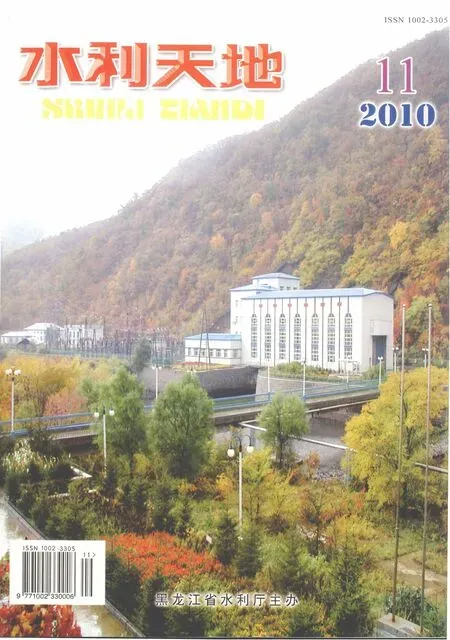倭肯河:骄傲与亮色
□ 范震威
倭肯河文明的曙光
带着下一本书的构想上路,昨夜睡得很浅,若干待写的事件逐渐浮现于心中的镜头,迷蒙中似睡似醒。不知何时,响起了风声雨声,在车窗上哗哗地闹腾了一阵后,方才辞去,只剩下絮絮叨叨的车轮与铁轨的叩击声,没完没了地在耳畔骚扰。天刚放亮,我便醒了,看了一眼地图,火车已经告别林口站,不久就将进入勃利县——七台河的界域了。
晨光从右侧的车窗中映进来,铁路两侧的苞米地和稻田交替地变换着,带着盈盈的秋色的希望,在田野上铺展,也扑入我的脸睑,激起一腔兴奋。坐在对座的画家老郑一边赞美窗外的景色,一边对我说:“诗情画意,画意诗情,真的美不胜收啊!”说着说着,列车已进入勃利县境了。勃利是七台河市所管辖的唯一的县。40多年以前,当七台河的煤还没有开采的时候,这片土地由勃利县所辖。1970年在文化大革命中,七台河由于煤田的开采而一跃先成为特区,后来又成为一个新兴的城市,勃利县却反过来从属于七台河市了——季羡林先生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里面的朴素的辩证法的关系,不仅反映了自然的变迁,也反映了社会人文的变迁。世上的许多事都是难以预料的,七台河市的诞生与崛起如此,比它略晚的广东深圳市的诞生与崛起也是如此。只不过,各有各的不同情况与条件而已。
火车在奔驰,嘈杂的旅客声从沉睡中泛起,车轮与铁轨的叩击声变得混浊了,不那么刺耳,也不那么令人心烦了。我还是在凝望晨光沐浴的波纹,那是倭肯河左岸支流碾子河向东北方流去,在下游它和另一条名叫五站河的小河相汇,然后注入倭肯河。现在,列车行进在倭肯河流域的怀抱里,感受的是母亲河的温馨。
枕着碾子河右岸的勃利县,为民国七年(1918)所设,原来它是一个人口略多的小镇。建县以后,人口逐渐多了起来。勃利为满语,意为吉祥幸福,另一说为豌豆或弓。勃利——伯力,原本是黑水靺鞨的一个部落名,后来几经迁徙演变,一部分南迁,来到倭肯河流域,才把勃利——伯力的名字也带来了。黑水部的核心地域在三江北部,即今乌苏里江与黑龙江交汇处的右岸,原名即叫伯力(勃利),沙俄于19世纪下半叶强占之后,于1880年先在伯力建了哨所,后设一俄人村庄,称哈巴罗夫卡,但在中国的地图上叫伯力(《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唐代时为黑水都督府之勃利州,故可以说勃利与伯力是同音异写)……如今,那里因为是水陆空枢纽而极度扩展成为一个大都市了。但它和倭肯河边的勃利县,仍然可以视之为辉耀过远东或东北地域的一个双子星座,只是经历了太多的沧桑变迁,物异人非罢了。
勃利——伯力,在历史上有时也记作布里、波力、勃力,总之它源起于松、黑、乌及三江地区的原生民肃慎,黑水部族就是肃慎人的后裔,也是女真、满洲人的先民。由此可见,勃利县虽小,历史却十分悠久。
崛起于倭肯河岸的煤城也在发展雄峙中,在这块由松花江支流倭肯河养育的土地上,它们还是有雄厚的历史文化的渊源的。只是,许多不可预见的历史因素执意地来打扰它——如19世纪五六十年代沙俄的强占,嗣后其对东北土地的垂涎,以及1931年代日本帝国主义的占领与蹂躏。如果没有这样的外来因素,历史一定会改写,倭肯河——勃利和七台河的历史也会改写,只是历史无法假设,一切存在都是诸因素共同演化的结果,许多事后的遗憾,只能是遗憾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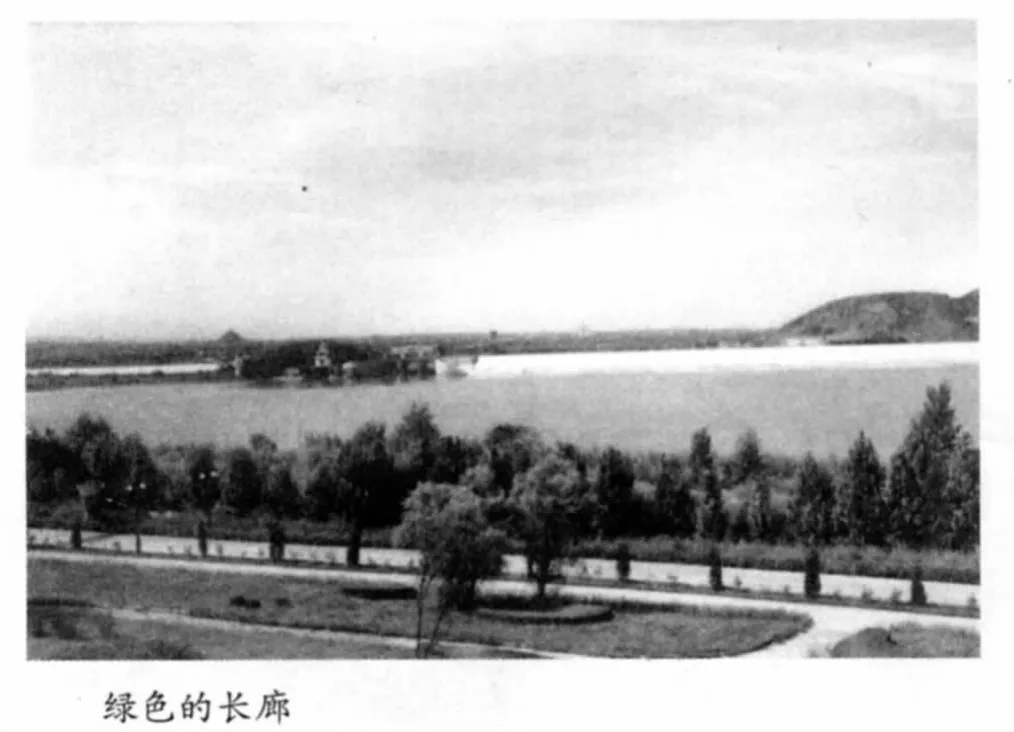
起身活动一下,去了洗手间回来,车厢里人声嘈嚷和车轮铁轨的叩击声混杂在一起,在咣当咣当节奏声的伴奏下,车窗外示出的是沿途的风景:太阳已经露出地平线,阳光照在田野大地和村庄,也照在河畔的草地和公路,更照进车厢中,有人在喝果汁,有人在喝啤酒;有人在刷牙,有人在刷鞋;有人在谈话,有人在谈诗;有人在呼叫孩子,有人在呼叫老公;有人在看小桌上的杂志,有人在看窗外的风景;有人在扯拉窗纱,也有人在扯淡闲聊……这是一个纷纭杂陈的世界,这是一个仿若物理学中没有一定规律的布朗运动的图景……中铺上谁的手机响了,是一支西藏歌曲《卓嘎在歌唱》的彩铃,那是藏族名歌手贡尕达哇雄浑的男高音:
当房顶升起的蓝烟把村庄唤醒
当太阳给碧绿的水塘镀金
一首古老的歌谣越过河谷传来
是谁哦,是谁是谁在歌唱……
手机被接听了,歌声戛然而止,而另一种无声的在旷野上流淌于河流青山间的古老的歌谣,却借着晨风晨露裹馥的草香传进我的耳畔。那或许是飘浮在倭肯河谷上的天籁之音,带着久远的岁月的包容与回响和今天的绿色的祈愿与祝福,一并地显现了……
倭肯河的土地,在20世纪初一度是荒凉的,可在遥远的古代,这里并不那么空旷寂寞。是的,我想起来了,倭肯河流域文明的曙色,美丽而灿烂。如今,被人们发现并引以为自豪并开发为当地的旅游景点的地方,已经有了多处……
在倭肯河左岸倭肯镇以东的平安村,在一片现今的耕地上,在距今4 000年前,发现了包括南北沙包在内的两处原始社会遗址。遗址的总面积有50万平方米,其表层厚度为11厘米,自上而下依次为厚度达23厘米的木炭层和厚度为20厘米的黑灰色熟土层,以及深度为11厘米的红烧土。当时的人使用火与木炭的痕迹十分明显。
这是一处肃慎族人的居地。肃慎(也写作息慎)族人在公元前2231年时,曾应召派人到中原参加帝舜二十五年的一次朝贡活动,并向中央王朝舜帝贡奉了弓矢,也就是弓箭。帝舜二十五年换算成公元前的年代,有几种说法,这里引用的公元前2231年,是笔者依据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陈芳芝先生给出的年代推算出来的,而且已应用于拙著《松花江传》中(参见陈芳芝《东北史探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6页)。由此推之,肃慎即息慎人向中原舜帝贡奉弓矢的年代,恰与发现于倭肯河左岸的平安原始社会遗址形成鲜明的历史对应。平安原始社会遗址出土的器物有石刀、野猪牙、木化石和手制陶器及其他石器等。平安原始社会遗址位于倭肯河中游左岸,这里也是山地边缘的低丘陵漫岗区,恰是原始人渔猎采撷生活的理想的选址,一块厚达23厘米的木炭层和20厘米厚的黑灰色熟土层,表明了原始社会生活在倭肯河左岸的这支肃慎族人,在这里居住的时间并不暂短。然而,正像所有的原始社会遗址所表现的一样,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以后又到哪里去了——这样无法解答的历史之谜,也同样困惑今天的人们。在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朝代,许多历史之谜都未能解开。像绥滨县同仁原始社会遗址,友谊县的挹娄时代(比肃慎人稍晚)七星河左岸的凤林古城遗址,密山兴凯湖岗新开流遗址等,当年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从何处来,以后又到何处去了,都无法回答,也无法诠释。然而,只要这些遗址存在就足够了,也就足以描绘出其所住之河流域文明的曙色了。
果然,从亘古荒原倭肯河畔飘出的是一支古老的歌,一支从4 000年前或更早更久远时发出的歌,至今它不仅是这片土地上的骄傲,也是这条几乎不怎么被人关注的倭肯河亘古以来的第一道文明的亮色。
倭肯河的记忆
第一次走近倭肯河是2002年夏天。
那时,我刚辞去了在一家报社当记者的工作,专心走访松花江沿途各地,为撰写《松花江传》而奔忙。当时是写出一个段落,休息一下,乃去下一个我所关注的地方进行田野考察。是年夏天,我来到依兰,看了宋金时代著名的五国头城及徽、钦二帝“坐井观天”的可能的旧址——所谓“坐井观天”,是指徽、钦二帝坐在一个被囚禁的院落的天井里,只可看院落中所见的一片方形的蓝天,而不是我孩提时代所看的小人书里画的,宋徽宗坐在一座干涸的井底,只身仰望天空那么可怜。其实,公元1127年完颜氏的金源帝国将宋徽宗赵佶虏押到松花江右岸的依兰时,宋徽宗当年才46虚岁,他的儿子宋钦宗才28虚岁。宋徽宗在依兰五国城生活了8年,金人允许他带来了除郑皇后之外,还有乔贵妃、崔淑妃、王贵妃、韦贤妃等4位妃子,8年中除了一子生于“北狩”——来五国城的途中,一子生于韩州外,还有4个儿子生于五国城。宋徽宗的长子宋钦宗赵桓到依兰五国头城时,随之而来的除朱皇后外,还带了一位朱慎德妃,以及郑氏和狄氏两位夫人。宋钦宗终年62虚岁。在来北地的途中,除朱慎德妃在燕山途中生了一个儿子外,又由郑夫人与狄夫人在韩州先后生下一子一女,后来狄夫人于金熙宗天会十年(1134),在五国头城又生下一个女儿。以上这些情况,或许可以说是徽、钦二帝被囚禁于一个院落中生活情景的某种旁证。五国头城坐落在牡丹江注入松花江河口下游右岸,同时也是倭肯河注入松花江河口上游左岸,依兰五国头城正夹在此二河口之间,这段历史轶事,既是松花江右岸的历史风景,也是牡丹江河口与倭肯河河口的历史风景。

宋徽宗顶着亡国之君的帽子死在北地,可他作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画家、书法家,却光环长存。崇宁三年,亦即1104年,25岁的他下令成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宫廷画院——翰林书画院,他成为当时艺术的领军人物,并以瘦金体书法独步天下。2009年,他的一幅“珍禽画”在保利以6 172万元的高价拍出,说明历史与岁月对他艺术造诣的认同。宋徽宗死于五国头城,正应了一句调侃的话:松江无意伴画骨,倭肯有幸照书魂。他死后两年,死讯传到杭州,又过五年他的梓宫才运回江南。这段历史上浸透了屈辱与遗恨的血泪故事,却使倭肯河口成为机缘的见证,风景的参照。
这幅历史风景,也可以从宋徽宗留下的一首七绝《清明日作》中看出某些真况来。诗云:
茸母初生认禁烟,
无家对景倍凄然。
帝城春色谁为主?
遥指乡关涕泪涟。
茸母即鼠鼠匊草,在北宋东京汴梁的宫中草地上也可以见到。由茸母草想到今日是清明——寒食节,而寒食节是禁烟的。由草想到寒食,又想到昔日宫中的奢华,却不知那里如今何种模样了,所以挥指乡关之际,宋徽宗只有痛哭。
痛哭无济于事,只能加重痛苦。囚禁中的宋钦宗的笔下,多少还能略有反思,且见他的《西江月》词云:
历代恢文偃武,
四方晏粲无虞。
奸臣遭致北匈奴,
边境年年侵辱。
一旦金汤失守,
万邦不救銮舆。
我今父子在穹庐,
壮士忠臣何处?
这种坐井观天、仰天长叹的悲悯,只能响彻在北地松花江、倭肯河与牡丹江,以及北岸注入的巴兰河的旷野中,因为苟且偷安的南宋小朝廷廷主宋高宗赵构不想去救援。赵构心中明白,一旦父兄回归,他赵构的龙榻必将难保。所以,他坚持不向金人索取父兄。宋朝赵家家天下的弊端,由此亦可见一斑。后来,宋钦宗咽下眼泪,收起悲痛,以平常之心对待囚禁——只好听天由命,顺其自然吧!变得木呐后的宋钦宗虽盼望弟弟赵构救他回去,却也能安然度日,竟活了62虚岁。虚度虽曰虚度,却也阅尽不少人间的冷热炎凉。
这样的风景也给倭肯河下游之水浸透了历史的悲怆。
然而,倭肯河并非没有过自己的文明与骄傲,前文中游左岸下安村原始社会遗址就是一例。而1950年4月,在倭肯河口附近发现的倭肯哈达洞穴中,发现了古人类遗骨5具,均呈双肩抱膝蹲坐式,以及大量的骨器、石器、陶器和玉器等文物。经测,为距今6 0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的遗存,和新开流人的年代相同。倭肯哈达洞穴位于倭肯河下游河畔的哈达山腰上,洞高2米,天然北壁断掉了一部分,洞深约10.2米,洞底原有石板,早被拆去。洞呈方筒形,其出土之遗物如石器、陶片等,同西伯利亚、内蒙古东部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物相类。洞穴在倭肯河下游右岸,是一个依山临水适于游徙渔猎生活的新石器时代人的较理想的住地。有人推测,5具人尸可能为大水所困饥饿死亡者,也有人推测是一处墓地——早年的居址被放弃后,成为墓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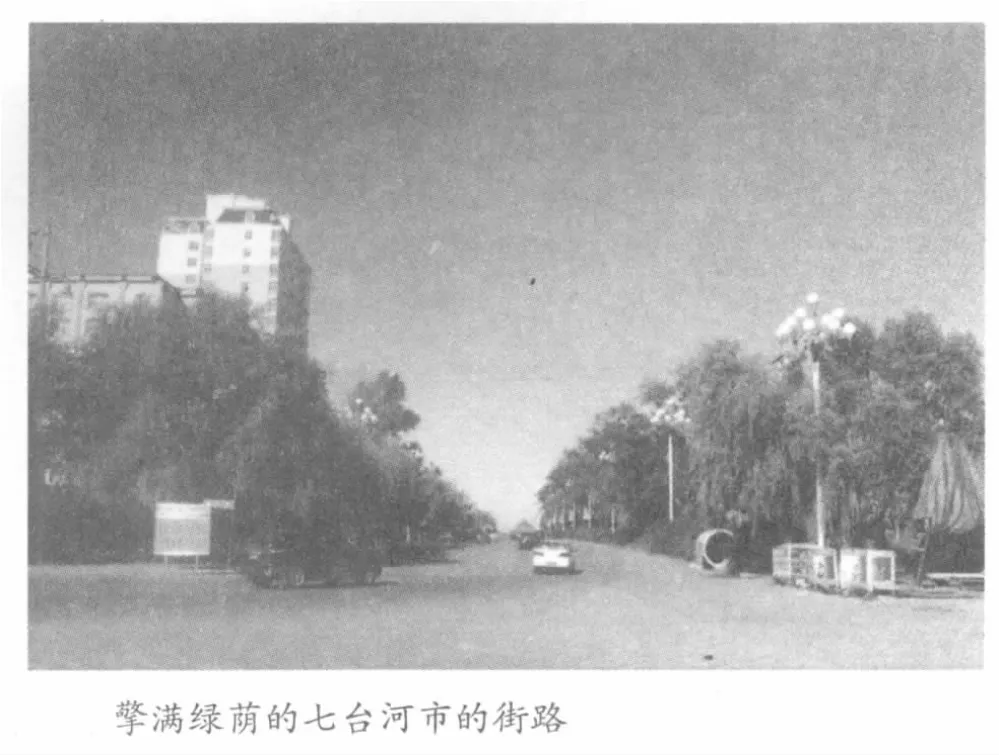
居于倭肯河下游右岸的哈达山新石器时代的古人类,是顺松花江下游进入西伯利亚了呢?抑或是溯松花江而上,到达嫩江进入内蒙古东部?反之,亦或是中原来的与红山文化同宗的人北上,并从那里沿松花江流域,来到她的各个支流之间,成为松花江母亲河的子民。久远的岁月,难以破解,一阵阵清风吹来,诉说的是一卷读不透的故事。
然而,这故事的余波仍可以从倭肯河的岁月中打捞,从她的身边拾起。
首先是倭肯河右岸,坐落在勃利县长兴乡倭肯河支流柳毛河左岸的马鞍山古城址,这里紧贴柳毛河畔,距河上游的柳毛河水库仅两三百米,东南距马鞍村也不过0.5公里。柳毛河从北边的大驾山流来,山地距城址约2公里。城址发现于1983年,由4个分布于小山顶上的小城组成,实际是一组古城群。城墙高3米,厚1米多,外城周长约300米,内城周长为240米。四座城的总面积为38 000平方米,规模十分了得。据测定为战国时期所筑,距今大约2 500余年,比七星河畔的凤林古城早数百年。出土文物有大陶罐、小陶罐及陶簸箕、石网坠、石磨棒等,说明彼时倭肯河右岸古城的居民,过着渔猎、早期农业和自然采撷的生活,显然比当时中原人的文明晚了许多。
其次,在倭肯河左岸地方,于勃利县双河镇东南新发村,距村约0.5公里的一个土岗上,发现一土石建筑城址,因年代久远,这里已辟为耕地。据测定,古城为秦汉时期遗址。此城址比上述马鞍山古城址要晚,仍比七星河凤林古城要早。城址北端连接一道东南西北走向的小岭,山缓林密,是彼时比较理想的猎取野猪之地。城址总面积为4 000平方米,遗址文化层相当厚,该地表层沙土中含有大量的陶器残片。
这两处古城址,据学者认定,均是满族——女真人先祖肃慎人的居地。彼时,肃慎人同中原已有较密切的往来,从《竹书纪年》开始,这种往来一直不断,在司马迁的《史记》之《五帝本纪》、《周本记》、《孔子世家》,以及《大载记·少闲篇》、《周书·王会篇》、《左传·昭公九年》、《国语·鲁语》、《说苑》、《孔子家语》等文献中,均有关于肃慎(或息慎)的记载。而《山海经·大荒北经》的记载最为清晰:“大荒之中,有山名不咸,有肃慎氏之国。”《史记正义》引唐《括地志》说:“靺鞨,古肃慎也,其国南有白山。”不咸山、白山即今天的长白山,说明古时肃慎人主要分布在今牡丹江及三江平原诸地,当然也包括居于二者之间的倭肯河流域了。
勃利县倭肯河流域中,在马鞍大队(马鞍村)果园和勃利县农牧场的防波堤上,均有金代的历史文物出土,如铁箭头、铁鱼镩、铁铲、锄刀钉、钻头、凿子、镰刀、剪刀、马具、雕刻石佩、石纺轮、铜手镯、铜镜、铜钱、鱼叉和大扑刀等。金代为女真人完颜氏所建。《大金国志》说:“金国本名珠里真,后讹为女真,或曰虑真。”清代《满洲源流考》说:“北音读肃为须,须朱同韵;里真二字,(连起来)合呼之音近慎。盖即肃慎转音。国初旧称所属珠申,亦即肃慎转音也。”由此说来,贯穿七台河市的倭肯河中游的三处遗址:平安原始社会遗址、马鞍山古城址、新发古城址,作为古时肃慎人的居住地及其遗迹文物等,和中国的正史记载完全一致,这不仅说明了倭肯河流域作为肃慎人早期的母亲河,十分悠远,它也是亘古荒原(大荒之中)上较早为肃慎人开发的若干松花江支流中的一支。平安原始社会遗址距今为4 000年,正是周初时期,彼时也有肃慎(息慎) 人进入中原参加成周大会的记载!从而说明了肃慎人所生活的不咸山以北地域——包括松、黑、乌三江及其支流地域和中原黄河地域神脉相通。不管你怎么看,他们本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部分,早就拥有共同的文化与文明了。
走近倭肯河
倭肯河的名字,对于普通人来说,也许让人感到陌生。从汉字的表音、表义来说,“倭肯”二字真是不知所云,也不知是什么涵义,但却有一种神秘的,也可以说像朦胧诗一样的历史美感。然而,这就对了。请不要忘记,倭肯河流域是松花江流域的一部分。这里本是: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满洲等,一脉相承下来的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的居地,故而在这块清代称为满洲或龙兴之地的地域上,它的许多地名都和这个民族的语言有关,如今留下来的,写在地图上的山名、河名和地名,也多半同上述的历史因缘有关。
当笔者走近倭肯河,站在倭肯河右岸的一处谷地上眺望倭肯河粼粼的波光,追怀她的历史变迁,也翻检同倭肯河有关的参考文献时,终于揭示了“倭肯河”这一河名的神秘面纱,了解了她的真正的美丽,恰在于历史风云在倭肯河上空飘逸而去后,为之留下的最本真的面容。
可是,关于倭肯河名,主要有三种说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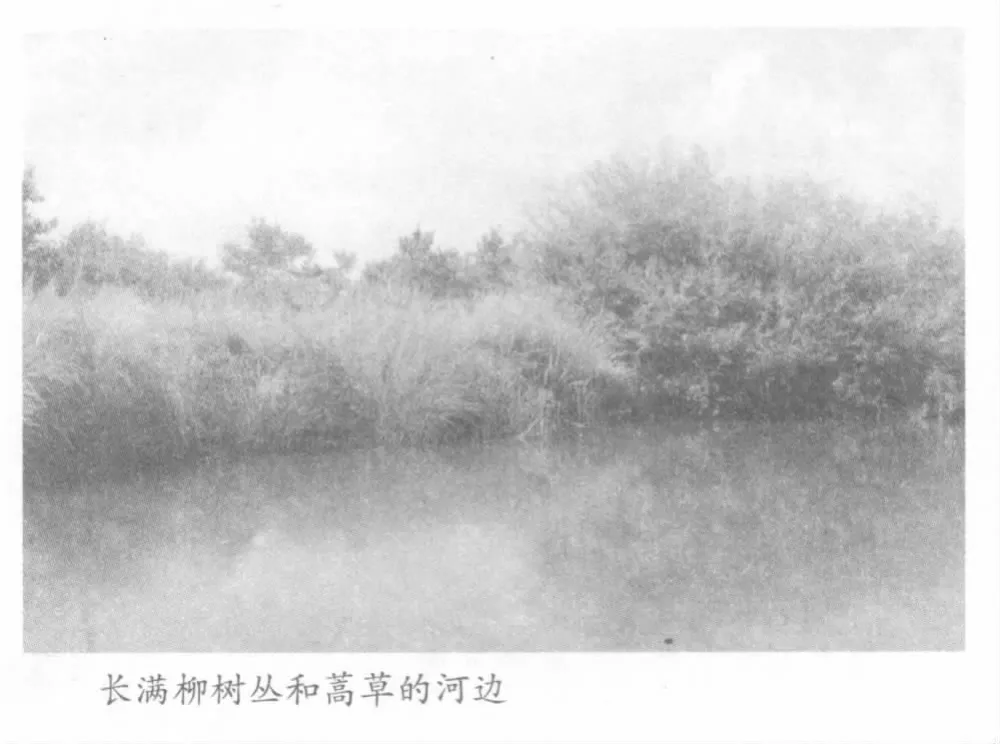
说法一,《黑龙江省志·地理志》说:“倭肯河为松花江中游右岸大支流之一。辽代时称仆干水、布尔噶水,明代时称呕罕河,《(伪)满洲国水道源流考略》称倭坑河、倭和江。‘仆干’、‘布尔噶’、‘倭肯’,均为满语,即‘柳条河之意’。”——由此可见,倭肯河名出自满语,其汉文之意为柳条河。换言之,倭肯河流域柳毛丛或柳树极多,故以其柳多的特征取为河名。笔者前面提到马鞍山古城址时说,古城址靠近倭肯河右岸支流柳毛河,可知柳毛河岸边正因长满了柳毛丛而得名。夫北地河岸之柳,因临水而遇旱涝更替,难以长成较大较壮的柳树,灌木丛形态的柳树丛,俗称柳毛丛,水壮冲倒甚至冲走也不怕,停在那里即可复壮而生,故有护岸护土的作用在焉。柳毛河虽为倭肯河支流,却可以为倭肯河名之取意为“柳条河”作一旁证。
说法二,1931年5月出版的、由臧励和等所编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倭肯河条》说:“倭肯河,一名海伦河,亦名倭和江,又作倭坑河。源出吉林宝清县七星折子。西南流经桦川县入依兰县,折西北流,合支河数十至县城北,入松花江,隔江与巴兰河相对,成十字形。”根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清时期》图示,倭肯河地域为吉林省所辖,其河标注为“翁锦河”,为《黑龙江省志·地理志》及《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所不载。但“翁锦河”一称,到底是倭肯河的别写,抑或是倭肯河一称“海伦河”之名的别写,似可两存。而倭肯河一称海伦河的说法,其中也另有含义在焉。海伦一词,据《黑龙江省地图册》 (黑龙江省测绘局,1980年版之内部用图)在诠释海伦县地名时说:“海伦系‘开凌’的转音,满语意思是水獭,因县城附近有一小河多水獭而得名。”因水獭得名的地方甚多,如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呼伦湖”之名,其意即水獭——呼伦与海伦之音互转。“贝尔湖”的名字,含义是“雄水獭”(参见《呼伦贝尔盟志·附录》)。蒙语称水獭为“哈溜”。“哈溜”也是满语“海伦”的音转,故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有一乡镇称“呼伦苏木”,呼伦也是海伦的音转,苏木为蒙语乡镇之称。由以上的情况可以推知,早年在倭肯河一名海伦河时,应是以其河域多水獭而闻名的。
说法三,据《七台河志·河流》说:“倭肯河,20世纪20年代有几家渔民,在河岸搭窝棚居住,故取名窝棚河,后改名为倭肯河。”
查倭肯河上游由两条小河汇合而成,主源出七星折子,在勃利县东北与宝清县交界地,此界即七星河与倭肯河之分水岭。主源流至北兴农场一分部附近,与源自元宝山中的正阳川河相汇,相汇后称倭肯河,由东北向西南流。在北兴农场总部西北,右岸汇入一支流窝棚河。说法三中的窝棚河,至今还在,它只是倭肯河右岸的一条支流,支流不是主流,看来用支流名衍化成为主流名这种说法,似乎待商量。其河名源自20世纪20年代,显然也太晚了。从窝棚河再下,右岸又汇入大金沙河。汇入金沙河后的倭肯河,于1958年在桃山附近筑坝截流形成桃山水库。水库于1983年扩建修竣,库容为2.6亿立方米,如今是七台河这座闻名遐迩的煤城的生活用水和工业用水的水源,也是一处最佳的风景。桃山水库拦河坝以下,右岸又汇入挖金别河、柳毛河、罗泉河等,之后倭肯河成为勃利县与桦南县的分界,又成为桦南与依兰县的分界,在这里右岸又注入七虎林河、八虎林河(此河清代称巴和里河)和松木河。在松木河口以下,倭肯河进入依兰县境,然后又纳入几条小河,最后在依兰县北部注入松花江右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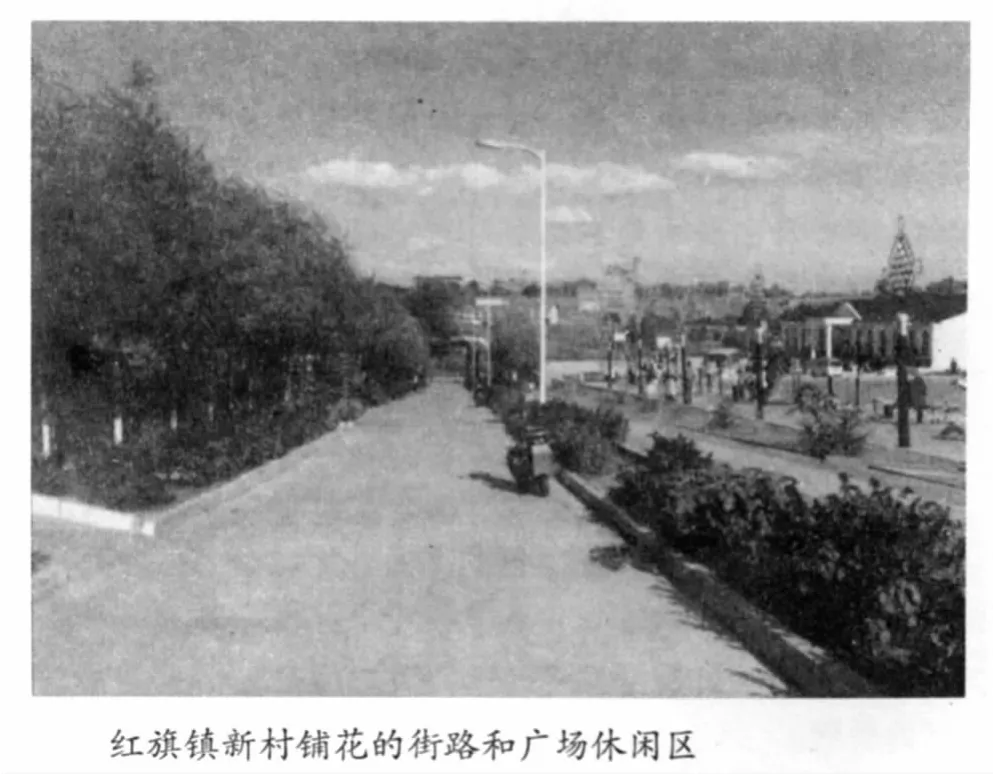
倭肯河左岸,上游几乎没有支流注入。桃山水库北端可为倭肯河中游起始,左岸先后纳入龙湖河、中心河、大茄子河等三条支流,此三条河下游还有一与倭肯河相平行的灌渠,叫更生自流灌区干渠,这里也是七台河水田与蔬菜的主产区。以下为七台河,也称奇塔河,亦是这座煤城名字的来源。奇塔河名,源自鄂伦春语,意为薪屋。奇塔河——七台河,在七台河火车站之北注入倭肯河,因而七台河下游在煤城市区穿过,它和从市区穿过的倭肯河主河编织出水陆相间的煤城风景。在建市之初,当年的理念是“先生产,后生活”,连职工的住房都相当简陋,更不要说对河流、对河岸的治理了。许多治河与美化河岸的理念,在20世纪末才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这10年,七台河以其惊人的速度在发生巨变,倭肯河与七台河,正在向美化的方向迈进。自七台河口以下,倭肯河左岸先后注入五站河、碾子河与杏树沟三条河的合流,再下左岸又注入连珠河——上游称玄举河,然后是吉兴河、双河、二道河、头道河——后者今日与倭肯河已不相连,在这三条河的下游,另有倭肯河的一支岔流与之沟通,从而形成了倭肯河中游的复杂河道。在进入依兰县与桦南县的界河段,这段岔流中部有一座安兴水库(其水库旁有一安兴村,位于水库与倭肯河之间),水库和三合排灌渠相连。自此以下,以及下游的倭肯河,左岸再无支流注入,一直流入松花江中。
倭肯河长450公里,在松花江干流诸支流中,次于牡丹江(长726公里)、呼兰河(长523公里)、汤旺河(长509公里),以其长度仅比拉林河(长448公里) 长2公里的优势名列第四。
……当我还徜徉在关于松花江及其支流的忆想时,列车终于正点驶至终点站——七台河。铁轨与车轮的叩击声停了下来,一声长鸣的汽笛在清晨的空旷里长嘶而散去。在接站的热烈气氛中,我和文友们一起认识了七台河的一些朋友,他们不是别人,恰是为倭肯河,也为七台河煤城的崛起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创业者们。
倭肯河的骄傲
倭肯河的骄傲,在于他以母亲河的身分养育了三个不同古迹上生活的子民。查看周围的地域,除了友谊县七星河凤林古城、七星祭坛外,还看不出可以与之比肩者。倭肯河中游两处古城址附近均有铁质器物出土。据《金史·世纪》记载,在完颜氏还没有强大崛起时,女真人手中极度缺铁,甚至无铁,后来完颜阿骨打为了强大自己的部族,才在各种贸易中换回了铁。铁的输入强大了女真的部族。所以,在倭肯河流域——当时称生女真的地区才有了铁的广泛应用。由铁器即可以断定,这是金源帝国强大之后的事。如是,人们可以说,倭肯河口的哈达洞穴、平安原始社会遗址和马鞍山、新发两处古城址,它们不仅是倭肯河流域文明中的亮点,也是倭肯河的骄傲。
然而,这些亮点与骄傲毕竟属于历史了。今天,在倭肯河流域,同样也有她做为母亲河的新的亮点与骄傲。这骄傲与煤有关。1910年(宣统二年),发现了勃利煤田。两年后,已进入民国二年(1913),便有人在七台河地区的安乐、茄子河两岸采煤出售。1930年——据《七台河市志》记述说,当时这里称勃利县的官方,为征集工业原料进行域内调查,发现小五站有原煤储量约580万吨。嗣后,日本侵占东北,日本人也曾在这里搞过调查。1935年出版的《宝清县志》记载说,本县山区土山、桃山、徐马架、茄子河等处有许多烟煤。1940年,日本人左木清水在大六站投资创建小煤窑。1947年的《勃利县志》中说,“本县矿产为煤,最富,现已发现大四站之连珠河沟里,七台河至桃山、大六站等数处,煤质良好。”这些,都是七台河建市以前关于当地有煤的零星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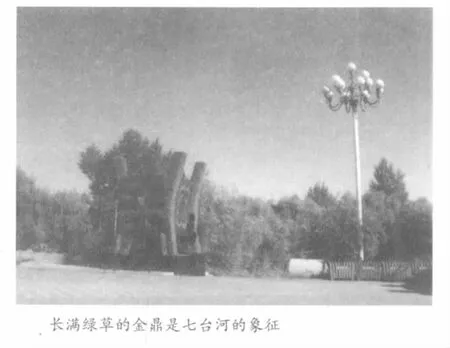
七台河市做为倭肯河的亮点与骄傲,开始于新中国时代,1956年在此开展的一次煤田调查。那次调查历时两个多月,据后来的报告所记,该区含煤有60层,大于0.6米厚的有25层,并初步确定为气煤和焦煤,当时远景评估为8亿吨——今日确定的约30亿吨以上。于是,这年年末,冒着严寒大雪即开始了煤的钻探。1958年2月,在全国大跃进的鼓点声中,七台河的煤田建设拉开了序幕——这一幕留给历史的是,煤矿工人住着地窨子(地窨子本是肃慎人过冬时所居之简露的穴居之地,人们挖坑于地下一两米深,上边搭上树枝与草,再覆以土层将之压住,内中生一火炉,烟囱支在外顶。这种古名穴居,今名地窨子的建筑,在三江流域十分普遍,因为有冬暖夏凉的自然变化,居住虽陋,因易于修建,至今不绝),吃着咸菜和窝窝头,在冬季刺骨的寒风和夏秋——黑龙江三大宝:蚊子、瞎蠓和小咬的袭击下,艰苦创业。这里煤层太薄,有的地段便需匍匐着行进……
辉煌就是在极为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由七台河人以无畏的奉献的精神换取的。当年,映照过创业初期简陋的地窨子与茅草房身影的倭肯河,如今映出的是鳞次栉比的楼群、开发区,以及设施相当完善的配套工程大手笔的合理布局。笔者在中共新兴区委宣传部张云凤部长等多位朋友的陪同下,观看了如今七台河市的许多让人看了眼睛一热的亮点、热点和转型区的经济试点。
七台河是国家循环经济试点市,也是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试点市,一切都围绕着煤——这种一次性资源开发利用和矿竭之后的长远目标制定规划,付诸实施。七台河市的核心地区是新兴区,它也是七台河市最大的一个辖区,人口30万,占全市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由于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2009年全区GDP实现44亿元,几近在2007年基础上翻了一番。新兴区坐落在绿岭秀美的五台山下,旖旎的波光潋滟的倭肯河从区中穿过,映出一片光影,勾画出一道煤城工业如画的长廊。如今,他们在走一条依托煤炭、延伸煤炭、超越煤炭的科学发展之路,随着宝泰隆98万吨焦化、10万吨煤焦油加氢,10万吨甲醇,万昌5万吨苯加氢,乾丰98万吨焦化一期等一批大型项目的建成投产,以及其他如双叶木业等六大产业的雄起,新兴区在全省4座煤城的19个区中,已领先了——这种领先,人们从城市前进步伐的热浪中和统一规划的住宅开发中能够感受得到。在浏览观看到这一切之后,笔者也由此而感奋而激越,同行中许多诗人的诗情也被点燃。
七台河市的另一个亮点是桃山水库,水库中的人工湖在原倭肯河上游河道上筑拦河坝而成。如今湖映蓝天,白云轻浮,远山近树,鹰鸽飞翔,竟是一片山川竞秀、游人依恋的所在。七台河市,在全国数千座市县中似乎极为平常普通,几乎默默无闻。可是,随着改革开放的经济振兴,除了它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外,如今让全世界瞩目的,则是从七台河、从倭肯河母亲河的臂弯中走出的像杨杨、王 、刘秋红等中国最优秀的一批冰上短道速滑选手和世界冠军。倭肯河这条不起眼的当年的柳条河,竟然成为世界冠军的摇篮!这是倭肯河母亲河的又一种骄傲和亮色!

七台河、倭肯河由此而闻名世界!
在城乡一体化方面,七台河市,尤其是新兴区走在前列。在七桦路北侧的工地上,东升村、曙光村的村民改居工程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这是在一块基本无人居住的荒地上的楼群崛起,两个村760户村民从棚户区改造工程中获得实惠,通过拆迁将会入住七星花园小区……另有红旗镇新村,通过对上争取资金改造了66栋民宅,户户入新居,条条展新路,村中修起了广场,安装了健身器,设置了俱乐部、图书馆……当笔者徜徉在新居的路上,看到几辆摩托车停在路旁,农民家居的门口,擎起绿荫的山葡萄藤系着累累果实的拱形架,一两株果树悬着红太平果,和树下的尖辣椒、西红柿相映成趣。屋内宽敞,阳光普照……古时的穴居、早年的窝棚、茅屋,都融进了历史,抗日游击队时代和煤城创业时的地窨子之类也向博物馆走去,代之而来的是幢幢新居和群群耸立的楼厦。中国人两千多年前有一种期愿:“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如今这期愿正在一步步地演化成眼前都市生活底线和谐社会的现实。故而,笔者如今走在倭肯河中游,也就是七台河市各地,新兴区、桃山区、茄子河区……看到他们正前进在最具希望的北国大地和田野上,从城市到乡村,都可以用“美景如画”四个字来描述。
在这样一篇以写松花江右岸支流倭肯河流域变迁,写她的岁月、梦想与现实的交际中,笔者不可能面面俱到地将一切新貌写尽写透。但走在七台河特别是新兴区的土地上,在休闲区的留连忘返中,笔者突然涌来一股诗情,乃口占一首名为《倭肯河》的打油诗,录之如下:
欲访七台两金城,
问后方知遗址空。
谢对江山犹感慨,
敬予煤城亮新容。
桃园频祝高杯酒,
湖畔轻吟小采风。
久慕倭肯河间地,
漫话新兴寄友朋。
吟哦之中,俯仰回忆,一阵小风从窗外吹来,秋日的馨香中又浮现出七台河桃山水库蓝绿相间的两岸风光,那真叫一个字: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