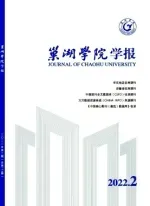唐诗中的“罗衣”及其文化意蕴
曾艳红
(广西师范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0)
唐诗中的“罗衣”及其文化意蕴
曾艳红
(广西师范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0)
“罗衣”是唐诗中经常伴随着女性形象而出现的一个审美意象。在唐代现实生活中,“罗衣”是指女性所穿着的丝绸上衣,它包括衫、襦、裆、袄等几种形式。在诗歌中,“罗衣”女性美有着紧密的联系:它衬托了女性的华丽、娇柔及动态之美。同时,它也被人们赋与了女性身份识别、性别审美、民族符号等多重文化意蕴。
罗衣;唐诗;意象;女性美
1 唐人的“罗衣”
“罗衣”是唐诗中经常伴随着女性形象而出现的一个审美意象,李白《赠郭将军》“爱子临风吹玉笛,美人向月舞罗衣”、刘长卿《昭阳曲》“昨夜承恩宿未央,罗衣犹带御衣香”。在我国古代,服装形制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上下相连的深衣制,另一种是上衣下裳制。《诗·邶风·绿衣》:“绿衣黄裳。”毛传:“上曰衣,下曰裳。”①(清)阮元等·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影印本。根据考古材料可知,在生活中,唐代的女装以上衣下裳为主。而唐代女性的“衣”中,包括有衫、襦、袄、裆、半臂几种款式。
衫:衫有两个特点,一是多为单衣,为人们春夏天所穿着者。《朝野佥载》卷一载杜景佺以“刚直严正,进士擢第后为鸾台侍郎、平章事。……初任溱州,会善筮者于路,言其当重入相,得三品,而不着紫袍。至是夏中服紫衫而终。”②(唐)张鷟·朝野佥载[M]·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说明了唐人的衫所穿着的季节。二是衫没有袖端。《释名·释衣服》:“衫,芟也。袖末无袖端也”,③(东汉)刘熙,(清)毕沅疏证,王先谦补.释名疏证补[M].北京:中华书局,2008.衫是春夏所穿之衣,为了散热的需要,故不设袖端。唐人男女均可着衫。有条件的人家多用纱、罗、縠等比较轻薄柔软的丝绸面料缝制而成,采用对襟敞领的形式,常常贴身而穿。
襦:《说文》曰:“襦,短衣也。”有单、夹之分。单者称为“襜襦”或“襌襦”,夹者被谓之“裌襦”,唐人的襦多为有夹层者,张籍诗云“红夹罗襦缝未成”,即为意此。襦在唐代也为男女皆穿,但女子多着襦,与裙配合,襦系在裙里。裴硎《传奇》之《张无颇》中张无颇:“睹真珠绣帐中,有一女子,才及笄,衣翠罗缕金之襦。”④引自吴增祺主编.旧小说[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85.《东城老父传》中:“元宗为娶梨园弟子潘大同女,男服佩玉,女服绣襦,皆出御府。”
袄:在唐代,袄也是女性上衣的主要款式之一。马缟《中华古今注》卷中说“(袄)盖袍之遗象也。汉文帝以立冬日,赐宫侍承恩者及百官披袄子,多以五色绣罗为之,或以锦为之,始有其名。煬帝宫中有雲鹤金銀泥披袄子, 则天以赭黄罗上银泥袄子以燕居。”①(五代)马缟.中华古今注[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6.袄的形制长于襦而短于袍,衣身较宽松,也是夹衣或棉衣,男女皆穿。
裆:裆在唐人的女装中,可指(礻盍)裆,也可能指裲裆。(礻盍)裆是一种套穿于大袖衣的外面而不遮掩大袖的外套,《霍小玉传》中描绘霍小玉“著石榴裙,紫(礻盍)裆,红绿帔子”,②鲁迅.鲁迅辑录古籍丛编[M](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宛如平生。《新唐书·车服志》中也经常提它,如武舞的舞服为“绯丝布大袖,白练(礻盍)裆”(P 520-522),“殿庭文舞郎,黄纱袍,黑领、襈,白练(礻盍)裆。”③(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裲裆则有点类似于今天的背心、马甲之类。《释名·释衣服》中:“裲裆,其一当胸,其一当背,因以名之也。”④(东汉)刘熙,(清)毕沅疏证,王先谦补·释名疏证补[M]·北京:中华书局,2008,卷五。(P172)《新唐书·车服志》中也描绘了它的形制为:“裲裆之制:一当胸,一当背,短袖覆膊。”⑤(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卷二十四。
半臂:《事物纪原》引《二仪实录》称:“隋大业中,内宫多服半臂,除即(却)长袖也。唐高祖减其袖,谓之半臂。”⑥(宋)高承.事物纪原[M].北京:中华出版社,1989.“半臂”是短袖式的罩衣。唐代制作半臂多以用锦,《新唐书·地理志》中说扬州土贡有“半臂锦”⑦(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卷四十一。,《通典·食货志》中也说广陵贡“半臂锦百段。”⑧(唐)杜佑.通典[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卷六。这是因锦的组织紧密、质地厚实,可较好的起到御寒作用的缘故。
2 “罗衣”与唐诗中的女性美
很早以来,丝绸服饰就成了女性美的良好载体。华丽温润的丝绸制成服装,穿在女性身上,与女性光洁的皮肤,柔曼之体态相互映衬、相得益彰。诗人们早就发现了这一点,故在诗歌当中,女性美丽的形象常与丝绸服饰联系在一起。如在《陌上桑》中写秦罗敷之美时,没有提到她形体相貌,而是写其“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借服饰描写以引发读者对罗敷的容貌产生意味深长的联想,女性之美借华丽优雅的丝绸得以传递。在唐诗中也是如此,人们经常用“罗衣”的描写来衬托女性的美好形象。
首先,诗人以丝绸服饰展现了女性的华丽之美。作为高级的面料,丝绸所制成的服饰为女性所喜受,《旧唐书·舆服志》说唐时女性着衣的风气为:“风俗奢靡,不依格令,绮罗锦绣,随所好尚。”⑨(后晋)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卷四十五。故杜甫《丽人行》中描写虢国夫人与秦国夫人“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丝绸制成有衣裙上用金线绣着孔雀与麒麟图案,富丽夺目的效果使贵妇人们显得气度不凡;白居易《秦中吟十首·议婚》中的“红楼富家女”身上是 “金缕绣罗襦”,温庭筠笔下的女子也身着“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菩萨蛮》),对于这些身着丝绸服饰的女子,文字中虽不言其身份,然从这些服饰描述里,却处处透着华丽与高贵,诗人欣赏和欲以表达的都是一种富贵之美。乔知之《下山逢故夫》,“妾身本薄命,轻弃城南隅。庭前厌芍药,山上采蘼芜。春风罥纨袖,零露湿罗襦。羞将憔悴日,提笼逢故夫。”题为拟古,在现实生活中,劳动妇女是不可能穿得如此华丽去从事劳作的,诗人之所以将其衣着写得如此华美,就是因为在唐人眼里,穿丝织品是一种富贵的象征,代表着美丽和时尚。
丝绸服装还展现了女性的娇柔纤丽之美。由于丝织物轻薄的特点,当它穿在人体身上的时候,会清晰的显露出人体曲线。对于那些纤弱苗条的女性而言,身着丝绸服饰,尤为显得楚楚可怜,这极大的符合了人们自古以来对女性“柔弱”的审美取向。提到唐代的女性审美,人们会有一个印象,认为唐代女性普遍个性张扬,是一个以丰满、健硕为美的时代。但实际上唐人在个性上依然推崇女性的柔弱顺从,如白居易的判文中颇多:“礼贵妻柔”,“德非柔淑,宜家之道则乖”、“妻惟守顺”之语,①(后晋)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卷六七三。宋若莘的《女论语》中也专列“和柔”一章,要求女子对父母、公婆和丈夫都柔和有礼。在体态上,唐人也欣赏纤弱秀丽的女性,这种类型的美女在唐人笔下经常出现。如唐传奇《步飞烟》中的步飞烟“容止纤丽,若不胜绮罗”,②吴增祺主编.旧小说[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85,乙集二。《杜阳杂编》卷上载元载宠姬薛瑶英 “肌香体轻”,“宝历二年,淛东国贡舞女二人:一曰飞鸾,二曰轻凤。”她们 “舞态艳逸,更非人间所有”,都是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而丝绸服饰是展现女性娇弱之美的良好伴侣:薛瑶英 “衣龙绡之衣,一袭无二三两,抟之不盈一握。”飞鸾轻凤则“衣軿罗之衣”③(唐)苏鹗.杜阳杂编(卷上),引自《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唐诗中很多诗句描写丝绸服装之轻薄,实际上是以丝绸轻软的质地衬托出女性柔弱的气质与体态。例如在许多闺怨诗中,就反复写到罗衣之轻、薄,王涯《秋夜曲》“桂魄初生秋露微,轻罗已薄未更衣。银筝夜久殷勤弄,心怯空房不忍归”,秋夜里已是夜凉如水,而诗中的女子仍然身着薄罗衣衫,其娇弱的形象自然惹人怜爱。又许景先《折柳篇》:“自怜柳塞淹戎幕,银烛长啼愁梦著。芳树朝催玉管新,春风夜染罗衣薄。”田娥《寄远》“泪流红粉薄,风度罗衣轻。难为子猷志,虚负文君名。”衣之轻、薄,都是因为在心理上觉得孤独,感到不胜风寒的缘故,在这些情况下,罗衣之轻薄与主观感觉上之清冷寂寞是互相映衬的。
丝绸服装还衬托了女性的飘逸之美。我国古代的服装造型总体上有着“褒博衣冠”的特点,这种特点的形成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丝国”,人们喜欢以丝绸制作衣服有关。④丝绸面料总的特点是轻薄、柔软,但它的不足则是易生褶皱,容易吸身。因此,丝绸服装的结构造型不宜太紧身合体,以免紧绷、吸身造成不规则的皱纹;结构分割线也不宜过多,以避免缝纫线迹产生的细碎褶皱,影响整体效果。宽松、直线型的服装结构造型就十分适合丝绸面料的结构设计,由此形成中国古代服装宽衣博带的特点。当这种造型宽大的衣服穿在人体身上时,每当临风站立,举手投足之间,衣袂飘动,更可显示出穿着者潇洒飘逸的姿态。唐诗中常写“罗衣”的动态美,以动态之美来衬托出女性的飘逸。如萧德言《咏舞》:“低身锵玉珮,举袖拂罗衣。对檐疑燕起,映雪似花飞。”李白 《前有樽酒行二首》:“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温庭筠《黄昙子歌》“罗衫袅回风,点粉金鹂卵。”在这些诗句中,服饰之美和女性之美都不是静止不动的,诗人追求的不仅仅是衣服本身的美,更主要的是服饰赋予人的那种灵动的姿态。因此,唐人描写丝绸服饰时还经常将其与外界事物如 “风”一起描写,以表现身着丝绸服饰的人物的飘逸,如 “悲歌泪湿澹胭脂,闲立风吹金缕衣”(韩偓《遥见》)、“龙池宫里上皇时,罗衫宝带香风吹”(韦应物《白沙亭逢吴叟歌》)、高堂静秋日,罗衣飘暮风”(王缙《杂曲歌辞·古别离》),正所谓“衣轻任好风”,轻薄剔透的丝织品再加上摇曳飘动的姿态,给人们的视觉带来极大的审美感受。
3 唐诗中“罗衣”的文化意蕴
符号是佩带在身上表明职别、身份等的标志。服饰正是这样一种符号,它同语言文字一样,具有区别意义的功能。法国美学家罗兰·巴特说:“(服饰)它是处于纯粹状态中的语言。”在生活中,“罗衣”包括种种细节,而在唐诗中,当当服饰描写也现在诗人笔下,浓缩成“罗衣”时,“罗衣”便成了区别意义的文化符号。
(1)古代男女服饰已定型,诗人巧妙地运用服饰暗示人物性别,在唐诗中,“罗衣”是女性身份的象征。如在张祜《题真娘墓》:“佛地葬罗衣,孤魂此是归。舞为蝴蝶梦,歌谢伯劳飞“,此诗即使我们不看题目,也会知道葬于此地的是一位红颜女子。又于武陵《高楼》:“远天明月出,照此谁家楼。上有罗衣裳,凉风吹不休”,薛逢《观竞渡》:“两岸罗衣破鼻香,银钗照日如霜刃。”俱以罗衣指向女性。最典型者莫过于鱼玄机的“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游崇真观南楼,睹新及第题名处》)句,鱼玄机感慨自已纵有诗书满腹,才华横溢,但由于她的女性身份,不能象男人一样取得功名,实现自已的抱负。谭正壁先生评论道:“她的心情很显明的表露出来了。可恨,她不是一个男性,虽有诗才似海,其将奈何!”⑤谭正壁.中国女性文学史话[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它反映了林丹娅所说的:“在人类文化中,‘服装’已不再是、或是游离了它所指物质的本质与功能,它被赋予了文化性职能,它代表着性别,它就是性别符号,它是性别所意指的一切社会内容。……女性在‘衣裙’之中经历了漫长的生长,现在,她与‘衣裙’合二为一,她是‘衣裙’,‘衣裙’便是她。”①林丹娅.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
在中国古代,以服饰代指人物身份是一种常见现象。如人们熟知“巾帼”、“黔首”等词,俱是从服饰文化中演变而来。但在诗歌中,“罗衣”与女性之间的这种紧密联系并非天生而成,它有一个沉淀、演变的的过程。在古代,男性也需穿衣,并且也穿丝绸所制作的衣服,在唐前诗歌中,“罗衣”有时也指向男性,如在江淹《效阮公诗十五首》之三的“白露淹庭树,秋风吹罗衣”,②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就不是指女性之衣。而在唐诗中,“罗衣”的出现更为频繁,在意义指向上也更为明确,“罗衣”变成专指女性的审美意象。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情况,我认为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丝绸与女性美之间的紧密联系,即社会审美心理的长期积淀后而形成的。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诗歌中的女性身上,无论是华丽之美、柔顺之美还是飘逸之美,都带着丝绸本身的特点。在古代,虽说男性也穿着丝绸所制作的服饰,但丝绸轻柔、细腻的质地与女性阴柔的气质有着更多的相似相通之处,这些相似相通之处容易引发诗人的联想,于是,“罗衣”就更多的与女性联系在了一起。其次是在服制上。虽说古代的男性也着罗衣,但在日常生活中,男性,尤其是贵族男性的服饰一般以上下相连的袍服为主,而汉族女性多采用上衣下裳的服制。上衣下裳从魏晋以后一直到明代结束之前,在女性的服式上都占着主流地位。彼得·波格达列夫在《作为记号的服饰》一文中说:“服饰既是物质的客体,又是记号。”③(捷克)彼得·波格达列夫.作为记号的服饰[J].戏剧文学,1992,(2).服饰有附着于体肤之外的标志意义,而这种标志意义是由它们的物质特性、社会应用及文学创作规律所共同决定的。在诗歌中,“罗衣”是女性身份的符号象征归根到底是由它与女性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所决定的。
(2)服饰具有审美的功能,中国的古典诗歌向来对女性服饰表现得饶有兴趣,以服饰美代替女性美,成了诗人们创作中的一大特点。在唐诗中,“罗衣”成为女性的美貌及青春年华的象征。权德舆的《玉台体五首》中:“隐映罗衫薄,轻盈玉腕圆。相逢不肯语,微笑画屏前。”女性圆润的肌肤之美靠罗衫质地的轻薄得以衬托出来。在我国古代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状态下,女性与服饰一样,是被观赏的对象。在服装起源的原理中,原本就有所谓的“性吸引说”,即,人类穿衣服不是为了遮蔽,而是为了吸引。唐代女性讲究妆饰,跟社会经济、文明程度固然有关,但也跟性的开放、女子以服饰媚惑男人有关。对于从属地位的女性而言,选择美丽的服装,是为了迎合男性的审美期待。当没有了取悦对象的时候,服饰似乎也失去了意义。崔国辅《怨词二首》,“妾有罗衣裳,秦王在时作。为舞春风多,秋来不堪著。”“罗衣裳”既见证了美好的年华及青春美貌,“不堪著”不仅仅是时令的缘故,而是没有了欣赏者,锦衣华服在此时也失去了它的意义。这样的情景在唐人笔下一次次出现,如崔液 《代春闺》:“青楼明镜昼无光,红帐罗衣徒自香。妾恨十年长独守,君情万里在渔阳。”“君”在万里之远,青春美貌又有什么意义呢?王勃《铜雀妓二首》:“君王欢爱尽,歌舞为谁容。锦衾不复襞,罗衣谁再缝。”题目虽是写古,一样具有现实的意义。
(3)服饰是社会的产物,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与服饰的发展变化密不可分,这就决定了服饰会具有特定含义,服饰所包含的内容往往是社会种种现象的折射结果。汉民族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形成了自已独特的服饰文化。历史上以服饰作为汉族文化象征的例子并不少见,如孔子就曾经说过:“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④(清)阮元等.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影印本。这是因为在古代汉族的服饰中,衣襟都是右衽,只有少数民族及死者是穿左衽的衣服的缘故。储光羲《明妃曲》诗云“日暮惊沙乱雪飞,傍人相劝易罗衣,强来帐前看歌舞,共侍单于夜猎归”,诗中的王嫱在下雪天还穿着罗衣,在这里,“罗衣”成了她汉族女子身份识别的象征。中国属于丝纺织文化圈范畴,⑤赵丰先生指出,从古代纺织原料使用的角度来看,世界可划分为四个纺织文化圈,中国虽也使用葛、麻,但其特点是使用丝纤维,无疑是属于丝纺织文化圈。见于赵丰.中国丝绸艺术史[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罗、纨、绢等丝织品是中原服饰文化的重要载体,而古代西北少数民族一般都服用毛织物,孟郊《征妇怨》中,“渔阳千里道,近如中门限。中门逾有时,渔阳长在眼。生在绿罗下,不识渔阳道。良人自戍来,夜夜梦中到。”也以“绿罗”代指汉文化,在唐诗中,丝织品、丝绸服饰由此成为汉族文化的标志。
在生活中,服饰体现了人物的年龄、学识、人与人的关系等等,服饰作为非语言符号时时在传达这些潜在的信息,实际上,它已是物化了的人的意识,具有指代性,久之成为心理定势。在唐诗中,诗人们这样浓墨重彩地写女性服装,既是他们对于女性服装美的一种关注,认可和审视。也可以看出时人对于女性的审美倾向,在一个以男权意识为主导的社会里,这实际上也代表着整个社会对女性服装的期待和要求。黑格尔《美学》中说:“艺术的显现通过它本身而指引到它本身之外。”①(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三卷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唐诗中的服饰描写也是如此,我们可以说,服饰,尤其是进入了审美状态的服饰,其本质上是一种物化了的人的意志和精神,它积淀着唐人的意识、情感与意识,具有一种折射时代风气和社会心理的意义与功能。
[1](清)阮元等·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影印本。
[2](唐)张鷟·朝野佥载[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3](东汉)刘熙,(清)毕沅疏证,王先谦补·释名疏证补[M].北京:中华书局,2008.
[4]吴增祺主编.旧小说[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85.
[5](五代)马缟.中华古今注[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6.
[6]鲁迅.鲁迅辑录古籍丛编[M](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7](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8](宋)高承.事物纪原[M].北京:中华出版社,1989.
[9](唐)杜佑.通典[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
[10](后晋)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1](清)董诰等.全唐文[M].中华书局,1983.
[12](唐)苏鹗.杜阳杂编[M].《丛书集成》初编本。
[13]谭正壁.中国女性文学史话[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
[14]林丹娅.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
[15]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6](捷克)彼得·波格达列夫.作为记号的服饰[J].戏剧文学,1992,(2).
“LUOYI”IN TANG POETRY AN ITS CULTURAL MEANING
ZENG Yan-hong
(Guangxi Teachers Education University,Nanning Guangxi 530000)
“Luo Yi” is a image that always associated female images that appeat in the Tang poetry.In the real Life of Tang dynasty,“Luo Yi”means silk coat that weared by female.They include Shan、Ru、Dan、Ao etc.In poetry,“Luo Yi”connect with the female’s beauty closely.It foils the female ‘s luxuriance、feminnin and dynamic beauty.At the same time,it is endowed cultural meaning of female personal identification、Sexual Aesthetic and national symbol.
Luo Yi;Tang Poetry;mage;female’s beauty
book=50,ebook=198
I207
:A
:1672-2868(2010)05-0050-05
责任编辑:陈 凤
2010-07-11
曾艳红(1971-),女,广西桂林人。广西师范学院,博士,研究方向:文化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