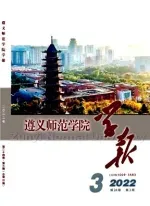走进一种别样的乡土
——论仡佬族女作家王华的小说创作
梁波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兰州 700020)
走进一种别样的乡土
——论仡佬族女作家王华的小说创作
梁波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兰州 700020)
王华是贵州仡佬族女作家,她的创作以柔软独特的民俗表现、本土化的魔幻书写以及对乡土温暖情怀的克制抒发,在当下众多的乡土文学中呈现出别样的特色。
民俗;魔幻现实主义;本土化;苦难叙事
2005年第一期的《当代》刊发了贵州仡佬族女作家王华的长篇小说《桥溪庄》,结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没有贵州作家在这个最为权威的文学杂志发表长篇小说的历史。不止如此,时隔一年多《当代》又推出了她的另一部长篇《傩赐》,这在全国范围内也颇为罕见,可以说是贵州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重大突破。加上散见于各种文学刊物的《在天上种玉米》、《老师》、《天上没有云朵》、《逃走的萝卜》等中短篇,王华近几年的创作实绩的确令人瞩目,已经很有论说的必要了。王华在黔北的偏远小县生活多年,由于工作的关系,足迹遍及小县的各个乡镇村落,竹林田垄,与当下中国农村乡土生活几近一体,《当代》在刊发其作品时也用到了“底层作者”、“无名作者”这样的称谓。因而对于这位来自乡野、身炙大地的乡土作家,我们原来的阅读期待停留在她将带来更为真实、琐屑的乡土生活层面,顶多在生活细节、人物语言上糅合更多的泥土气息和边地色彩,然而读了她的作品,却让人得到超出预期收获的惊喜。事情不是想象的那样简单,王华的创作以柔软独特的民俗表现、本土化的魔幻书写以及对乡土温暖情怀的克制抒发,在当下众多的乡土文学中呈现出别样的特色。
一、柔软的民俗
本民族的风俗人情、民族文化无疑是一位少数民族作家最为丰富的写作资源,终其一生也受用不尽,拥有这样一个精神的宝库当然令人羡慕,但与此同时不可回避的是作家必须承担起弘扬本民族文化的责任。印度诗圣泰戈尔说过,“一切民族都具有在世界上表现本民族自身的义务。假如没有任何表现,那可以说是民族的罪恶,比死还要坏,人类历史是不会原谅的。”[1]作为为数不多的仡佬族作家,向世界表现仡佬族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王华责无旁贷。仡佬族主要居住在贵州北部,少量散居于云南和广西,有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大多信奉道教,有的也信奉佛教,在建筑、服饰、饮食和艺术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意蕴。怎样才能将这样瑰丽的民族文化让世人认识和了解是王华写作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为此王华做出了独具个性的探索,她的作品带有强烈的仡佬族民族印记,民俗描写随处可见,但却并不拥挤生硬。
其一,王华并没有以仡佬族民俗文化为其小说创作的标签,甚至在小说中她有意地回避着对民族身份的明确指认。她所有作品的故事都没有说明是发生于具体的哪一民族,哪怕是最能体现其少数民族文化背景的“寻根”之作《傩赐》也是这样。《傩赐》讲述的是一个山外女人秋秋同时嫁给了大山里傩赐庄三个男人的故事。小说中充满对傩赐庄民俗的绘声绘色的描写,“桐花节”、“打篾球”、“高脚狮子”以及婚俗葬礼等,这其中虽然很大一部分都是仡佬族的民俗文化,但作者却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一代一代的祖辈,只告诉傩赐人要过桐花节,过桐花节要穿这样一身盛装,但并没有告诉过我们是什么民族。就是说,傩赐人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民族。”这种在文学作品中对民族身份的有意模糊,并不代表作者民族意识的自我隐退,因为小说首先必须是小说,如果过分凸显民族身份,对民俗文化进行公然宣讲,极易滑向以民族秘史异闻来吸引人眼球的写作误区,这必将大大降低小说的品格,使之成为猎奇者的快餐消费品。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王华笔下的民俗虽然在作品中没有民族指向,归属是模糊的,但她对它们的展示却是清晰生动的,在《傩赐》中作者甚至花了整整一章的篇幅对桐花节作了精细鲜活的描摹。换一个角度来看,这样的做法反而会引起读者对这一民俗文化进一步探究的兴趣,并最终寻找到它的根源。
其二,王华对民俗有着自己的取舍和再造,它们的出现都以服务情节发展为基准。如果简单生硬地将民俗文化、风土人情等移植到作品中,甚至是毫无计划、无关题旨的堆积罗列,那么小说将变成一份轻飘飘的民族风情旅游的宣传手册。王华的小说不是仡佬族民俗文化原封不动的照搬,而是经过了作者的冶炼熔铸,使之不显得仓促突兀,适时适地地与小说情节契合在一起,起着引发、烘托、推动故事发展的作用。《傩赐》中作为故事原动力的傩赐庄“一妻多夫”的风俗并不见于仡佬族,作者借鉴了其他少数民族的婚俗,加以改造,使之成为引发小说前进的关键。仡佬族有“年节祭树”的大树崇拜,据此作者以其丰富的想象力虚构了傩赐庄的桐花节,为之设计了一个感人至深的桐花姑姑拯救村庄,嫁给三个男人繁衍傩赐的传说,并将原汁原味的仡佬民俗唱傩戏、对山歌、“打篾球”、“高脚狮子”等巧妙镶嵌其中,不着痕迹。同时,这一段民俗描写的插入,是秋秋得知自己还要嫁给第二个男人蓝桐而陷入巨大心理危机的时候,它有效地缓和了矛盾,使秋秋的心理认同在被动中发生变化,故事得以继续向前延伸。王华并不刻意地让民俗浮现于作品之上,而是如信手拈来一般,让其自然流淌。《歌者回回》里死人出殡时唱离歌的传统,《桥溪庄》里雪山当石匠表明仡佬族盛产石匠的特色,《傩赐》里的玉米干饭、油茶等饮食文化,都带有浓重的仡佬族印记,它们在王华的笔下变得柔软,与小说本身贴合无缝,浑然一体。当然写民俗只是弘扬民族文化的第一步,从目前王华的作品来看,对仡佬族民族文化的展现还略显单一,她还必须更加努力地将仡佬族真正的精神根柢和民族魂魄艺术地呈现于世界。
二、本土化的魔幻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对中国小说创作的影响虽有消长隐显,但从未间断。新世纪以来回归传统现实主义的“底层叙事”洪流滚滚,为免于淹没其中,对乡土世界的魔幻书写成为一种突围路径,但魔幻现实主义的移植从来就有水土不服的问题。如何“把魔幻和中国本土观念和文化、中国历史本身、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态度和我们的世界观融在一起,把这些全部融入了我们历史本身,”[2]是对中国作家的巨大考验。从莫言的《生死疲劳》、阎连科的《受活》、《丁庄梦》等作品我们已经看到了探索的趋向。原以为在经济等诸方面都欠发达的贵州山区小县,王华与魔幻的距离如同横亘的重重大山一样遥远,但王华用她的创作回击了我们的猜测,这再一次印证了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的发展同艺术生产之间并不平衡的论断。王华的笔下不仅有魔幻,而且由于熟谂乡土生活,对农民的所思所想、所欲所梦了如指掌,加上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王华的魔幻与当下中国乡土结合得更加紧密,显示出与众不同的个性和对魔幻现实主义本土化的努力。
首先,王华在小说中将故事发生的时间、背景尽量淡化,以期滤去外部因素对乡土的遮蔽,还原一个更为“纯粹”、“本色”的乡土,为魔幻的生发开辟值得信赖的土壤。在《桥溪庄》、《傩赐》、《家园》、《在天上种玉米》等作品中故事时间被抽离,读者只能得到一个故事发生时间的笼统印象,但却不能将之具体到某一更为明晰的阶段,甚至从小说中去刻意寻找能够反映时间概念的社会事件、生活细节,并以此来指认故事时间也是困难的。时间的碎裂为故事的生长清除了障碍,读者的注意力不再是将小说中的情节与现实作对应的比较,而是完全进入了故事本身,故事得以自由伸缩。同时,作者将故事的发生地封闭在一个相对自足的空间内。在以上几部作品中,桥溪庄是因为一个水泥厂的存在,由不知从何而来“向厂求生”的人们组成的移民村落;傩赐庄在“一年四季里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才有真正的阳光”的高山之巅;《家园》里的没有“死亡”这个词汇,人与山水草木、鸟虫鱼兽和睦相处的世外桃源一般的安沙;直至《在天上种玉米》中村民集体由乡入城租住在城市边缘的漂移着的三桥,所有的故事都意图指向一个内收的、外界干扰不大的世界。这从某种角度看来是虚化了作品的真实性,但仔细分析却并不是这样。显然作者并不着意营造一个现实乡土世界的纸上模型,没有把对现实亦步亦趋的模仿和使读者以之为真当作创作的指归,而是力图在这样的时空界说下,摆脱那些可能的束缚,直指当下乡土生活的本真,展示农民本质的原初的生存困境和精神磨难,呈现一个能够为读者体验得到的世相人生。
其次,王华对魔幻的运用不是随心所欲地拼贴,而是有着清晰的逻辑和现实依据。在时下很多所谓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中,作家醉心于刻画荒诞不经、诡异恐怖的情节,那怕这些情节并没有现实大地的依托,使魔幻成为炫人耳目的闪光亮片,小说走向了为魔幻而魔幻的虚无之途。王华的旨趣显然并不在此,她的小说虽然故事大都令人匪夷所思,但却有着坚实的现实生活的支撑,并不是凭空而来。《桥溪庄》写的是一个靠近水泥厂的村庄里所有男子死精,女子只怀气胎、不怀血胎的怪异现象及由此引发的悲剧。作者虽然没有明确指出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但却在作品中对水泥厂的严重污染不断进行暗示:天空总是灰蒙蒙的,村庄里没有一棵树,村里的壮劳力不管男女都在厂里干活,“被自己弄出来的灰尘包裹着,喘粗气,流大汗”,使人不得不将二者联系起来,认识到是生态的破坏导致了这样的悲剧,这就让魔幻有了逻辑。还有小说中雪山为雪豆傻了,雪果为雪朵疯了,父亲李作民砍掉性变态的儿子雪果的脚板这些带有魔幻因素的细节,无一不是逼仄生活对人的挤压所造成,透露出厚重的现实底色。《傩赐》里“一妻多夫”的秘俗,在当下发生有些让人难以置信,但作者也给出了它的根源:极端的贫穷和久远的民俗传统。《家园》里“曹操干尸”的横空出世,成为移民村庄一个所谓的旅游资源,我们在倍感荒诞之余,可见作者对现实中臆造旅游景点的莫大讽刺。《在天上种玉米》里三桥村的年轻人出外打工,最后将村里老人、孩子都集体迁移到城市里的城中村租住。村庄挪了一个地方,原来的村长王红旗执着地要将现在居住的善各庄的名字改成三桥,为此他自己动手做村名标牌,让全村人都将村庄叫做三桥。同时,由于失去土地,他又异想天开的在屋顶上铺土种玉米。这些看似笑谈的怪诞行为并不是毫无来由,相反它是对农民离别家乡、失去土地后微妙心理的放大展现,显示了作家对当下进城农民无根处境的深刻洞察。魔幻现实主义的宗师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谈到他的《百年孤独》时说,“我认识一些普通的老百姓,他们兴致勃勃、仔细认真地读了《百年孤独》,但是阅读之余并不大惊小怪,因为说实在的,我没有讲述任何一件跟他们的现实生活大相径庭的事情”;“在我的小说里,没有任何一行字不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1]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是以拉美国家的现实生活为基础的,要使中国的普通读者不对小说中的魔幻大惊小怪,魔幻必须本土化。中国作家的魔幻必须以中国的现实为基础,而不是只制造标新立异、耸人视听的魔幻亮片,置中国文化、本土观念和百姓日常生活态度于不顾,这样的话,这些魔幻的亮片只能是空中楼阁,浮游在中国现实织物的表层,并不能与之相匹配。
最后,王华还倾力于魔幻意象的构建,以凸显小说的主题意蕴。正如前文所述,王华的作品中我们并看不到虚空高蹈、不着边际的魔幻情节,但在读她的小说时我们却被一种浓郁的魔幻气息所包裹,这主要得力于作者对魔幻意象的营造。《桥溪庄》的开始作者就写了村庄的无雪,当四周都雨雪纷飞的时候,桥溪庄却不下雪,“一片茫茫雪野中,桥溪庄,一个方圆不过一里的庄子,仍然固执地坚守着它那种灰头土脸的样子,坚守着它那份坚硬的憔悴”,“像茫茫雪野上的一块癣疤”;“他们想雪是上天赐给地上生灵万物的最圣洁的礼物,上天要是不给桥溪庄雪了,就说明上天是要抛弃桥溪庄了”;以及雪豆出生时预言似的大叫“完了!完了!”,一下将故事导入魔幻意境之中。为增强这种效果,小说中的桥溪庄没有一棵树,天空一直是灰蒙蒙的,这也昭示了小说的主题,为故事的悲剧性奠定基调。作者还精心设计让主人公雪豆养了一群猫,“雪豆是那样的喜欢猫,见了猫就像见了心肝宝贝一样,又是亲又是抱”。当猫死后,还用棕缝成口袋将猫送去挂在树上。“猫是很有巫性和神性的动物,雪豆养的那群猫给桥溪庄渲染出一种神秘而低沉的调子。”[3]这样的魔幻意象并不只是偶然出现,它们贯穿小说始终,被反复强调。《傩赐》里不断提及的村庄上方天空中的“白天阳”和遮天盖地的浓雾,“傩赐这个地方,一年四季里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才有真正的阳光。平时,这里最富有的就是雾,于是,很多时候傩赐的天空中就会有一轮白太阳。从升起到落下,一直洁白如银,一直那么美丽而忧伤”、“看不到白太阳的时候,我们傩赐的雾,比奶还要浓。都应该是太阳升起一尺高的时候了,可傩赐还被泡在雾里”。这样的意象营造不仅将故事笼罩在一片魔幻氛围之下,还是主人公秋秋的悲剧命运的隐秘象征。在这里魔幻意象并非作者故弄玄虚的艺术把戏,它是整个小说叙事进程中一个密不可分的构成元素。正是由于魔幻意象的参与,王华的叙事才显得神奇而具有趣味,同样,也正是由于魔幻意象群落的存在,王华小说的主题才显得隐曲而意蕴深远。
三、克制的温暖
在当下反映乡土的小说创作中,存在着一种较为极端的现象,那就是为弥补“悲悯情怀”的缺失,作家往往走进情感泛滥的另一误区。如很多“底层叙事”的作品,作者以对底层农民生活苦难的堆积式展览,近于哭诉的叙事声音,毫无节制地宣泄着心中郁勃的情感,读者甚至能从文字里看到一个腔调悲戚,泪水涟涟的作者形象。当然,我们并不怀疑这种情感的真实性,在文学普遍缺乏温暖的今天,这样的情感是珍贵的,这样的声音是有价值的,这样的作家也是值得尊敬的。但是,如果仅仅如此却又难以让人满意,情感的青筋暴露必将影响小说的艺术性,文学还必须回到文学本身,文学需要约束。黑格尔说过,“啼哭在理想的艺术作品里也不应是毫无节制的哀号……把痛苦和欢乐尽量叫喊出来并不都是音乐。”[4]王华小说的故事很多都是沉重的,不过却并没有“哀号”与“叫喊”,她对故事的讲述显得平静从容,甚至有时还让人有一丝凉意,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体会到她那克制的温暖。
王华写苦难,并不只是呈现苦难本身,而是意图揭示人在苦难面前的坚韧与温情。《桥溪庄》里的李作民一家经受着苦难的折磨,人物命运乖蹇,雪山为雪豆偷猫被砖头砸傻了;雪果因为雪朵的离去而疯掉,甚至性欲变态强暴了自己的母亲;李作民剁掉儿子雪果一只脚的脚板;雪豆一丝不挂疯疯癫癫的失踪了;李作民女人喝敌敌畏自杀;英哥被公爹强暴而出逃,又被人贩子拐卖……这些深重的悲剧,作者写来并不是呼天抢地,而是近于不动声色,以至于有人以“冷文学”相称。然而冷的文学并不代表缺乏热的真情,尽管苦难重重,但桥溪庄人依然坚韧,并没有丧失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与关怀,李作民对山子的父亲般的照顾,雪朵离开山子重新回到疯掉的雪果的身边,全庄人凑钱让李作民去为雪豆治病等印证了这一点。正如作者所说,她描写的是冷环境中一群有血有肉充满爱心与真情的农民,这个群体中的人们是充满暖意的,[3]作者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描写将自己对乡土的温暖情怀慢慢地浸润进作品当中。对乡村女性生存与命运的叙写也体现着王华含蓄深沉的思考。《天上没有云朵》里一个传统的农村女性坚决反抗了村长的霸占,但在两村争水的械斗中,却不得不让邻村的男人们玩弄,独自承受着传统道德的巨大压力。《女人花》中王冰长期忍受着两地分居的生活,来到高原工地看望丈夫,但看到的却是丈夫的放纵,她并没有指责哭闹,而是试图去理解严酷高原工作给丈夫带来的变化,默默地离开,将反思留给了丈夫。《傩赐》里的秋秋一女嫁三夫,虽然她也奋力抗争,但最终在严峻的生活面前,她不得不接受了现实。在这些作品里,作者延续着一贯冷静的笔触,超越了一般的人性批评和道德评价,也没有简单地将女性的悲剧命运归因于男权的欺压,而是展示了在生活的逼迫下女性的无奈选择,透射出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关注。
作为一种苦难叙事,苦难与生活的双重关系需要深入认识,因为这不光涉及作品的艺术性问题,而且关乎文学表现苦难主题的深度和广度。作家如果一味地将个人情感充盈到故事中,没有必要的审美距离,那么对现实生活的表现也将会显得声嘶力竭,张牙怒目。文学毕竟不是赚取眼泪的廉价情感故事,但同时过度的冷静客观又极易陷入自然主义的泥淖而无法自拔。其实这方面,鲁迅式的“忧愤深广”已经为我们开辟了如何反映现实的大道。王华显然在沿着这条道路的指引前进着,在她那看似冰冷的文字下有着对乡土的深情,并对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命运进行着自己的思考,但不可否认的是将现实生活处境的挤压作为人物命运的答案似乎还不能解释一切,也不能让人完全信服,人作为个体的独特性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王华自己也在《桥溪庄》里发出了疑问,“现在想起来,倒好像谁都有错,又好像谁都没错。你说咱们桥溪庄这日子咋就过成这个样子了呢?”人物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在生活的背后是什么等等问题还需要王华继续思索,我们期待着她能在作品中给出更好的回答。
[1]现代艺术札记·文学大师卷[M].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2001.124,228.
[2]罗四鸰.莫言新长篇《生死疲劳》面世——用“东方魔幻”书写乡土.文学报[N],2006-1-19.
[3]周静.固守在故土和乡情里——记“骏马奖”获得者王华.贵州日报[N],2009-1-16.
[4]黑格尔.美学·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204.
(责任编辑:王 林)
Stepping into an Exotic Vernacular Land——A Study into Fiction Writing of Wang Hua,an Authoress of Gelao Nationality
LIANG Bo
(School of Literature,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700020,China)
Wang Hua is an authoress of Gelao nationality of Guizhou,and her writing is featured by tender and unique representation of folklore,magical writing of indigenization,and restrained expression of her warm affections towards vernacular land,which presents particularly distinctive in contrast with other native literatures.
folklore;magic realism;indigenization;misery narrative
I207.9
A
1009-3583(2010)-02-0079-04
2009-12-01
2007年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全球化语境下中国西部电影改编研究”中期成果(041210)。
梁波,男,贵州遵义人,兰州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