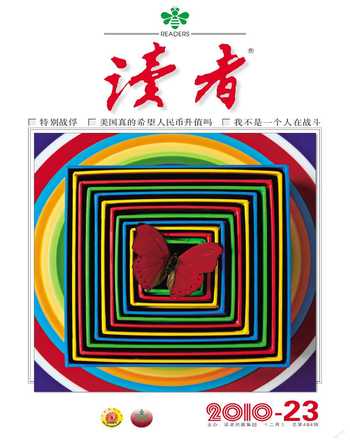小黑的选择
李家同
我做大学教授已经很多年了,我注意到大学男生属于白面书生的已经非常少了,大多数男生都有很健康的肤色,可是比起在外面做工的人来说,我们的大学生仍然白得多了。
张炳汉是少数皮肤非常黑的那种大学生,难怪他的外号叫“小黑”。我是他的导师,第一天师生面谈,他就解释给我听为何他如此之黑。他说他从高二开始就去工地做小工,再加上他是屏东乡下长大的,所以皮肤黑得不得了。他说他家不富有,学费和生活费都要靠哥哥,而他哥哥就是一位完全靠劳力赚钱的建筑工人,他大一暑假就跟着他哥哥打工,赚了几万元。
有一天,一位屏东县社会局的社工人员来找我,他告诉我一件令我大吃一惊的事。他说张炳汉现在的父母绝不可能是他的亲生父母,因为他们的血型都是O型,而张炳汉却是A型。他们早就发现了这个个案,通过计算机数据库不断地搜寻,他们总算找到了他的亲生父母。
我只在这里说一个强有力的证据:他们发现张炳汉其实是走失的孩子,他现在的父母领养了他,而他被发现时穿的衣服也有很清楚的记录。当时他只有两岁,十八年来,他的亲生父母仍保留着当年的寻人启事,也从未放弃过找他的念头,那个启事上的衣服和小黑当年被找到时穿的完全吻合,再加上其他的证据,他们已可百分之百地确定小黑可以回到亲生父母的怀抱了。
社工人员问我小黑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我告诉他小黑性格非常爽朗,于是他建议我立刻告诉小黑这个消息。
小黑听到了这个消息,当然感到十分激动,可是,他告诉我,他早就知道他的父母不可能是他的亲生父母,血型是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是他和他哥哥完全不像,他哥哥不太会念书,初中毕业以后就去做工了,他却对念书一点困难也没有,他哥哥的体格也比他强壮得多。
他们俩唯一的相同之处就是口音,可是他认为这是因为他从小学他哥哥的缘故。不要看小黑年纪轻轻,他的决定却充满了智慧。他说他不知道他的亲生父母是什么人物,可是不论他们是什么人,他登记父母一栏时不会有改变。他的理由非常简单:他们对我这么好,收养了我,含辛茹苦地将我带大,我这一辈子都会认他们为爸爸妈妈。至于亲生父母,我会孝顺他们,也将他们看成自己的父母,只是在法律上,我不要认祖归宗了。
我和社工人员都为小黑的决定深受感动。社工人员告诉小黑,他的生父是一位有地位的公务员,生母是中学老师,他们还有一个儿子,比小黑小一岁,念大学一年级,他们住在台北。
小黑表现得出奇镇静,他要和社工人员一起回屏东去,将这一切告诉他的爸爸妈妈。他的爸爸妈妈是典型的乡下好人,他们听到这个好消息立刻和台北方面联络,约好周六小黑去台北见他的亲生父母。
星期六一大早,我和太太就陪着小黑去了台北。小黑虽然是个壮汉,可是当他走下汽车的时候,两腿都有点软了,几乎是由我和太太扶着他进电梯上楼。大门打开,小黑的妈妈将他一把抱住,哭得像个小孩。小黑有没有掉眼泪,我已不记得了,我发现小黑比他妈妈高一个头,现在是由他来轻拍安慰妈妈。
事后,他告诉我,当天他在回台中的火车上,大哭了一场,弄得旁边的人莫名其妙。我和我太太当然识相地只坐了半小时就走了,半小时内,我观察到他的亲生父母都是非常入情入理的人。他的弟弟和他很像,可是白得多,和小黑一比,真是所谓的“白面书生”了。
我心中暗自得意,觉得还是小黑比较漂亮,尤其他笑的时候,黝黑的脸上露出一口白白的牙齿,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小黑收到一件夹克作为礼物,是滑雪的那种羽绒衣,小黑当场试穿,完全合身——这也靠我事先通风报信,将小黑的衣服尺寸告诉了他的亲生父母。
我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小黑要我请客,将他的“双方家长”都请到台中来,我这个导师只好听命。除了两对爸妈以外,我还请了小黑的哥哥和他的亲弟弟,因为大家都是很真诚的人,宴会进行得十分愉快。我发现小黑的哥哥的确比他壮得多,我又发现小黑的弟弟比他们白得多。小黑好像感觉到这一点,他说他还有一个绰号,叫做“非洲小白脸”,他显然希望由此来缩短他和弟弟间的距离。
小黑的账户中增加了很多钱,可是小黑的生活一如往常,只是周末有时北上台北,有时南下屏东。他的亲生母亲开始时每天打电话来嘘寒问暖,他只好求饶,因为同学们已经开始嘲笑他了。
大二暑假开始,小黑向我辞行。我问他暑假中要做什么,他说他要去做苦工。我暗示他可以不必担心学费和生活费了,但他说他一定要再去屏东,和他哥哥一起做一个暑假的苦工,他要让他哥哥知道他没有变,他仍是他的弟弟。
我知道屏东的太阳毒得厉害,在烈日之下抬砖头、搬水泥,不是什么舒服的事,我有点舍不得他做这种苦工。小黑看懂了我的表情,安慰我,教我不要担心,他说他就是喜欢做苦工,他还告诉我他做工的时候,向来打赤膊、打赤脚,这是他最痛快的时候。
可是小黑没有骗得了我,我知道小黑不是为了喜欢打赤膊、打赤脚而去做苦工的。如果仅仅是要享受这种乐趣,去游泳就可以了,我知道他去做工,完全是为了要做一个好弟弟。
小黑大三没有做工了,他是信息系的学生,大三都有做实验的计划,整个暑假都在计算机房里。他自己说,他一定白了很多。
暑假快结束的时候,我看到小黑身旁多了一个年轻人,在他旁边玩计算机。我觉得他有点面善,小黑替我介绍,原来这就是他弟弟。可是我怎么都认不出来了,他过去不是个白面书生吗?现在为什么黑了好多,也强壮多了?
小黑的弟弟告诉我,他已经打了两个暑假的苦工,都是在屏东,两个暑假下来,他就永远黑掉了。我忍不住问他:“难道你也需要钱吗?”小黑的弟弟笑了,黝黑的脸,露出了一嘴的白牙齿。他指着小黑对我说:“我要当他的弟弟。”
在烈日下做了两个暑假的苦工,他真的成为小黑的弟弟了。
我们有选择的权利,而每个选择都是转折。
小黑可以选择回台北亲生父母的身边,小黑的弟弟可以选择做其他轻松的工作。他们的选择,加强了彼此间的联系,不单单是亲情,还有选择后面的智慧。
(归雁生摘自《博爱》201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