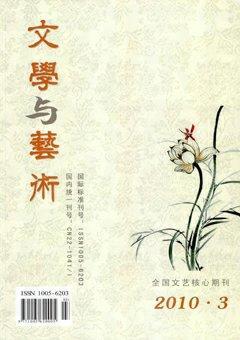东成西就
杨剑波
画了许久时间画,又在学院教书多年,自己也觉得有必要写点什么。但既不善于理论又不会修辞,我只能从绘画创作的感悟中糊乱说些什么。
在大学学习油画,期间包括了结构、色彩、明暗、材料、肌理、笔触、质感、光感、空间、构图、技法等多项造型因素,也在一段时间内利用油画的特性,极力描绘自然对象,真实的再现一物一人、一草一木。油画的特性有利于反复的修改,长时间观察和充分地表现物象。油画色彩的细微变化,以及光感、质感的不同,在画面上营造一种真实的,如身临其境的感觉。后来,经常接触一些画中国画的朋友,也时常阅读中国画,在观赏与阅读中,体会出一种似与不似之间的妙处。那么,如何在西方油画与中国传统水墨画的相互碰撞中形成独有的特色,从而获得更强的生命力呢?我从自己的风景油画创作语言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画了一些不同以往的油画创作,思考和尝试新的绘画语言。结合这种尝试,也写一点文字,谈一谈自己对油画语言发展、变化的一点认识和理解。
在美学思想和审美理念方面,中国画受儒道思想的影响,重“心”而“略”物,形成了重表现而略再现的美学观念和基础。传统西方油画所追求的是尽最大量的再现自然,采用不同的手法描摹对象。甚至寻找科学的方法(如印象派),试图更直接、更形象、更有效的表现自然,这种创作方法最基本手段是不断的观察自然,描绘自然。我试图从两者间汲取各自的优点,在绘画语言上进行融合。我把很多具体的、直接的写生重新构建。我在尝试创作中,画面所描绘的景色不具体指向是哪儿,也没有具体的视角,而是许多局部的腾挪和拼装。为了对形象的抒情达意,画面舍弃很多外在形态和光感,把个性化的构图、装饰化、平面化的手法结合在一起,强化内心体验的表达。以自己的绘画语言表现对象,力图抓住对象的本质特征及神情。我不断重视立意构思的重要作用,主张艺术形象是为了表达内心与外界之间的交流。我使用程式化、装饰化与夸张变形的手法,为对象传神,为作品达意。这与西方表现主义绘画也有相似的地方。
从绘画表现形式上来看,西方风景油画讲究构图,中国山水画讲究经营位置;风景油画对色彩研究至广,中国山水画对墨色研究至精;风景油画讲究焦点透视;中国山水画讲“三远”法则;风景油画论刀法笔触,中国山水画重骨法用笔。在色彩方面,我的作品中运用了一些黑色和类似留白的空间,再加上油和黑色,在画布上基本上可以表现水墨渲染的效果。我并不厌恶和排斥色彩,甚至非常喜爱运用纯粹强烈的色彩,在黑色与彩色的关系上,是以色(深灰、浅灰)为主,黑色为辅,加入很多鲜活的色彩,创造出许多肌理,在表达上具有更强的视觉冲击力。 我所理解的“随类赋彩”也不是完全照抄自然,而是经过自己写生和创作,从而得出的对自然物象全面的认识。我试图抛开象印象派那样追求不同光影下的色彩变化,转而进行自己的 “二次创作”来表达作品的意境。
在空间观念的认识上,山水或风景绘画上相差迥异。中国传统美术理论中,对空间观念有这样的阐述,宋代郭熙说“山有三远,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远例如: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这不是单纯的物理空间观,而是置身于自然中充满诗意的空间概念,也就是说中国画家寻求的“神游”的意境,并非现实生活的东南西北、前后左右。中国画所要求的画面是以有限的画面,表达无限的空间。这样,我们在理解中国画时,就不能把这种空间理解成科学的透视空间。为了表达这种感觉,我们可以把散点透视法代替焦点透视法,这是在中国文化背景和思想中形成的视察上的心理空间,既“心视”。这种审美观在19世纪末才受到西方的重视,提出在美术上打破时空界限,以开阔绘画的表现作用和功能。西方油画所描摹的自然就是“二维的平面空间虚幻的追求三维空间”的真实感,所以,西方对于空间理念的认识,就是对自然实实在在存在的空间的认识,既科学的空间。这并不能像中国画家那样脱离真实自然约束,“绘画成为人认识自己、反思生活”的一种形式,画家只是在自然的空间和画面中的空间的转化中充当了载体的作用,而一个思想自由的画家总是以吞吐天地浑然一体,来作为追求的目标。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理论阐述及创作研究,初见了我对风景油画语言的一些探索和尝试。油画是驳来品,其优秀的品质是要吸收和学习的。东方也有自己的审美观和文化背景,中国油画在东西文化背景下相互交融、吸取,才能获得更强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