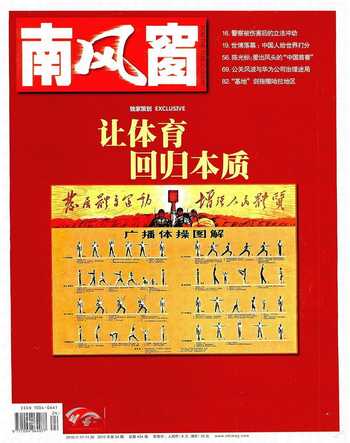名家评刊
唐艺蕾 洪诗鸿
用透明和自律重建公信力
唐艺蕾(李连杰壹基金中国区合作发展部总监)
2010年第23期的文章《如何培育慈善公信力?》道出了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困境,制度环境、体制问题、社会资本的匮乏等等。而文章从“公信力”的视角去分析这困顿的现实,可谓切中要害。
体制问题之解在哪里?开放权力、抓紧立法?当然美好,却总是步履维艰。道路漫长。文章指出捐赠人、基金会、受助机构三者之间的信任危机,那么政府怎么看呢?除了习惯性的对公民社会不放心,更有现实的案例让公众都质疑不断,但这是否就是当然的理由不放松权力?信任,不正可以成为化解一切的力量嘛!
可以说,公民社会的不够自律,让公众、公益领域的既得利益者和政府都没有形成足够的压力,去推动或接受一个享受充分制度空间保障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自身在呼吁外部制度环境改善的同时,也要反问自身,是否在内部治理和公信力提升方面足够自律?我们知道中国治理历史“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恶性循环。权力之所以不肯开放,“担心会乱”既可能是借口却也是现实。陈健民谈到“当政府明白公民社会是一种改革而非革命力量时,便无需处处设防”。除了“不是革命力量”,公益组织还必须证明自己不是“反面的力量”,那就必须“言行一致、公开透明”,没有财务丑闻,没有服务欺骗或放水,没有违法违规,而这都需要靠一整套治理机制来保障。
当然一切错综复杂,制度和体制有时正是无法透明和自律的原因。对慈善公信力的探索,只能在互动博弈的过程中推进。虽然在注册、税务、筹款、地域、与官办NGO关系等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公益组织面临制度困境,但我们还是要大声倡导、并努力落实民间公益组织的自律和问责。越是不被信任,就越需要用透明和自律来证明:公益机构有清晰的使命、严格的财务、严谨的决策、强有力的项目管理、稳定的领导人更替,并且出了问题有问责机制,这才是体制性地推动体制性问题的解决。否则,单靠个别人与政府建立友善关系取得信任,事是可以做一些,但于全局无补。(评《南风窗》2010年第23期《如何培育慈善公信力?》)
中日外交价值观的代沟
洪诗鸿(日本阪南大学教授)
本次中日间的钓鱼岛危机,虽尘埃还未落定,但事件整个轮廓已经让我们可以看出日本对世界多极化趋势的抗拒,以及企图重组中日格局的意愿。当然日本内部的路线斗争也从未停止过。从年初的鸠山内阁“脱欧入亚”的尝试到本届内阁利用该次钓鱼岛事件而成功引导舆论重回美国怀抱,前后不到半年时间。
这里可能有两个问题需要思考,一是为什么近年中日间经济合作互动不断深化,而政治总是与经济分离,甚至与美国一起常常对中国节外生枝?第二,为什么外交事务部门屡屡互相误读对方,难有互信?
如果说中日关系的外部因素是美国的世界霸权战略的一环的话,内部因素就是近年来日本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掉队者,他们很容易怪罪于中国的便宜商品和劳动力。欧洲的反移民法案,反中国商品倾销也是如出一辙。因此中国在入世后,面对这种政经不协调的双重人格外交压力越来越大。
中国人往往认为外交和人际交往一样是礼尚往来,确实老一代日本政治家颇重“义礼人情”,有着许多共同的儒家价值观。日中老政治家之间的口头协议和心领神会的交往曾经十分有效。但今天的日本社会,由于政治家的世代交替,人文理念和价值观已经今非昔比。这种深层变化,中国往往没有察觉,还是一厢情愿地以儒家风范和人情常理进行国际交往。而对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强势价值观、国际议题的话语权的应用上略显滞后。特别是国际关系中盛行的美式“现实主义”、“本国利益优先”的政治伦理使我们感到陌生而不能从容面对。
而日本的中生代政治家,行政官僚乃至整个社会在战后普遍接受美式价值教育,“现实主义”政治已经习惯成自然,加之日本人固有的暧昧(战略性模糊)和“有距离感的人际关系”,让近年的中国对日外交常常有找不到北的感觉。
国内的日本研究感觉偏重于日本古代或近代思想和文学,对现代日本的社会思想和社会价值体系以及后冷战时期日本社会科学思潮的转变较少关注。因此急需重构日本研究和对日政策。
这提醒我们,应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迎接全球化对中国外交的必然挑战。一是明确自己的立场,制定长期远景和沉着的危机处理机制。二是主动掌握话语权,多用西方语言和法律阐述中国立场和价值观,积极参与制定反映多极世界的国际规范。同时多管道输出中国的声音,比如日本相当关心中国网民的态度。(评《南风窗》2010年第23期《中日经济关系不是零和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