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大业:梁漱溟在1949
贺照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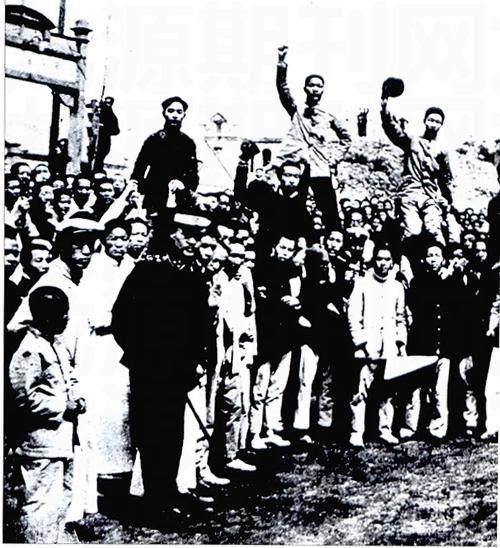

在梁漱溟看来,武力的胜利并不意味有能力掌握武力的政治主体相应形成。而政治主体阙如,必继之以武力的蜕化与新的割据。这就是梁对1949年的建国内心波澜不起的原因。但随后,他却看到不仅强有力的政治主体已经形成且扎根极深,中国人缺乏团体生活和人心麻木陷溺的情况也大有变化。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有意思的是,这一当时便在很多人心中引发强烈反应、事后更被证明具重大历史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在卷入中国现代史甚深的梁漱溟心中却没有翻起太多波澜。
就在这个1O月,梁漱溟为他用力甚深、甚久于该年完成的《中国文化要义》写了序言。在序言的结尾处,他写道:“‘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这是我的两句口号。继这本书而后,我将写《现代中国政治问题研究》一书。盖近几十年来政治上之纷纭扰攘,总不上轨道,实为中国问题苦闷之焦点。新中国之建设,必自其政治上有办法始。此无可疑也。然一旦于老中国有认识后,则于近几十年中国所以纷扰不休者,将必恍然有悟,灼然有见;而其今后政治上如何是路,如何不是路,亦遂有可得而言者。”
显然,其时梁漱溟并不认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意味着中国已突破了清末以来中国人渴望建成稳定有能力的现代国家而不得的难局。梁所以对此不乐观,并非因他对现代中国的隔膜,事实上,他的不乐观恰恰源自他对中国现代史卷入甚深、思考甚深。
疑虑与震撼
回望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起伏: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战建国”,都曾让很多人高燃热望——中国从此将步入稳定有能力的现代国家,迅速铺开现代化建设,自立于世界民族2,,ht。但结果总是希望越深,失望越深。
对这些起伏有很深观察的梁,忧心的是,既然导致辛亥革命建国和国民革命建国失败的历史条件仍在,那么,中国共产革命凭什么能逃脱失败的历史命运?
是以,1949年底梁虽应邀从重庆北上北京,但对中共能否真的开创出一历史新局未存奢望。是以,当梁和毛泽东见面,毛泽东邀请他加入政府时,梁拒绝。而梁所以拒绝,按其原话是:“我尚信不及中国能以就此统一稳定下来,以为,我如其参加政府,就落在共产党一方面,莫若中立不倚,保持我对各方面说话历来的立场资格。”可见,梁当时并不认为中共突破了太多政治力量都曾致力追求而不得的建成稳定有能力现代国家的困局。而没有根本性突破,1949年的建国不过就像以前已出现的各种旋起旋落的事件一样。
不过,梁的疑虑没有维持太久。i950年4月初到9月半,通过到山东、河南、东北许多地方考察,梁清楚地看到,虽然建国尚不满一年,但他一直梦寐以求的目标却已大见眉目,“这大半年来,我从各种见闻中,体认出全国统一、国权树立是已开了端的。”更让梁惊讶兴奋的还有,梁所一直致力改变的——中国人缺乏团体生活和人心麻木陷溺的情况,也都太有变化。
1951年5月~8月在四川几个月的土改经验,给梁以新的震撼,因为梁清楚地看到国权如此深入牢固:“此次到西南参加土地改革,在下面看了看,才知道高高在上的北京政府竟是在四远角落的农民身上牢牢建筑起来;每一个农民便是一块基石。”(梁漱溟《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可想这会给先前多年在乡村寻求中国建国出路却收效有限的梁以多强的冲击。
为什么建立稳定有能力的现代国家这么难?其核心不在社会认同分裂、国际强力干涉或精英观念分歧,挑战性恰恰在于,它是在我们通常意识中影响建国的几个最关键不利条件不能影响大局的情况下发生的。
梁漱溟认为,关键在于不能形成一种核心势力,掌握武力,建立国权,本应作为工具的武力反成为破坏统一、戕害社会的毒瘤。成功建国的关键,则在成就出有责任感、有能力、能掌握武力作为政治工具之中心势力,以此实现统一,树立国权。
这可谓直探现代中国建国困境的核心。但如何突破?梁很受阶级理论的影响,以为最方便的当然是有两大对立的阶级冲突,在冲突中产生掌握武力、树立国权的中心力量。但梁以为中国的特殊在于中国不是阶级社会,而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因此中国想通过阶级冲突建立现代国家便绝无可能,而只有走梁所设计的乡村建设道路。
这也就是梁对1949年的建国内心不起波澜的原因。因为在他看来,武力的胜利,并不意味有能力掌握武力的政治主体相应形成。而政治主体阙如,必继之以武力的蜕化与新的割据。
而深入基层考察,让他看到强有力的政治主体不仅形成,且扎根极深。中共做到这一切,走的竟然是他认为绝无可能走通的阶级斗争道路,而这等于在事实上推翻了向来自信极深的他对中国社会的基本判断。
阶级论的局限
梁氏的局限来自其思想上两方面的不足:一是把建国艰难的原因推得过远、过于宏观。二是观念框架上过于受阶级斗争建国论的限制。因此梁重点追索中国社会为什么不能形成西方式的阶级,所得出的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社会的认定,又反过来让他对现实中存在的冲突重视不足。比如,武力为什么在现代特别容易成为破坏性的要素?要知道,清末以来许多武力在兴起时都是颇有责任感和朝气的;为什么政治组织精英、社会经济精英不能最终掌握武力主体,仅仅因为这些精英没根植于一个有力的阶级吗?
以国民党的经验论,如果说起初国民党对建国中武力掌握问题认识不足,到1924年国民党改造,则已基本形成通过组织强有力的党,组建由党掌握的武力来突破军阀割据局面,实现建国的共识。经过改造,国民党在各种政治力量中脱颖而出。但为何国民党在一时的朝气之后很快涣散,没能实现孙中山以党掌握军队开创新局的设计,而共产党却走通了以党掌握军队的建国之路?是因为孙中山的后继者不想国民党真的成为强有力的列宁主义式的政党吗?看看二三十年代蒋介石的一系列公开和内部讲话,显然不是。
如果说,是因为大革命顺利开展导致太多投机者涌入国民党,那共产党在大革命中以几何级数扩张也同样碰到思想、组织、行动的混乱问题。当然,1927年国民党对共产党的镇压帮助后者清除了动摇分子。但接下来,抗战中共产党成为全国性政治力量,特别是在国共战争胜利在望时,共产党又何能避免急速扩张带来的问题?
问题的关键是有没有找到建立稳定的核心,有召唤力、说服力的论述、制度与组织、生活机制,可把涌入的有朝气有责任感的力量不断转化为自己可以依赖的组织、精神和实践机体,从而使得各种不可避免的带有投机性的力量,不仅不会左右党内氛围,而且在事实上真的做到不倚赖他们。这么说,是指许多这类投机性的力量更具政权运作经验和社会活动经验。因此,当国民党北伐从广东一隅迅速蹿升为全国最大力量时,便在极大程度上倚赖这些精英构成自己的权力机体,后果便是蒋介石一再抱怨的国民党革命精神的迅速衰败。相比,共产党也大量使用这类精英,但值得分析的是,共产党却基本做到了为己所用,而不被其改变。
蒋对国民党失望后,曾颇寄望军队成为改造社会与政治的力量。

确实,构成国民党武力核心起点的黄埔,主要由被民族主义救国热情所激动的热血青年所组成,以这样的力量为酵母改变社会与政治并非可不能。但事实是,军队同样不能避免自身的热情衰退,乃至腐化、堕落,在国共内战中,数量和武器装备上具绝对优势却被迅速击垮。
这些当代事实不仅未被梁细致思考,且被快速作为梁阶级论逻辑正确的佐证。即,国民党的暮气、涣散被认为没有根植于一个明确的阶级,而军队的犬儒、虚无、破坏性,则被归为这武力本身没有一个政治主体掌握,而孙中山所希望的国民党成为掌握军队的政治主体进路所以失败,仍被解释为国民党没有根植于一个阶级。
大革命失败的教训
没有阶级斗争就没有中国共产革命。但过度强调阶级斗争,不可能深入理解中国共产革命。要成功运用阶级斗争手段,有许多相关结构性课题必需加以解决。
首先,被中共认为革命的阶级并不自然起来革命,特别是并不自然参加国共分裂后中共要生存壮大离不开的武装斗争。毛泽东在井冈山组织武装斗争时便碰到这个问题。当时,再分配土地的受益者贫农很少参军,红军兵员的主要来源是俘虏和游民。这带给中共很大挑战,因为行伍和游民是有着很强特定习气的人。加之当时红军条件艰苦,牺牲大,武力易处于中心位置,可以说,在面对武力不受政治控制、易往破坏性方向发展的问题方面,共产党有着更不利的条件。但有意思的是,共产党何以在更不利的情况下扭转了状况?
其次,被唤醒的阶级起来之后,有很强的惯性和冲力。20年代国民革命的经验很典型。对工农的广泛唤醒是国民革命的巨大成功之一,但同时也是国民革命所遭遇的许多重要困难的根源。工农力量被唤醒后并没有自然汇入唤起他们的精英所期待的政治、社会、组织轨道,反而威胁到社会要存在所必不可少的秩序和组织的维持。
所以,当时毛泽东一边公开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称赞农民运动“好得很”,并宣称不拥护这个运动的,就是反革命。另一方面则在不发表的给当时中共中央的信中承认,虽然农村要彻底改造,离不开“一个烈风暴雨的农村革命”,非此“决不能推翻封建阶级几千年累积的权力,决不能迅速完成民主革命”,但若不能迅速过渡到“联合战线”阶段,则农村无政府状态不能迅速解决,农村的武装、民食、教育、建设问题也都不能有“最后着落”。
不过,看到了并不表示当时他已找到有效的过渡方法。毛泽东只是策略性提出,凡面对诸此问题,“均必须抬出K.M.T.(注:国民党)的招牌去解决,万不可马上抬出CP(注:共产党)的招牌去解决。因此农民中必须普遍发展K.M.T.,让K.M.T.去调和敷衍这些极难调和敷衍的事情。”(毛泽东:《视察湖南农运给中央的报告》)
而同样,刘少奇大革命时期对工运的观察和经验,向我们显示了被唤醒的工人阶级的运动组织方式,和前述的农民革命存在一样的问题。
在1937年2月20日刘少奇致当时中共中央负责人洛甫(张闻天)的长信中,刘谈到工人运动的“左倾”问题:“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作时间至每日四小时以下(名义上或还有十小时以上),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搜查轮船火车,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在当时是极平常而普遍的……
“这些事干起来,而且是越干越厉害,在社会上、经济上、人心上要发生严重的影响,是无疑的。企业的倒闭,资本家的关门与逃跑,物价的高涨,货物的缺乏,市民的怨恨,兵士与农民的反感(当时有许多小城市的工会被农民捣毁,而且是农民协会领导的),军官与国民党人的非难,就都随着这种‘左的严重程度而日加严重起来。而工人运动在当时是共产党负责的,这一切非难,就都加在共产党身上。人们并不责备工人,而责备这是出于共产党的指使,这就影响共产党与各方面的关系。
“在起初人们都恳求共产党想办法,改正这种情形,就是政府都不直接去干涉工人,共产党在当时也责无旁贷,答应改正这些事。但共产党未能改正这些事,而且连阻止这些事的发展都未做到,这就使得人们走入另外的出路。反革命就从而大施阴谋,利用来组织反革命的暴动。
“大革命的失败,无疑是由于右倾的错误(注:指未能更积极抢抓革命领导权,未能更积极组织自己的武装、组织力量等),但在失败以前及以前很久,并不是没有‘左倾错误的。这种‘左倾错误,至少是帮助了反革命,帮助了右倾。”
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叙述,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大革命之所以后来被逆转,并博得相当社会阶层的同情与支持,与大革命唤起了工农等社会力量后,不仅不能有效将其导入自己所期待的轨道,甚至不能将其控制在社会维持起码运转所必需的秩序之内有密切的因果关联。
团体与精神
与大革命相比,共产革命唤起工农与阶级斗争开展的程度,更广更深。后者为什么不仅没使社会必要的运转被破坏,且被唤起的力量还被有效组织到既定轨道中去了呢?显然,这得益于中共自身力量的扩张,和一套发展得越来越成熟的政治、组织技术。然而这套技术的运用必需一大批原本就有民族责任感、相当的政治理解力和组织领悟力的精英作为核心主体。怎么转化、训练出大批这样的精英就成为问题。
在近年流传颇广的黄仁宇关于中国现代史的说法中,他认为蒋介石为现代中国建造了一个上层结构,毛泽东打造了一个下层结构。但中共如不能建立起一个坚固的力量核心,并在实践和论述中发展精英的转化与训练机制,是不可能成功进行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动员,并成功把这些被动员唤起的力量组织为自己可以稳固依靠的社会基础的。也就是,中国共产革命不可能在没建造出一个足够有力的上层精英结构的情况下,打造出一个下层结构。
同样,假设蒋真的按梁漱溟有关建国的核心理解,建造出了一个稳定、能牢固掌握武力的政治中心势力,加上事实上蒋已占尽先机,中共怎能与其抗衡?
毛泽东说,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衡之中共前期历史,这的确是事实。但更重要的是历史的另一面:更多数的五四运动骨干分子加入了国民革命和国民党。试想,如果蒋和国民党始终保持了对有责任感、有献身精神、有现代眼光青年知识分子的吸引力,并把他们有效转为党和政府内充满活力的力量,再结合国民革命军初起时的热情和朝气,党军交互影响共进,那中共还有机会吗?
但事实上,北伐胜利后,国民党始终没有再获得大规模转化精英为自身有效机体的能力。并不是国民党缺少机会,最突出的就是抗战开始时社会热情是明确指向国民政府的,但国民党和蒋却并没有把握住机会。而抗战阶段共产党成功建立起吸纳青年知识分子为自己论述、宣传、组织骨干的机制。一得一失,衡之历史,实为二战后国共迅速易势之重大关键。
孤立地谈论阶级斗争和土地问题,会让我们无视丰富的历史实践过程。本来,梁在《中国的建国之路》相当重点谈中国共产革命中的阶级斗争,对全国统一、国权树立的重要性,但同时梁也以很大的注意力,认真讨论中共成功引进团体生活和中共革命成功“透出了人心”。
可惜的是,此后他虽然注意到这几面的实现在中共的土改实践中原是被连成一体的,但却未能历史地去观察团体生活和精神问题在中国共产革命中的位置和它们的历史演变过程。而梁所以失掉这一契机,固和当时中共对自身成功的解释越来越意识形态化,即越来越偏向阶级斗争论有关,也和梁原本就偏向阶级斗争建国论密切相关。
北伐胜利后,国民党始终没有再获得大规模转化精英为自身有效机体的能力。并不是国民党缺少机会,最突出的就是抗战开始时社会热情是明确指向国民政府的,但国民党和蒋却并没有把握住机会。而抗战阶段共产党成功建立起吸纳青年知识分子为自己论述、宣传、组织骨干的机制。一得一失,衡之历史,实为二战后国共迅速易势之重大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