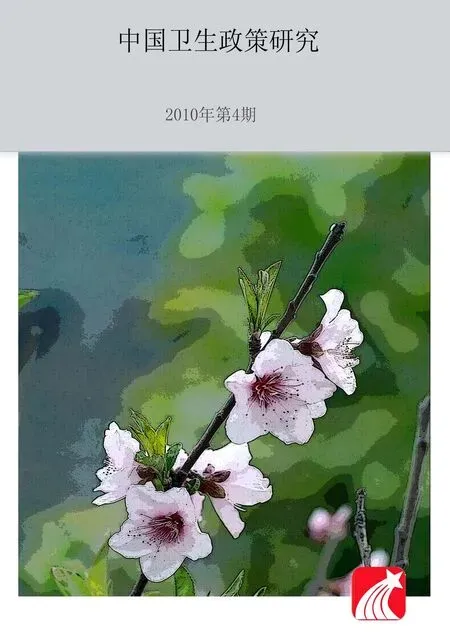世界卫生组织政策的挑战及应对策略研究
韦 潇 郭 岩 李世绰
1.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 北京 100020
世界卫生组织是公共卫生领域最重要的国际组织之一,但近年来无论在联合国系统、各国际组织之间,还是在成员国,甚至在组织内部不同层级机构间,世界卫生组织的权威性和影响力都存在下降的挑战。本文就世界卫生组织政策面临的主要挑战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未来发展的建议。
1 世界卫生组织政策面临的主要挑战
作为国际卫生领域的重要组织,世界卫生组织曾是国际卫生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近年来其影响力日益下降,这是健康领域发展、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世界卫生组织自身的政策也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政策过于技术化,宏观战略性不够
纵观世界卫生组织60年的政策历程,有两个阶段的政策主张是受到好评的[1],一是上世纪70年代末,马勒博士将发展基层卫生机构、发展基本卫生服务等技术层面的各种政策概括成为“人人享有健康”的政策理念,并把这种理念与基本人权和国家责任联系到一起;[2-5]另一个阶段是布伦特兰博士将健康与宏观经济联系在一起,把卫生置于全球发展议程之中,这两个阶段的政策都极大地提升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影响。[6-7]而其他时间内,世界卫生组织都埋头于各种具体项目与技术规范的制定,影响力又慢慢下降。虽然这一情况因SARS爆发而有所改善,但其主动提升和参与的意识仍不足。可见,虽然世界卫生组织是以专业技术见长的,但主动提升其在国际社会上的政策主张,把政策与整个国际经济社会发展相联系,对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提升国际地位仍是十分必要的。
1.2 政策约束力低,执行力弱
迄今为止,世界卫生组织只有《国际卫生条例》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具有较强的法律效力和约束力,其他政策和规范都不具有强制性,是否执行都取决于成员国自身。西太区办事处的一位部门负责人谈到:“成员国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态度分为三类:一是根本不需要世界卫生组织,对其呼吁和政策不予理睬;二是部分需要,它们既不愿意公开违背世界卫生组织政策,但也仅把它当作利用的工具,选取政策中有利的部分,发展自己、制约别国,甚至在技术指南上也可能受到这些国家意志的影响;三是发展中国家对世界卫生组织政策比较重视,但这些政策又很难适应本国需要,而且常常受到世界卫生组织批评,其政策反而成了成员国的负担。”世界卫生组织的组织机构、运行机制和领导体制都影响了其政策的执行,总部、地区办事处以及国家代表处之间的组织结构问题导致政策执行不统一,常常使政策难以有效贯彻。领导人的更替,也经常导致政策不能延续。
1.3 选择政策重点时受到现行预算方式和投入机制的极大限制
以往的政策制定程序和原则都表明,其政策制定应从主要卫生问题出发,但实际上,世界卫生组织选择政策重点时受到现行预算方式和投入机制的极大限制。有专家就指出,世界卫生组织目前突出的问题是“工作重点随着经费走”,“没有固定的经费,再重要的领域也没有发展,甚至不断的萎缩”。西太区官员也指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危害日益加大,但由于资金所限,世界卫生组织的重点还是放在传染病上”,“卫生系统的发展是世界卫生组织设定的重点领域之一,但目前预算的1/3仍是传染病,应该被重视的重点领域,如卫生系统建设仍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可见,资金资源和预算方式对政策重点选择有着很大影响。世界卫生组织仅有1/3是预算内资金,2/3的经费来自预算外的自愿捐款,虽然这为世界卫生组织注入了大量资金,但由于大多资金都附带着捐助者的意愿流向指定的领域,很大程度地影响了世界卫生组织政策制定和执行。对此,《柳叶刀》杂志评价,“捐助者感兴趣的优先领域左右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1]陈冯富珍总干事也非常清楚世界卫生组织的预算问题,她曾组织过20个最大捐助方讨论增加非定向的预算,使世界卫生组织有更大的弹性,能够把工作聚焦在优先的全球卫生问题上。但她也表示“为了保证履行责任,我们目前还不能舍弃带有意向的捐款,我们要尽可能与合作伙伴共同说服投资者投入更需要的领域”。
1.4 政策制定过程中协调能力不强,存在消极妥协
在世界卫生组织政策制定过程中,成员国的合作、协调与妥协越来越重要,其中,妥协成为政策决策过程中的必然选择。[8]有些学者认为,产生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是世界卫生组织的结构和管理方式,“要使192个成员国共同应对同一核心卫生问题是非常困难的”,加之各种相关行业和利益集团的意愿也在影响决策,因此妥协不可避免。有些研究还证明,这与国际组织着重于集体安全设计的决策模式有关,也是国际组织的“通病”。[9]在政策学中,政策妥协可以分为积极妥协和消极妥协,积极妥协能够协调和促成各方的目标趋于一致,促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消极妥协是政策实施效力减损的重要原因,导致严重的政策执行损失。虽然妥协不可避免,世界卫生组织应更积极的协调,减少消极妥协,提高决策效率和政策执行力。[10-11]
1.5 未能配合国家的实际卫生需求、资金使用效率不高
有些学者认为,世界卫生组织的政策和投入重点往往不能针对国家最迫切和切实所需的卫生问题,如非洲国家的儿童免疫、基本饮用水等问题。这样严重的卫生问题和政策缺失,并没有得到世界卫生组织足够的关注。目前,多部门投资于卫生的现象很普遍,确实形成了浪费,要避免这一问题,只有使卫生投资项目由受援国决定,而不是投资者。由国家政府主导,制定综合的卫生规划,负责导向资金和政策,才能切实发挥世界卫生组织政策和投入的作用,解决各国实际的卫生需求。[12]相比起来,那些政治实力相对较弱的国家更需要国际组织的支持,也更愿意听取它的建议,然而世界卫生组织却没有深入了解这些国家的需求并选择适宜的合作方式,在投入的同时附带了很多限制性条件,给这些国家造成了负担。
1.6 关于世界卫生组织的功能定位、工作重点和未来发展仍有分歧
虽然世界卫生组织强调健康对于政治经济和国家发展的重要作用,这大大提升了卫生的战略地位,但对于世界卫生组织是否应在健康相关的更多方面发挥作用,不同专家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专家认为,全球卫生问题是世界卫生组织制定政策的基础,既然影响当前健康问题的因素越来越复杂,世界卫生组织就要着手制定政策解决问题,与此同时,不能单纯依靠卫生部门解决问题,需要依靠多部门参与。也有人反对世界卫生组织扩大对健康领域的关注,如西太区卫生发展部门的负责人就认为,“世界卫生组织不可能成为各国卫生工作的领袖和领导,它应发挥的作用就应是在国际卫生的技术方面给各国提供帮助、咨询和指导,只能帮助成员国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提供更科学的证据,而不能左右政策。”也有专家指出,“世界卫生组织没有技术能力和政治影响力去改变诸如环境变化等问题”。美国一家独立咨询机构的全球发展中心项目执行副主席Ruth Levine曾指出,世界卫生组织应该先帮助大多数国家建立起核心的公共卫生功能,如卫生设施建设、信息共享、疾病研究等,在做好这些工作的基础上,再考虑拓展更多的卫生领域。[13]
2 对世界卫生组织未来政策发展策略的思考
对于整个国际组织的未来发展趋势,学术界有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认为虽然国际组织在经济和社会领域能够取得一定成绩,但其作用十分有限,“它只能在有限的领域办成有限的事情”,一旦所涉及的问题在政治或经济上与国家利益相冲突,国际组织注定无所作为。而另一种观点相对乐观,认为全球化的发展要求更多的国际合作和国际机制,每个国家对国际组织的需求与期望将进一步加大,这对提升国际组织的影响力是难得的机遇。在客观上,国际组织职能和作用的继续强化是目前国际社会的一个基本事实。[14]
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对卫生问题日益关注,既是世界卫生组织发展的机遇,也是未来新的挑战。许多成员国开始呼吁世界卫生组织要进行改革,以全面提升其权威、地位、作用和影响。这种权威不仅仅取决于世界各种力量对于它的认同和期许,同样取决于它是否能够对未来国际卫生领域具有控制力和影响力。具体来说,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作为技术权威,具有满足不同层次需求的技术保障;二是在技术可实现的基础上,能够拥有或调动足够的资源,解决卫生问题;三是建立被各方认可的国际规则和制度,并确保制度规则的有效运转;四是在思想和理念上能够不断创新,成为该领域的引领者(图1 )。

图1 发挥组织影响力的四个关键方面
就世界卫生组织在历史上取得的成就和发挥的作用,以及目前的资源和能力,作为联合国的专门机构,世界卫生组织应该承担起技术指导和管理的双重责任。而世界卫生组织要确保在国际卫生领域的权威和作用,其组织发展的基本策略应该是:“保持技术领先的优势,提高获取资源能力,建立更多有约束力的规则,不断创新理念,成为健康引领者”。在这一理念下,对于具体政策的制定、实施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2.1 发挥技术优势,政策制定中要多利用研究信息和证据
相比起一些新进入卫生领域的国际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在资金资源的动员协调上并不占优势,却拥有更多的人才和技术优势,各专家委员会聚集了世界上最优秀的卫生专家,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和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卫生组织就应该充分利用其技术优势,为解决各种卫生问题提供技术保障。为此,世界卫生组织应该充分发挥技术优势,迅速、有效的解决卫生问题;还要就新现象和新问题加强研究,主动与政府、民众和其他机构沟通信息,保持技术的领先和权威。尽量多地把研究成果转化成政策依据和国际通行的标准和规则,避免束之高阁。
2.2 提高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的能力
只有把研究成果和技术优势转化为政策才能使更多的人从中受益,在这个过程中组织的权威和影响力才能进一步提升。然而,政策转化能力的不足恰恰阻碍了世界卫生组织把自身的技术优势转化成强有力的政策优势,逐渐被其他更具政治影响力的组织挤占了原有地位。2005年以来,世界卫生组织向各国提倡循证卫生决策,就其自身来讲,世界卫生组织并不缺乏好的研究证据,而是缺乏把成果转化为政策,把政策转化为健康结果的能力。因此,世界卫生组织要想提升自身的权威性,就必须努力提高这种成果转化为政策的能力,这决定了世界卫生组织能否从专门技术机构向行业领导者转变。
2.3 根据主要卫生问题和资源状况,选择战略重点
确立组织发展长期战略方针后,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无论什么样的政策都要结合资源状况和现实卫生需求,否则无法实现。世界卫生组织应根据现阶段的主要卫生问题和资源技术水平选择战略重点,并明确目标、注重落实,分阶段的产出政策成果。在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的《2008—2013年中期战略性计划》中,就选择了13个卫生重点领域[15],主要包括减轻传染病的卫生、社会和经济负担;与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作斗争;预防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在生命的主要阶段改善健康;减轻突发事件、灾害的健康后果以减少负面的社会经济影响;促进卫生与发展,预防与减少危险因素;以及环境、营养、信息、技术和国家领导等卫生领域各个方面。
2.4 选择能够代表组织的核心政策,并注重其长期性和统一性
国际组织学研究者认为,国际组织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它的矛盾性。一方面,成立国际组织是人们对公平、正义、合作的美好理想追求,国际组织的原则和宗旨大多如此;而另一方面,国际组织又是现实中各国谋求自身利益的场所,意识形态的分歧、强权行径常常使国际组织在运行过程中陷入无法执行的困境。能否坚持公平正义,坚持组织最初的宗旨,成为每一个国际组织面临的严峻挑战。早在成立之初,世界卫生组织就把其宗旨写入《组织法》,即“使全世界人民都获得可能达到的最高水平的健康”,并强调这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之一。后来的“人人享有基本卫生保健”思想和“初级卫生保健”政策之所以到现在都被大多数人认可和称道,正是由于它们体现了卫生领域理想的价值观,即平等、高质量和可获得性,并成为评价其他政策的标准。随着时间推移、卫生问题的增多,世界卫生组织的政策越来越庞杂和细致,对各种利益的妥协往往使组织的核心价值观被众多具体政策所淹没。因此,建议重新确立指导世界卫生组织今后20年的总政策,无论是继续坚持“人人享有基本卫生保健”思想,还是结合未来需要,重新确立新的核心政策, 这一政策应作为组织的长期方针,不受成员国或领导者影响,保证延续性和统一性,以便能够指导和检验世界卫生组织的长期健康发展。
2.5 加强部门沟通,改善融资模式
除了政策内容本身外,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方面的不协调也会对政策的各个环节产生影响。从1990年代末开始,世界卫生组织机构内部间政策思想不统一、行政效率低下等弊端被广为批评,实行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近年来,陈冯富珍总干事把改善组织机制的重点放在加强总部和地区办事处理解和沟通上,成立了由总部首脑和地区主任参加的“政策小组”(globe policy group),并加强与成员国的联系,共同商讨组织发展的重大事项和国家策略,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有利于政策在制定上更有针对性,执行上更好贯彻落实。此外,世界卫生组织还应多方尝试新的融资模式,增加获得资源的渠道。如发展多领域的伙伴关系,拓展公共政府部门与私营企业合作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PPP),以争取更多的政策资源,同时达到各方的“双赢”或“多赢”。
参考文献
[1] Samarasekera U. WHO: 60 years on[J]. The Lancet, 2008, 371(9619): 1151-1152.
[2] WHO. Health-for-all polic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Fifty-first World Health Assembly[R]. Geneva, 1998.
[3] Health for all——all for health. 40 Years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J]. Acta Chir Plast, 1988, 30(4): 193.
[4]阿拉木图宣言[R]. 阿拉木图: 国际初级卫生保健会议, 1978.
[5] Chan M. Return to Alma-Ata[J]. The Lancet, 2008, 372(9642): 865-866.
[6] WHO. 1999年世界卫生报告: 健康改变世界[R]. 日内瓦, 1999.
[7] Health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WHA55.11)[R]. Geneva: WHO, 2002.
[8] 施忠道. WHO总部组织机构改革[J]. 国外医学社会医学分册,1999, 16(4): 154-157.
[9] 刘圣中. 政府权威下的有限妥协——政策执行的三方行动分析[J]. 南昌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 37(1): 17-23.
[10] Fee E, Cueto M, Brown T M. WHO at 60: Snapshots from its first six decades[J]. Am J Public Health, 2008(98): 630-633.
[11] 史哲. 向现实妥协:对集体安全组织决策模式的分析[J]. 国际论坛, 2002, 4(6): 47-50.
[12] WHO. Strengthening health system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R]. Geneva, 2001.
[13] 饶戈平. 全球化下的国际组织[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14] WHO. 2008—2013年中期战略性计划修订本(草案)[R]. 日内瓦,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