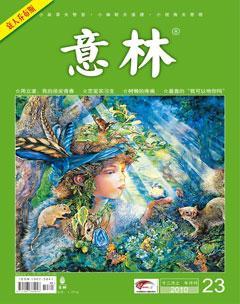终局
安德烈•阿加西
我出生时脊椎前移,腰骶部的一块椎骨与其他椎骨是分离的。这块椎骨特立独行,如反叛者那样(这也是我走路内八字的原因)。由于这块“与众不同”的椎骨,我脊柱内部神经的活动空间相应缩小。正常人那里的空间本就不是很大,我的则非常小,因此哪怕只是微微地动一下,那里的神经都会受到挤压;加之还有两处椎间盘突出,以及一块想要保护整个受损的区域而徒劳疯长的骨头,我的那些神经感受到了彻底的压抑。当那些神经开始抗议其狭促的立足之地或发出求救信号时,疼痛就会在我的腿部四处游走。这种疼痛使我呼吸困难,甚至语无伦次。因此我一直都在与我的身体谈判,大多数时候,谈判都以可的松为中心。打上一针可的松,疼痛可以暂时得到缓解。但是在可的松起作用之前,要经历非常痛苦的注射过程。
我昨天打了一针,这样今晚我才能够比赛。这是这一年的第3针,我职业生涯的第13针,也是迄今为止最为骇人的一次。由于我的椎间盘突出和骨刺的阻挡,他无法使针头直达神经附近,于是他尝试“绕道”注射,希望能破除我背部的“枷锁”,这使我疼痛异常,不堪忍受。他首先将针头刺入,然后把一个大型X光检查仪压在我的背上,查看针头离神经有多远。他说,他得使针头紧靠神经,但又不能碰到神经。如果针头碰到了神经,哪怕仅仅是轻轻掠过,那种痛苦也足以毁了我的整个赛事,甚至可能改变我的一生。刺进去,拔出来,动一动,他不断调整着针头的位置,直到我疼得眼里充满了泪水。
最后,他终于找准了位置。“正中靶心。”他说。
可的松被注射进去了,那种灼人的痛感使我咬住嘴唇。压力不断增加,一度我甚至认为我的背即将爆炸。
请让这一切结束吧。然而,我还并未准备好就此结束。
职业生涯的终点线与一场比赛的终点线并无差别,目标就是触及那条终点线,因为它散发着一股极富磁性的力量。当你接近终点线时,你能感受到那股力量在吸引着你,你可以借助那股力量实现穿越。但是就在你即将获得那股力量时,你又感觉到了另一股同样强大的力量,正将你推离终点。这一点令人费解,神秘玄妙,但这两股力量确实同时存在。我深有感触,因为我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都在追寻着其中一股力量,同时在与另一股力量进行斗争。
在我看来,网球使用生活中的语言绝非偶然。一局终了;几局过后,一盘完结;等到数盘打下来,胜负分出,即是一场比赛。各个环节都联系得如此紧密,以至于任何一分都有可能成为转折点。这令我不禁想起秒、分钟、小时之间的那种关联。生活中的任一小时都有可能成为最美好的时光,但也有可能留下最黑暗的记忆,这取决于我们的选择。
但如果网球就是人生,那么球赛终局之后,则必是不可捉摸的空虚和寂寥。
我回想起那些特别的胜利———那些球迷们不会记得的,但却仍会令我难以入眠的胜利———在巴黎对阵斯奎拉里、在纽约与布莱克鏖战、在澳大利亚与皮特一争高下。我珍惜其中的分分秒秒,当然也会回想起一些失败,想到失望之处时我摇摇头。我告诉自己,今晚不过是场考试而已,而且考的是我已经学了29年的东西。不论发生什么,我至少已经经历过一次。或是身体上的测试,或是精神上的考验,没有什么新鲜的。
(聂勇摘自《阿加西自传》中信出版社 图/宋德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