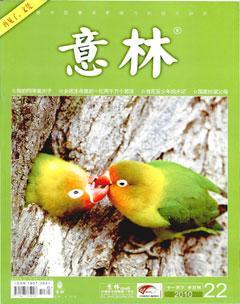考试奴隶
我爸爸要参加公务员的考试,要我辅导他。
我原本不大乐意。因为前几天他刚刚怒斥过我冷漠不讲人情,废物,做人失败,我内心还有怨气。之后的几天里,我爸每天下午都打着赤膊,手里拿着笔坐在饭桌面前,对着一大摊参考书和草稿纸算题。我们家的饭桌矮得突破人体工学的极限,我爸佝偻的脊柱和突出的肩胛骨,让我生出很大的同情,所以当他再次一路响亮地穿着拖鞋走到我面前,表情严肃得像要通知我一个噩耗,并说“你看这道题怎么做?”的时候,我就不忍心拒绝了。
几乎所有的数学题我爸爸都不会做,我给他讲解完一道题,就看到他缓慢而漫无目的地在草稿纸上临摹一遍我写的算式。我们家喜欢没有意义地相互打击,当我爸结束了一天的学习时,我妈就兴高采烈地对我爸说:“你女儿说你一道算术题都不会。”话音未落,我和我妈同时条件反射地瑟缩着脖子,以为会被骂,结果我爸听到后很温和,没有大吼大叫。
在我爸考试之前,家里那个谨小慎微的人一直是我。我从来没有对自己被压迫的身份质疑过,更毋论是反抗了。直到最近,我才明白了为什么:我唯唯诺诺了近20年,只是因为我当了近20年的职业考生。“考试”的表面目的是为各种的社会填充物挑选材料,然而,“考试”的核心目的则是恐惧。恐惧是最强韧的链条,绑得人屏气凝神,万众一心。
我身边的所有同学,在经过那场所谓“决定人生”的高考之后,都有种上当受骗的轻微茫然。这就是关于考试最大的谎言:它并不是孤注一掷,大喝一声“show hand!”(手上已经没有筹码了),而是一场惨淡的等待。
我们家住在一所高中旁边。已经开学几天了,我每天早上都可以看见一行行学生走进校园,我却无端地想到另外一幅画面。清朝的赵翼是皇宫的守卫,他回忆站岗时看到皇子们上学的景象:冬天的凌晨3点半,冷得要死,黑得要死。可每到这个时候,总会看到一行灯笼在阴森的紫禁城里走,后面跟着一行小孩儿,低着头走得整整齐齐,静悄悄地进入大内,走进书房。这就是一天学习生活的开始。
(尘中塑摘自蒋方舟的新浪博客图/何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