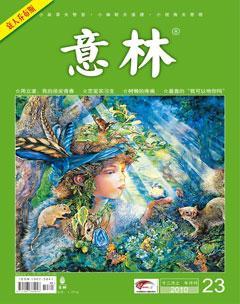一个厌食症患者的自述
Graeme Dalling
我以前一直是个胖乎乎的孩子,但我吃东西却非常挑剔。吃饭时,妈妈做的饭菜总是被我剩下。到了13岁,我开始留意自己的外表,并且把自己和其他人进行比较。我迷恋上了班里的一个女孩———我希望在她面前有个好形象,于是开始强迫性地锻炼。然后我开始限制饮食,不吃那些我认为不健康的食物。起初我看起来很棒———我不那么胖了,身材很好。14岁生日那天,我甚至得到了心仪女孩的亲吻。
然而,那时我已经得上了厌食症。记得我当时的想法是:如果我瘦了一点儿就得到这个回报,那么再瘦下去的话又会发生什么呢?我开始不吃饭,直到一整天只吃一个苹果。我很享受饥饿感,我全神贯注于这种感觉,以致不再关心那个女孩。这时我的节食已经和让自己更有吸引力无关了。
那时关于厌食症的资料还不像现在这么多,而且它只与青春期女孩和模特相联系。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体重迅速下降。爸爸认为我一定在吸毒,妈妈流着泪恳求我多吃点。我变得精于欺骗她:把土豆放在花盆里,巧克力藏在沙发后面,烤面包片塞进书桌抽屉里。
她每天都给我称体重,我必须确保在口袋里塞满东西,以增加几磅重量———过一会儿我会回去称我的真实体重。由于我在谎言中生活,我成了一个孤独的人。我和朋友们失去了联系,周末在繁华的大街上独自游荡。我走进书店,聚精会神地读关于饮食的书以及食谱。我所有的念头就是食物,而读食谱弥补了我食物摄入的不足。
事实是我知道自己已经瘦得不正常,但每次站在镜子前,我仍然看见一个胖子在盯着我。我被困在自己的身体里———我想求助,但我的大脑不允许。厌食症的致命之处就是这种生理和心理的搏斗。我无数次想到自杀。有一次我走进商店,问他们有没有安眠药。还有一次,我和妈妈发生了特别激烈的争吵,当时我差点从车里跳出去。
15岁时,我的体重刚刚超过5英石(注:即70磅,约等于31.75公斤)。我没有脚趾甲———它们由于衰弱而脱落了。我的皮肤变黄了。由于长期以水果为食,我的牙齿被酸所腐蚀。我的一个转折点发生在一天早上,妈妈走进我的房间把我叫醒,说房间里有腐烂的气味。我当时简直就是躺在床上变得日益瘦弱。即使作为厌食症患者,我也知道这样很糟糕,我必须做些什么了。
我决定不去医院治疗。我从来不愿承认自己病情的严重性,所以我学着自己好转起来。我开始重新训练自己的大脑,告诉自己吃东西没什么不好,增加体重并不会使我变成胖子。我慢慢开始增加食量,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恢复了体重,尤其是我的面部。不管吃什么,我的身体都会迅速吸收。这是一个痛苦的生理恢复过程。21岁时,我的体重达到了10英石,我终于能够从容地面对自己了。
我常常觉得很好笑:我选择了做演员,这种职业决定了不断有人对你的外表评头品足。你很难不把自己和其他演员作比较,而且经常感到压力,要求你改变原来的样子,把自己套进某个模子里,然而这却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帮助了我。在我感觉最糟糕的时候,我靠表演来逃避。在舞台上,我可以成为任何人,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我不是厌食症患者。
现在我24岁,还在恢复的过程中。最近我有一次复发,起因是我要为了演一出对身体要求很高的戏而减肥。这是厌食症的后遗症———它在你的大脑里留下印记。当我决定晚餐吃什么或者决定去跑步时,它就发挥了作用。我所做的一切都和我的进食障碍有关。但我现在年纪更大、更聪明了,当我发现事情过了头时,我就会采取行动。我知道自己曾经是什么样,我不想再退回那一步。我有很多理想,不会让过去的经历阻止我实现理想的脚步。
(白蹄乌摘自《21世纪经济报》2010年10月12日 图/大卫卡森)